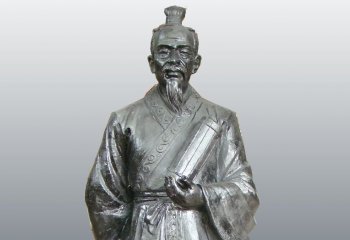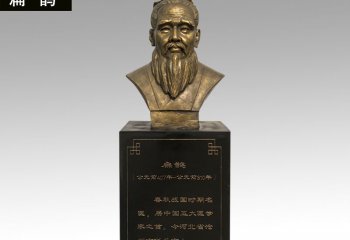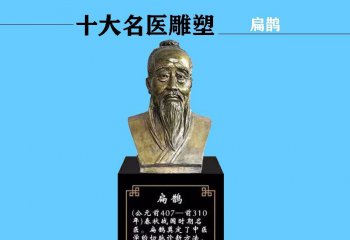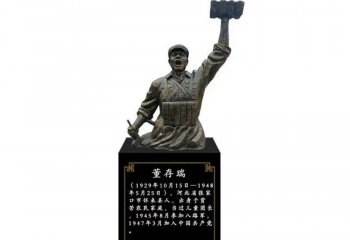當代藝術過去三年在中國上演一場藝術資本主義的中國狂歡,這是一場有里程碑意義中國藝術體制轉型的陣痛,也是中國政治和經濟改革模式畸形化的產物。藝術的資本主義化并非人類歷史上沒有實踐和理論上的先例,從法蘭克福學派思想家本雅明提出的“資本主義時代的藝術生產和復制”、美國批評家格林伯格提出的“前衛的媚俗化”到法國哲學家鮑德里亞的藝術的“商品符號學”,這不僅在中國已經變成現實,而且形成一種更極端化的藝術商業化,我把它叫做“藝術資本主義在中國”。當代藝術在市場資本主義的泡沫下,正在產生以當代藝術和市場運作名義下的“新官方藝術”和“新商業藝術”。

近半年關于當代藝術是否存在“天價騙局”,以及藝術市場是否應該絕對的自由市場化的辯論,不僅是一場關于藝術市場本身的經濟學辯論,實際上,這涉及到中國藝術未來的價值取向以及藝術體系的建立。它是一場關于當代藝術價值觀的辯論。當代藝術是否需要與主流社會保持距離?這是整個關于藝術市場辯論的核心問題。

目前當代藝術走在一個十字路口,因為中國藝術不知道自己處在一個什么樣的承上啟下的位置,不知道自己從哪里來,要到哪里去?拜金主義和主流化正在當代藝術蔓延,眾多的藝術圖像越來越跟時尚雜志的趣味沒有什么區別,不少成名藝術家將自己大部分精力用于市場經營,津津樂道成為達官貴人和新富階層中的一員,藝術語言抄襲模仿現成的照片和著名形象,藝術創作變成制造空洞的符號,再使用藝術史理論解釋這個符號,使其變成可以高價銷售的著名符號,藝術創作變為成批生產和復制,藝術作品商品化和金融化,藝術家企業家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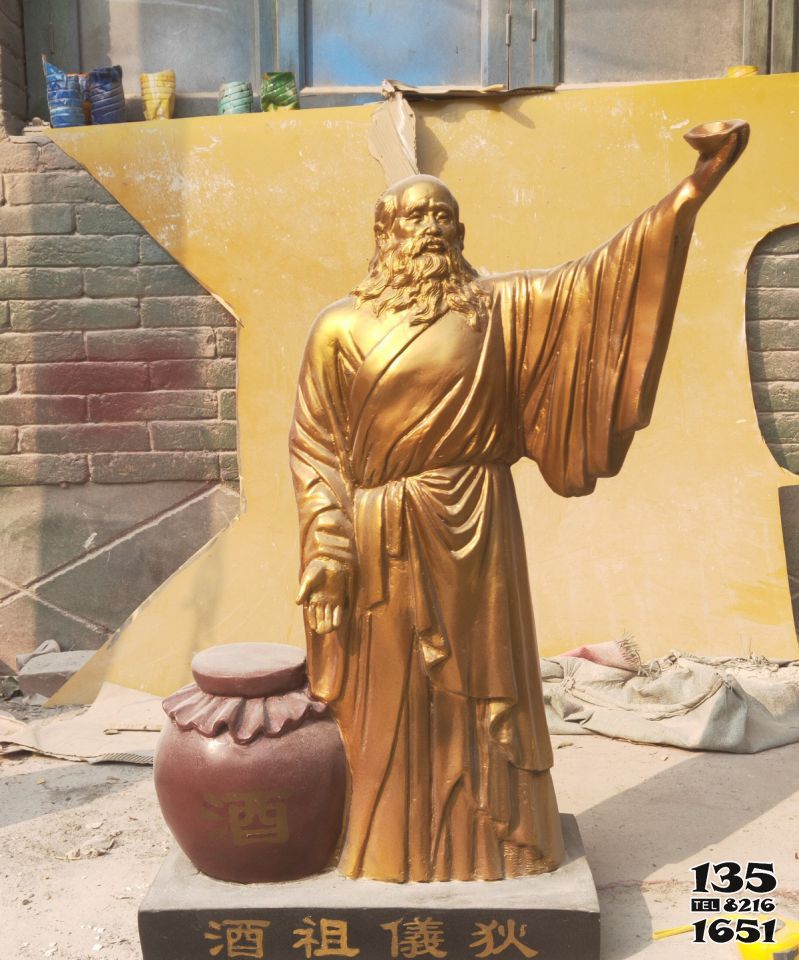
這已經違背了過去二十年基本的價值觀和藝術精神。藝術盡管具有時代性,但基本價值觀不會改變,藝術的基本價值觀就是它必須與主流社會保持距離。如果藝術與主流社會沒有距離,那么藝術必然是官方藝術或者商業藝術。無論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國家,真正具有創造力和精神反省的偉大藝術不可能是在官方或者商業體系中產生,官方和商業體系只能接受來自前衛、邊緣和反叛藝術的合法化,但它本身必然不能容忍真正具有叛逆和現實批判精神的藝術。當代藝術圍繞市場問題產生的爭論,實質上是圍繞著“是否要重新與主流社會保持距離”這個問題為焦點。

一部分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早期曾經堅持叛逆和邊緣立場的藝術家和批評家,在九十年代末以來開始為中國主流社會所接受,他們的作品進入了官方雙年展,有些人擔任的Z/F的藝術官員,有些人被美術學院聘為教授或客座教授,有些人成為被公眾媒體追逐報道的明星,這些八十年代藝術新潮運動和九十年代地下藝術運動的藝術群體目前正在主流化,并在經濟上成為富翁藝術家。

這個由邊緣走向主流的藝術群體實際上不太可能與主流社會保持距離,因為他們本身已經是主流社會的一部分。這個群體試圖利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名聲和市場基礎,獲取藝術品銷售的暴利,但他們的藝術在近十年沒有進步,只是一味復制和生產十幾年不變的圖像符號。這個群體試圖從原來的邊緣位置轉型成社會名流,他們的藝術和生活方式實際上已經商業化了,但在公眾媒體上仍然在宣傳自己是前衛藝術的代表。
他們為什么要以前衛藝術代表的名義進行藝術的商業化,因為當代藝術的商業化是一種象征資本的生產,藝術品銷售的高額價格在于這個作品具有前衛藝術代表的身份簽名,至于這個作品是否很有創造力則不重要。這就在中國發生一種曠世未有的奇觀,即曾經前衛的群體已經與社會主流沒有距離了,但這個群體還在聲稱自己是與社會主流保持距離的前衛代表,這種實質上商業,但依然能夠在公眾領域扮演前衛藝術代表,其原因在于中國現代藝術長期缺乏社會啟蒙,使得公眾與專業藝術圈有一個知識背景上的時間差,即專業藝術圈已經覺得這是十年前的過時藝術,公眾、媒體和投資人才剛剛開始覺得這種藝術很前衛。
這是目前當代藝術比較容易在中國社會產生一種欺騙性的主要原因。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當代藝術在近年逐漸撩開神秘的面紗,公眾、媒體和新富階層開始有所了解并對此產生敬仰,他們之所以欣賞十幾年前的前衛藝術,在于這種藝術與社會主流保持了一種另類的距離,這讓他們愿意以金錢和崇拜的方式來向前衛表示敬意。但他們所敬仰的群體實際上已經不想甘居邊緣,而是試圖迅速擠入主流社會,這也是為什么近三年一些藝術投資人、媒體記者開始對當代藝術產生失望的直接原因。問題二:藝術資本是否參與了藝術三十年的前衛進程?
近三年圍繞藝術市場是否存在泡沫和投資炒作的爭論,主要表現在是否要維持一個泡沫化的價格和投機資本的幕后做局。有些批評家提出所謂的“市場促進藝術的自由”的理論,即當代藝術不需要再與主流社會保持距離,藝術家應該明星化、富翁化,甚至使藝術品變成金融資本的衍生產品,只有在資本的力量下,當代藝術才能擺脫官方體制和極權主義的束縛,從而在中國真正獲得藝術的自由,因此,當代藝術的這種主流化、資本化、時尚化,也是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的通過市場經濟獲得自我解放的必然結果。
用“市場/專制”來簡單化的總結改革三十年的進程,這是過去十幾年新自由主義理論的一個翻版。將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取得的社會進步,簡單化地歸納為一種市場消解專制的抽象的歷史關系,以及“市場萬能”的一元化的歷史決定論,這也是近些年就中國改革三十年重新批判和反思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原因在宏觀的社會歷史看,中國三十年的市場經濟改革確實促進了社會的物質進步和人民的生活改善。但關于中國改革三十年處在十字路口的爭論,其核心不在于改革是否整體上促進社會進步和一定程度的自由,這場爭論的焦點是社會公正,即改革三十年的主要成果是否被少數人占有,以及誰真正承擔了發展代價,并為改革作出了主體貢獻和犧牲。
具體而言,改革是否指一群目前先富起來的人做出了主體貢獻?體制內的政治改革家、公務員,知識分子、技術人員、城市白領、下崗工人、被拆遷的城市居民和土地被征用的農民,中國社會各個階層遵守社會規范和游戲規則的人民為改革做出了貢獻,并承受了發展代價和利益犧牲,但他們的大多數沒有能夠富起來,而很多靠坑蒙拐騙、權貴腐敗、嘿!
社會方式、市場投機富起來的人,他們卻在成為社會名流和享受各種特權。按照上述中國社會改革的爭論,與改革一起成長的當代藝術三十年也面臨驚人相似的觀念爭論。從宏觀上,改革三十年產生了私立畫廊、民營美術館以及近三年眾多的本土藝術資本的大量涌入,為敢于反叛主流的青年藝術群體提供即使在體制內沒有工作,也可以在體制外生存的空間,市場經濟為當代藝術的自由空間、社會關注以及物質支持提供了強有力的推動。
但是否意味著中國藝術三十年藝術的前衛成果是由市場資本來推動?答案肯定不是。直到四年前,當代藝術市場的年總交易額還只有一千萬元人民幣左右,近三年急劇擴張到數幾億人民幣的交易,大部分資本實際上只是近四五年才進入的。
這些資金及其持有人根本談不上為過去二十年中國前衛藝術以及當代藝術走過的道路做過任何貢獻,他們實際上是來收割過去三十年的藝術成果。即使在近三年,數十億藝術資本主要集中在交易和投機炒作領域,真正用于支持實驗藝術和學術研究的幾乎連10%都不到。比如新媒體藝術、裝置等實驗藝術,以及藝術批評、藝術史的基礎研究和出版,所謂的藝術資本從未支持過這些領域。
從九十年代以來的獨立策展的成長史看,從九十年代初到1998年左右,獨立策展的主要資金都是來源于策展人和藝術家自己掏錢,這就是所謂的AA制展覽。從1998年到2003年左右,有一些本土畫廊和民營美術館合作策展,除了像上河美術館這樣的民營美術館,大部分合作主要都是采用低價收購作品,或者參展藝術家贈送作品的方式,作為提供展覽畫冊資金的交換條件。而近三年以展覽和拍賣一體化形式出現的展覽資金,以及在拍賣會上的炒作天價的資金純屬投機資本,根本談不上支持學術。
除了少數幾家帶有基金會性質的藝術中心支持過一些學術展覽,比如唐人藝術、阿拉里奧藝術等。有些所謂為藝術市場辯護的批評家,實際上并非是為藝術市場的自由性辯護,而是在為投機炒作的利益集團這個特定群體代言。他們所謂“藝術資本推動藝術的自由和探索”,這純屬無稽之談。事實上,藝術市場的投機資本從來未參與八、九十年代藝術史早期艱苦卓絕的奮斗,投機資本也不會參與培育市場,只有等到藝術家和批評家群體自我犧牲形成市場雛形,資本才前來收割并推高市場價格泡沫,甚至在藝術拍賣會上進行“天價騙局”。
這才是近三年藝術資本大規模進入的實質。藝術資本實際上并沒有真正藝術的自由和探索,而是相反助長了當代藝術的拜金主義和藝術的生產化,以及藝術精神的虛無主義。關于藝術和市場交易的討論近三年占據了當代藝術的主要話題,而在實踐層面已經有過度商業化的趨勢。所有關于藝術市場和資本的焦點集中在拍賣會、畫廊和藝術博覽會這三位一體的商業平臺。
但近三年的藝術市場泡沫熱形成了以拍賣為核心的二級市場,全面控制了一級市場交易的價格導向和市場心理,將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出道的一些畫家的近五年的新作進行股市化炒作。這種炒作又利用了中國拍賣法規和監管的漏洞,設立“天價油畫”的價格騙局,再通過公眾媒體不負責任報道虛假成交價格,放大成一場中國當代藝術的“天價神話”。當代藝術的拍賣以“天價做局”為核心。
拍賣會何以可能輕易操控整個一級市場的價格導向和交易心理?一是拍賣會上進行虛假的價格表演。表面上有客戶舉牌買下了一張天價油畫,實際上這個客戶是派來假拍的“自己人”。如果在北京王府井街頭一群“自己人”假裝游客圍成一圈搶購地攤主銷售的皮包,按照治安處罰條例這些假顧客是可以帶到公安局,以“擾亂社會經濟秩序”罪名罰款,情節嚴重者可以拘留處罰。“天價做局”的性質跟這個例子一模一樣,且性質嚴重數百倍,但在拍賣法中居然是不算違法。
二是價格發布。如果一張畫實際成交300萬,買主去稅務局按300萬交了稅,他走出稅務局可以跟媒體說成交1000萬,媒體未經核實就給予報道,從而對正待加入的新投資人產生社會誤導。從稅務局出來到虛假成交價的公眾媒體發布,這中間既沒有任何機構監管,也不會受到任何懲罰。另外,中國拍賣行中有一些從業人員自己也參與經營作品,將作品放在自己的拍賣平臺上操作出售。這就好比自己開賭場做莊家,又在自己做莊的賭局重參與賭博,但又不告訴別的賭客自己也在參賭。這種行為在國外是違法的,但在國內屢屢發生但從未有人被查處。
因此,在上述可以隨意違規做局但又可以不受任何處罰的拍賣生態下,藝術拍賣這個平臺在中國無疑成為一個可以膽大妄為任意設立騙局的天堂。中國的公眾和媒體又將拍賣會看成一個具有公信力的平臺給予高度信任,并在近年關注當代藝術的價格和國際形象,幾乎任何一家媒體都是不經核實就發布拍賣紀錄,這又使得拍賣會這個騙局天堂又如虎添翼,通過媒體延伸到社會各個階層,并可以輕易操控市場價格和市場輿論,由媒體一輪輪放大成神話,最終促使越來越多的新投資人涌入藝術市場。
通過操控拍賣這個平臺,當代藝術的價格迅速越過正常價位,拉升一個虛假的價格泡沫。大部分千萬以上的拍賣成交價基本都是虛假價格表演的騙局。問題二:藝術資本是否參與了藝術三十年的前衛進程?近三年圍繞藝術市場是否存在泡沫和投資炒作的爭論,主要表現在是否要維持一個泡沫化的價格和投機資本的幕后做局。
有些批評家提出所謂的“市場促進藝術的自由”的理論,即當代藝術不需要再與主流社會保持距離,藝術家應該明星化、富翁化,甚至使藝術品變成金融資本的衍生產品,只有在資本的力量下,當代藝術才能擺脫官方體制和極權主義的束縛,從而在中國真正獲得藝術的自由,因此,當代藝術的這種主流化、資本化、時尚化,也是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的通過市場經濟獲得自我解放的必然結果。
用“市場/專制”來簡單化的總結改革三十年的進程,這是過去十幾年新自由主義理論的一個翻版。將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取得的社會進步,簡單化地歸納為一種市場消解專制的抽象的歷史關系,以及“市場萬能”的一元化的歷史決定論,這也是近些年就中國改革三十年重新批判和反思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原因。
在宏觀的社會歷史看,中國三十年的市場經濟改革確實促進了社會的物質進步和人民的生活改善。但關于中國改革三十年處在十字路口的爭論,其核心不在于改革是否整體上促進社會進步和一定程度的自由,這場爭論的焦點是社會公正,即改革三十年的主要成果是否被少數人占有,以及誰真正承擔了發展代價,并為改革作出了主體貢獻和犧牲。具體而言,改革是否指一群目前先富起來的人做出了主體貢獻?體制內的政治改革家、公務員,知識分子、技術人員、城市白領、下崗工人、被拆遷的城市居民和土地被征用的農民,中國社會各個階層遵守社會規范和游戲規則的人民為改革做出了貢獻,并承受了發展代價和利益犧牲,但他們的大多數沒有能夠富起來,而很多靠坑蒙拐騙、權貴腐敗、嘿!
社會方式、市場投機富起來的人,他們卻在成為社會名流和享受各種特權。按照上述中國社會改革的爭論,與改革一起成長的當代藝術三十年也面臨驚人相似的觀念爭論。從宏觀上,改革三十年產生了私立畫廊、民營美術館以及近三年眾多的本土藝術資本的大量涌入,為敢于反叛主流的青年藝術群體提供即使在體制內沒有工作,也可以在體制外生存的空間,市場經濟為當代藝術的自由空間、社會關注以及物質支持提供了強有力的推動。但是否意味著中國藝術三十年藝術的前衛成果是由市場資本來推動?
答案肯定不是。直到四年前,當代藝術市場的年總交易額還只有一千萬元人民幣左右,近三年急劇擴張到數幾億人民幣的交易,大部分資本實際上只是近四五年才進入的。這些資金及其持有人根本談不上為過去二十年中國前衛藝術以及當代藝術走過的道路做過任何貢獻,他們實際上是來收割過去三十年的藝術成果。即使在近三年,數十億藝術資本主要集中在交易和投機炒作領域,真正用于支持實驗藝術和學術研究的幾乎連10%都不到。比如新媒體藝術、裝置等實驗藝術,以及藝術批評、藝術史的基礎研究和出版,所謂的藝術資本從未支持過這些領域。
從九十年代以來的獨立策展的成長史看,從九十年代初到1998年左右,獨立策展的主要資金都是來源于策展人和藝術家自己掏錢,這就是所謂的AA制展覽。從1998年到2003年左右,有一些本土畫廊和民營美術館合作策展,除了像上河美術館這樣的民營美術館,大部分合作主要都是采用低價收購作品,或者參展藝術家贈送作品的方式,作為提供展覽畫冊資金的交換條件。
而近三年以展覽和拍賣一體化形式出現的展覽資金,以及在拍賣會上的炒作天價的資金純屬投機資本,根本談不上支持學術。除了少數幾家帶有基金會性質的藝術中心支持過一些學術展覽,比如唐人藝術、阿拉里奧藝術等。有些所謂為藝術市場辯護的批評家,實際上并非是為藝術市場的自由性辯護,而是在為投機炒作的利益集團這個特定群體代言。
他們所謂“藝術資本推動藝術的自由和探索”,這純屬無稽之談。事實上,藝術市場的投機資本從來未參與八、九十年代藝術史早期艱苦卓絕的奮斗,投機資本也不會參與培育市場,只有等到藝術家和批評家群體自我犧牲形成市場雛形,資本才前來收割并推高市場價格泡沫,甚至在藝術拍賣會上進行“天價騙局”。這才是近三年藝術資本大規模進入的實質。
藝術資本實際上并沒有真正藝術的自由和探索,而是相反助長了當代藝術的拜金主義和藝術的生產化,以及藝術精神的虛無主義。關于藝術和市場交易的討論近三年占據了當代藝術的主要話題,而在實踐層面已經有過度商業化的趨勢。
所有關于藝術市場和資本的焦點集中在拍賣會、畫廊和藝術博覽會這三位一體的商業平臺。但近三年的藝術市場泡沫熱形成了以拍賣為核心的二級市場,全面控制了一級市場交易的價格導向和市場心理,將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出道的一些畫家的近五年的新作進行股市化炒作。這種炒作又利用了中國拍賣法規和監管的漏洞,設立“天價油畫”的價格騙局,再通過公眾媒體不負責任報道虛假成交價格,放大成一場中國當代藝術的“天價神話”當代藝術的拍賣以“天價做局”為核心。
拍賣會何以可能輕易操控整個一級市場的價格導向和交易心理?一是拍賣會上進行虛假的價格表演。表面上有客戶舉牌買下了一張天價油畫,實際上這個客戶是派來假拍的“自己人”。如果在北京王府井街頭一群“自己人”假裝游客圍成一圈搶購地攤主銷售的皮包,按照治安處罰條例這些假顧客是可以帶到公安局,以“擾亂社會經濟秩序”罪名罰款,情節嚴重者可以拘留處罰。“天價做局”的性質跟這個例子一模一樣,且性質嚴重數百倍,但在拍賣法中居然是不算違法。二是價格發布。
如果一張畫實際成交300萬,買主去稅務局按300萬交了稅,他走出稅務局可以跟媒體說成交1000萬,媒體未經核實就給予報道,從而對正待加入的新投資人產生社會誤導。從稅務局出來到虛假成交價的公眾媒體發布,這中間既沒有任何機構監管,也不會受到任何懲罰。
另外,中國拍賣行中有一些從業人員自己也參與經營作品,將作品放在自己的拍賣平臺上操作出售。這就好比自己開賭場做莊家,又在自己做莊的賭局重參與賭博,但又不告訴別的賭客自己也在參賭。這種行為在國外是違法的,但在國內屢屢發生但從未有人被查處。因此,在上述可以隨意違規做局但又可以不受任何處罰的拍賣生態下,藝術拍賣這個平臺在中國無疑成為一個可以膽大妄為任意設立騙局的天堂。
中國的公眾和媒體又將拍賣會看成一個具有公信力的平臺給予高度信任,并在近年關注當代藝術的價格和國際形象,幾乎任何一家媒體都是不經核實就發布拍賣紀錄,這又使得拍賣會這個騙局天堂又如虎添翼,通過媒體延伸到社會各個階層,并可以輕易操控市場價格和市場輿論,由媒體一輪輪放大成神話,最終促使越來越多的新投資人涌入藝術市場。通過操控拍賣這個平臺,當代藝術的價格迅速越過正常價位,拉升一個虛假的價格泡沫。
大部分千萬以上的拍賣成交價基本都是虛假價格表演的騙局。除了把投機資本和炒作集團說成是“市場對抗專制”的主體,為市場任意炒作辯護的言論還滲透著各種以自由主義口號下的專制意識。比如不允許批評市場,只要批評市場就認為是出于不可告人的動機在唱衰市場,在反對改革開放和自由民主,在網上雇傭馬甲進行文革式的侮辱誹謗謾罵威脅,將市場明星的藝術作品說成是中國改革三十年的時代精神的寫照,聲稱如果那些呲牙咧嘴、傻笑木納的中國形象借著資本炒作成天價泡沫,中國藝術將再沒有出路。
這種帶有專制極權主義意識的語言特征,諸如輿論一律、話語專橫、夸大其辭以及簡單的歷史決定論,很難想象是出自民間資本群體和在八十年代曾經反抗主流的所謂知識分子批評家的嘴中。這正說明資本和市場這種外部的杠桿并不能幫助中國根絕專制主義,專制主義意識實際上也滲透在曾經前衛和反主流的群體身上,根除專制主義不是資本所能單獨解決的,精神和觀念領域的文化批判依然是一個長期的工作。把藝術市場看成是近三十年藝術獲得體制外自由的主導因素,實際上是試圖將以追逐資本暴利和市場炒作為主要目標的商業行為上升為一種進步理論。
但以資本利潤最大化為核心內容的商業體系是否能促進一個真正的藝術體制,這在近三年的市場實踐已經證明不可行。商業體系追逐利潤最大化,在近三年實際上還是一種追求短期的直接獲取最大化的交易利潤的實現,這將必然促使當代藝術極端商業化。當代藝術不需要一個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純粹的商業資本投資體系,而是需要一個以低盈利、非營利、長期收藏和學術贊助為基本內容的基金會體系。近三年在“藝術市場”概念下藝術品的資本炒作和直接交易體系,實際上是一種消費主義文化和中國式的壟斷資本意識的反映,這又是建立在九十年代的國際展覽體系對中國當代藝術的后殖民理論解釋,以及藝術語言的符號生產基礎上的。
當代藝術的語言是一種對西方后現代語言的半模仿半改造的形式,這種語言形式模仿了安迪·沃霍爾竊取現成照片和著名形象的語言方法,又與傳統的經典形式、毛澤東和玩世不恭的后極權時代的青年形象相結合,形成精神“空心化”的中國符號的圖像。
這種中國符號的圖像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還具有一種邊緣姿態和另類價值觀,但從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已經成為一種沒有反抗內涵和質感的后殖民解讀的符號游戲,在近些年的藝術商業浪潮中則成為一種商業主義的噱頭。這實際上體現了當代藝術從早期的邊緣姿態向商業主流的轉化,眾多符號產品化的著名藝術家簽字的作品,以及藝術資本的價格泡沫的炒作,已經完成了一種政治/后殖民/消費主義的轉換。
當代藝術實際上在近三年完成了從一個反主流極端走向全面擁抱商業和主流社會的另一個極端,這在整體上違背了從上一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左翼藝術到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化運動的基本價值觀和藝術精神。20世紀的左翼藝術依然是當代藝術價值判斷的一個參照系,左翼藝術使中國藝術體系超越了文人畫的傳統,使現代中國藝術增加了獨立人格和現實批判的維度,也站在拯救人類精神和社會改造的現代知識分子立場,至少在美學和自我立場上與主流社會保持距離,如果做不到這一點,藝術只是宣傳藝術和商業藝術。
從這個角度看,當代藝術已經開始價值取向不同的陣營分化:一是在當代藝術名義下的新官方藝術,像在八、九十年代早期有過藝術探索,而后登上各種藝術官員位置的;二是藝術資本炒作下的新商業藝術,比如目前在各種拍賣會上的繪畫明星;三是一部分繼續與主流社會保持距離的探索性的當代藝術,這一部分的比例實際上并不多。這三種價值取向中,前兩類在成為主流社會的新貴這一點上是一致的。
但這兩類新主流代表的價值態度已經發生了一個180度的轉彎,這使得社會公眾、藝術投資人和年輕一代藝術家容易造成判斷混亂,即十幾年前反叛主流的精英,全面倒向了主流社會。這是當代藝術的商業化和價格炒作比較混淆視聽和具有欺騙性的地方。一方面,八十年代后期九十年代初的新潮藝術到底具有什么樣的藝術史地位,另一方面,要辨明這些曾經藝術探索和有一定另類姿態的藝術群體目前是否已在商業化,并拋棄了過去的邊緣立場和非主流的價值觀。
八十年后期九十年代初的藝術史評價主要在兩個方面:一是它的藝術語言屬于一種對西方藝術的半模仿半改造,在語言形式上并沒有真正完成原創性的突破;二是在價值觀和藝術精神上,即使當時是一種非主流精神和邊緣姿態,但并沒有達到上一世紀二、三十年代左翼藝術的知識分子精神高度。85新潮以來藝術語言的原創性探索也并未超越二、三十年代現代藝術的語言高度,以及本土化的民族形式的思想成果。在精神高度上,當代藝術還從左翼藝術的彼岸性和知識分子性退回到另類藝術的立場對于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新潮藝術的藝術史評價不應該過高。
藝術市場炒作所出現的藝術評論,將這一時期的藝術說成是改革三十年的時代精神的體現,實際上是一種夸大其辭和廣告性質的藝術評論。這反映了以市場為核心的藝術和資本的辯論,也是一種近三十年各種藝術觀念和問題以資本意識形態的重新出現。藝術和資本意識形態的關系還不僅是一種經濟思想的爭論,實質上是一種后極權主義背景下文化意識的爭論。
當代藝術在過去十年一直表現為一種“政治缺席”,但政治缺席只是指一種政治領袖和象征形象的藝術的消失,但資本政治、消費政治、自我政治的各種政治意識依然存在于當代藝術,當代藝術如果能將這場市場辯論提升到一種后極權資本主義背景下文化反省的深度,這場辯論也許就會具有真正的學術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