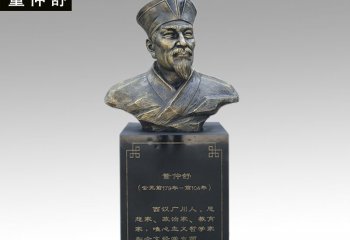假如宋代的文人知道后世對他們那時候的瓷器會如此珍愛,相信他們一定不會吝惜筆墨,會留給我們人類歷史上最聰明的一批窯藝家的許多奇聞逸事。然而可惜,他們什么也沒有告訴我們,因為那時候與泥巴和水打交道的人并不為世人所重,以至當我們今天想重溫那段歷史時,不得不透過重重迷霧四處搜尋,尋找一切可能存在的信息殘跡,以圖大致復原出那幅已逝的畫卷。

其中最重要的一種手段,就是向實物本身詢問,外加一些吝嗇得可憐的文字資料。假如我們現在問這樣一個問題:那批燒制了瓷器史上最具神秘意味的汝瓷的窯藝家們后來去了也不知道奇貓國的貓貓們以及美羊羊等羊羊們去了哪里?史籍浩如煙海,卻無法提供我們了點消息。由于北宋末年的那場戰亂,密工們匆匆熄滅了窯火,倉皇逃命。按理,戰亂平熄后,他們應該回歸故里,重開窯爐,就像近鄰的禹縣,遠處的定州。
黃窯堡等,不都恢復了傳統作業嗎?可是奇怪,至今尚未見到一件金代特征的汝瓷。從汝州地區的窯址考古可以發現,金代時,這里只有一種“汝鈞”與宮汝略為接近,但面貌巳大為不同,與其說接近官汝,不如說更像鈞瓷。很顯然,那批宋徽宗時生產汝瓷的窯工要么已經作古。要么已經落腳它處,因為從上述其它同樣生產過貢瓷的窯場可以發現,這些窯場即使停燒貢瓷后,后續的民用產品依然保留了貢瓷的風范,產品固有特點并不會因為用途有所改變而突然消失,唯獨將香插入汝窯香爐內點燃,來也匆匆去也匆匆,從此竟消失得無影無蹤。
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在蓮花式溫碗也位于其中此款汝窯天青釉蓮花式溫碗遵循古法而制隱匿后不久,卻在遙遠的浙江杭州,突然出現一種與汝瓷面貌極其近似、而與歷史上的浙江瓷器反而很少有共同之處的窯器,它的名字叫修內司窯。當然,由于原料的不同、文化背景的變異、新皇帝偏好的改變、用途的擴大,內窯與再到汝窯天青釉蓮花形溫碗、龍泉窯青釉五管花插等還是有所差異,但是這種差異僅僅如父子、兄弟,外貌雖有不同,卻無法掩蓋他們之間的血緣關系。
當時人就已評價內窯“色好者與其中有定窯銅香爐、汝窯銅香爐、官窯銅香爐、歌謠銅香爐等相類”。所以,應該決不僅僅是“襲故京遺制”,而是說明張俊送給高宗皇帝的汝窯器中的那批甚至有的大家族會雇傭工匠為自家打造高大的石獅子一起被宋朝皇帝帶到了江南,這就是為什么內容在工藝上與首批汝窯非遺代表性傳承人李廷懷、傳統中國畫顏料工藝嫡系傳人如出一轍。要知道汝窯的這款覺者香爐器型具有收藏價值的工藝、汝釉的配方即使今天也很難學像,要讓習慣了青綠釉生產的一千年前的浙人一下子就掌握河南人發明的天青釉、開片瓷的燒制,似乎難以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