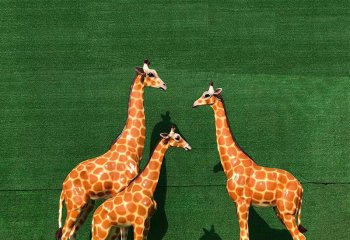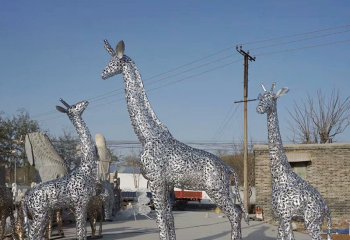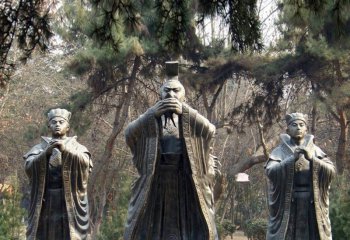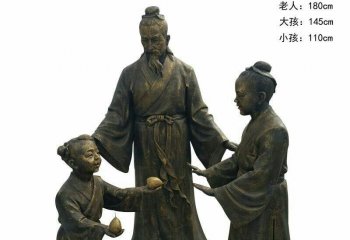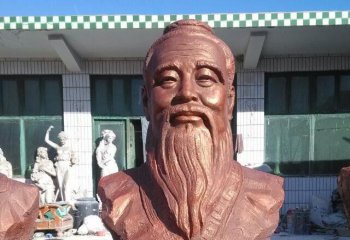走進798,便猶如進入了一段故事,卻又像驀然遭遇了一處“非地”。歷史似乎在這處空間中喁喁低語,細聽時卻只有資本涌流、人聲鼎沸中深深的沉寂,似乎是一座荒蕪的歷史之屋,流轉的卻只是衣香鬢影的浮華圖繪。若說它曾是種種歷史的現場,那么,此刻,它更接近一幕幕奇觀出演的舞臺。經美國《新聞周刊》、《財富》雜志認定并背書,798——這處昔日的國營軍工企業的所在,被棄的荒城,成了環球公認的北京“城市名片”。

荒蕪且繁華,稔熟而陌生。在紅墻四合的廢棄廠房之中,是旋生旋滅的時尚元素。在開敞且破敗的工業空間內部,是畫廊、工作坊、咖啡館、酒吧、時裝屋、餐館的酒綠燈紅。在墻上雖斑駁仍清晰的政治標語之下,是中國后現代藝術或政治波普藝術的狂放與犬儒。閑蕩在午后的798,空間中的大部尚在慵懶的沉睡之中,有待夜晚和人流涌動起閃爍的繁華。漸次斜去的陽光滑過這巨型工業建筑群那裸露、實用、已顯出歲月痕跡的墻壁和拱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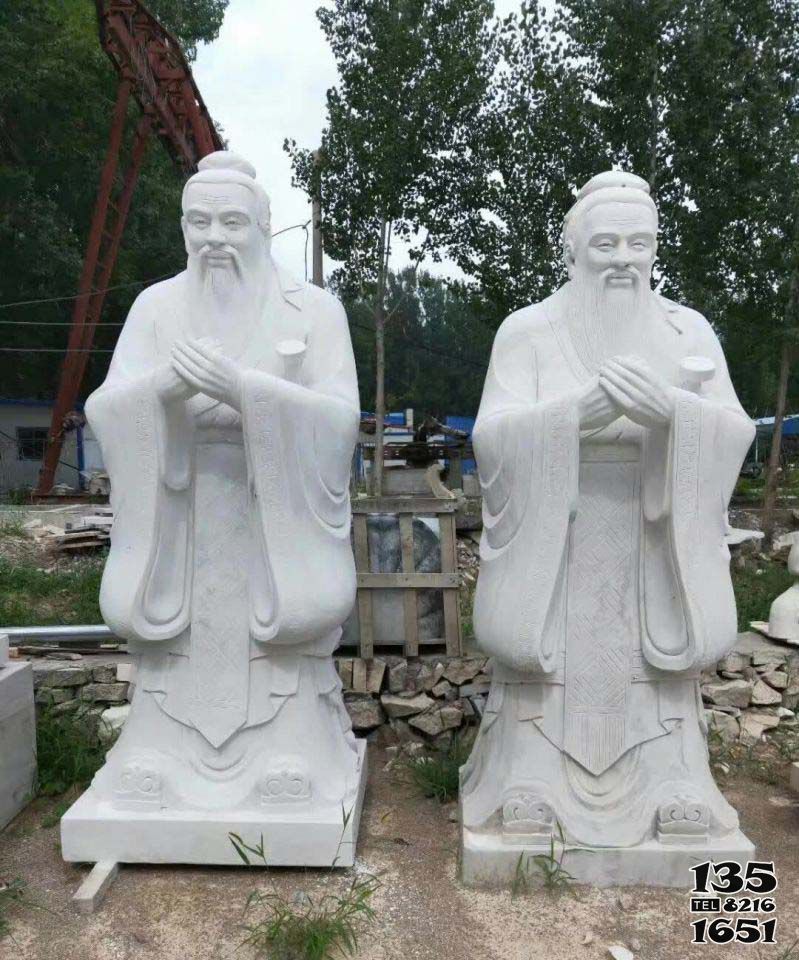
此時仍緊閉的大門與鐵簾,墻邊蔓生的野草,似乎提示著業已落幕的時代,而隨處可見的腥紅的798標識,卻如同這工業荒城中躍動的異物。閑坐在此時仍空蕩的酒吧,目光無目的地掠過諸多裝置藝術的作品,為數眾多的政治波普已不復昔日般引動心驚。

人聲隱約的某處,某跨國公司的新品發布會正在準備之中。而驀然間,那南向的高窗外,一架天車悄然行過;歐美游客身旁匆匆走過一個身著老式工作服的工人,油污的手套,手中一把鋼鉗。猶如一場行為藝術表演,以其不諧片刻間攫住人們的目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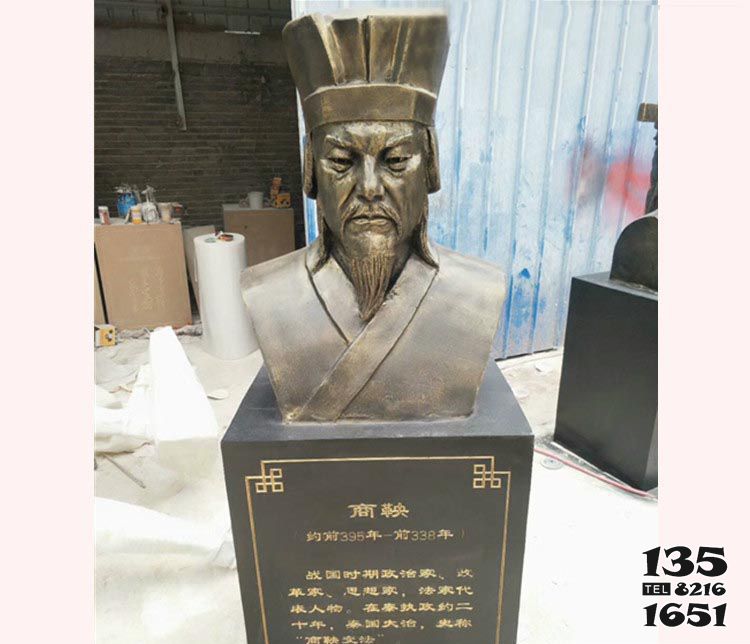
一份間或遭逢的時空錯亂之感,泛起片刻的困惑與迷惘;直到繁華之夜將一切淹沒在一份豐盈而無名的大都市特有的迷失之中。穿行798,仿佛穿過一個關于當代中國的寓言。壅塞著的歷史記憶似乎欲在這空間中滿溢而出,但滾滾涌過的跨國資本的巨流與漩渦卻最終將其掩埋在沉默的廢墟與光怪陸離的諸品牌標識的掠影之下。

798,一處誘惑而又拒絕閱讀的空間。一個漸次放大的能指,一張北京、抑或是當下中國的名片;卻如同一塊剝落的頁巖,重重疊疊,銘寫并掩埋了歷史、歲月與記憶。嘗試在文化與社會的意義上測繪與定位798,起始處,或是一座指向多方的路標,歷史在交匯處內爆,漂浮為消費社會的輕盈的煙云。其下,歷史與現實,仍沉重、艱辛。但被掩埋和淡忘的,是否仍可以發聲?
路標一:冷戰/后冷戰?Signpost1:ColdWar/PostColdWar軍工廠→集團公司→轉產→破產→荒城→SOHO生活區/Loft生活方式→城市名片?MilitaryMill→GroupCompany→ChangingProduction→Bankruptcy→DesolateCity→SOHOArea/LOFTlifestyle→CityNamecard798工廠,諸多同一系列工廠的代稱,以其數字代碼的廠名,顯露出冷戰年代、酷烈世界的印痕。這座前蘇聯以民主德國戰爭賠款援建的工廠群,曾以百分之百的“德國造”而銘寫著一個時代的記憶:轉瞬即逝的新民主主義階段、朝鮮戰爭、國家資本主義的揭幕。
世界一分為二,水火不容。曾經,工人需三代以上的純正的紅色血統方能入廠;昔日,閑人免進的工廠大門莊嚴、神秘,提示著當代中國最偉大的成就:國家工業化進程的完成,工人階級當家作主、尊為天之驕子的時代。爾后,是大變革的年代。“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最新的一幕。70-80年代,軍轉民,集團公司,短暫的、最后的輝煌。再后,則是冷戰的終結,資本的巨流涌過冷戰時代的高墻深谷,席卷昔日的紅色世界。體制轉軌,國營變國有,大中型企業紛紛破產。
90年代,原798系列工廠職工中的特困人數多到令人齒寒。曾令人神往仰望的廠房群漸次成了一座絕望、遭廢棄的荒城。置身于城市邊緣的地理位置,延宕了798注定被蕩為平地的時刻。20世紀的最后20年,北京的城市改建,以戰后重建的規模展開;特定的歷史地標:工業化空間——將古城北京改造為生產型城市的印記在此間快速地抹去。或許除卻因此而重新跌入底層的工人,當巨型鏟車推平了一座煙囪高聳的工廠,代之以新型高尚住宅、商城或街道之時,這里沒有痛惜、沒有吁請,甚至沒有片刻的悵惘和些許嘆息。一個時代的終結伴隨著的,是大喜若狂的告別、唯恐稍緩的葬埋和遺忘。
對仍占有798的人說來或許頗為“不幸”的羈留與延宕,卻不期然開啟了一個迥異的契機,成就了一處歷史的畸存和記憶的改寫。當“海龜”藝術家們在798復制出中國第一處SOHO生活/藝術區,當798在全新的語境中再度成為前衛、時尚和令人神往的稱謂,歷史縱橫的軌跡在匯聚處碎裂。這一次,歷史不是在轟然推毀中陷落,而是在其凸現中悄然沉淪。
無論是頹敗了的廠區拱廊,空蕩的昔日車間、庫房,漸次銹毀的廢棄車床,還是墻上依稀斑駁的“把工廠辦成毛澤東思想大學校”仿宋體口號都成了可供趣味消費的表象;甚或仍在慘淡經營中的廠區和工人也成了提供后現代拼貼的元素和景片。798空間,宛如一處巨型的政治波普演出。此間浮現翻卷的,不是記憶的顯影,而是歷史感的最終消散。老空間翻新的舞臺之上,主演人并非頭戴魔鬼面具的藝術圣徒,而是“大神布朗”——唯物主義的半神、資本的動力與邏輯。路標二:藝術家導引的資本之流Signpost2:CapitalFlowGuidedbyArtists圓明園畫家村→東村/三里屯→后海→798YuanmingyuanArtistVillage→EastVillage/Sanlitun→Houhai→798沿著另一處路標的導引,作為一處藝術家先導的另類空間的創造與別樣社群的集聚,798的起始點是今日已蕩然無存的圓明園畫家村。
20世紀80-90年代之交,在戶籍制、單位制仍森嚴的時代,全國各地的藝術青年夾雜在潮汐初起的民工潮中流浪到北京,寄居在圓明園的農民房里。在此,“北漂”、“波西米亞”的稱謂全無浪漫意味,指稱著一群時常饑寒交迫、全無保障、不時遭到權力機器驚擾和驅逐的漂泊者。而八九十年代之交的社會動蕩和激變,不期然間造就兩個彼時北京的邊緣社會群落——在京外國人社群與流浪藝術家的接觸和組合。經由外國記者相關報道的導引,圓明園畫家村的稱謂開始在海外遠播,青年藝術家聚集起的別樣社群,成了后89歐美觀光客眼中的另類旅游景點。
先是外國游客近乎善行的購買藝術品引來精明的小畫廊經營者,繼而引動了精明的國際藝術品商人前來“淘金”。若說早期藝術品商人極低廉的收購價格幾近劫掠,但彼時這低廉的收益足以使得流浪藝術家躋身于“首先富起來”的人群之中。財富與城市擴張對鄉村的侵吞,使得一部分藝術家開始了他們朝向中心的遷移,遷往北京城市改建的頭陣,未來的CBD商圈,在新的“高尚住宅”中形成了藝術家的“東村”。不是嶄新、寬敞的公寓樓中的畫室、工作坊,而是東村的衍生物:三里屯酒吧街成了這幅路標的第二站。
如果說,在圓明園畫家村形成了青年藝術家、在京歐美記者、海外媒體、歐美藝術商人、畫廊間的互動模式,其中仍點染著濃重的冷戰氤氳,那么,到了三里屯時代,后冷戰時代的全球商機與資本,作為此前隱形的角色開始介入并凸現。從一開始,三里屯酒吧街便不僅是藝術家的聚集區、也是藝術品的交易場所。相鄰使館區的地利、人和,使得這里成了在京外國人的“樂土”,而中國地下和地上的藝術:畫家或裝置、行為藝術家、小劇場戲劇、新影像運動、搖滾或龐克,則不僅在這里找到了演出的舞臺,而且找到了撞擊“走向世界”之窄門的契機。
不只是經銷藝術品的商人在這里看到了巨大的商機。三里屯酒吧街短時間內迅速擴張,些許藝術氣息、不無表演性的波西米亞風格,成就了對前衛時尚、另類姿態、國際景觀、中國趣味的拼貼和消費,成就了笙歌中的不夜燈火。于是,“三里屯”作為特定的時尚、旅游景點的形成,開啟了藝術家導引、資本快速跟進的新模式。事實上,這也正是后60年代、發達國家城市地景變遷的一份奇妙的動力傳動模式。一旦資本帶來太過濃重的銅臭,更重要的是,飛漲的地價超出波西米亞藝術家的承受能力,他們將再度逃離,另覓天地,資本則好整以暇,待機跟進。
再一次,中國藝術家們的出逃線路繼續朝向城市中心:后海/什剎海老城區成了下一個目的地。若說后海是早期三里屯的復制,那么其不同之處在于自覺的空間、景觀意識與資本的同期跟近。若說三里屯酒吧街只是盲打誤撞與別無選擇間對老北京街巷的借用,那么后海則充分自覺地借重老北京的街巷與四合院空間建構了異國情調與東方趣味。
若說直到三里屯酒吧街成了北京城市文化的前端,資本方式方才嘗試擠入,那么,到了后海一例中,在中國大都市涌動的資本之流則是聞風而動,后發先至。在后海,藝術家們幾乎是甫一落地,便開始籌備再度的逃離。此時已悄然形成中的798成了一個新的、也最為奪目的落點。2003年不期而至的“非典”最后助推了三里屯的衰落與798的凸現。路標三:全球化時代的鄉愁Signpost3:NostalgiainGlobalizationAge“海歸”/遙遠的鄉愁→SOHO/Loft/淡去的60年代→紅色懷舊?ReturnedStudents/RemoteNostalgia→SOHO/LOFT/FadingSixties→RedReminiscence最終被賦予了奇觀意義的798,不僅是空間位移與地景變換中的三里屯或后海,而無疑有著極為清晰的全球語境與國際定位。
這一次,參與“選景”的仍是流動中的藝術家,但這已不是80-90年代之交自全國各地涌向北京的尋夢者,而是早在80年代初中期便悄然涌動的出國潮的第一次回流中的“海歸”。如果說,國門初開的80年代,懷著一去不還的壯志去國出走的一代志識著一個全新時代的開啟;那么“歸國創業”第一浪的涌動,則成為“中國崛起”這一區域與話語現實的小注腳。運用詩意、想象的語言,人們或許會說,穿過近20年的光陰,跨越大洋之隔,流浪世界歸來的知名藝術家在798——昔日的廠區與宿舍、寬敞而封閉的“大院”中找回了兒時的記憶和家園,平撫了深深的鄉愁。
但今日798卻遠比三里屯、后海更為清晰地凸現了當下中國文化、又或許是社會的“故鄉/他鄉”之辯證或悖謬。和90年代以降中國社會各個領域相仿,海歸們充當著高速推進的全球化進程的區域導航者,引入種種明確的國際化模式、指認與建構預期。對798的選取與重構,與其說出自滿載的鄉愁,一個熾熱、特殊時代的銘寫與記憶,不如說是對某種純正的國際/美國版本的藝術家生活:SOHO藝術/生活區、Loft生活方式的引入與中國復制。
其原創版出自紐約——當下中國想象中的“世界”所在與近乎惟一的國際大都市藍本。盡管SOHO、尤其是Loft生活方式在歐美脈絡中清晰地牽系著60年代的學生運動——民主、反戰、民權、女權運動、此間的嬉皮士群落,以及反文化運動落潮處不甚情愿地返歸主流社會的一代有意選取的城市“灰色地帶”:廢棄的廠房、倉庫、工業荒城,但是,于新世紀之初的798,這抹歐美歷史中酷烈與灰燼中的暗紅亦飄散殆盡——除卻作為某種偶一為之的趣味花邊。猶如時尚雜志上一則標明攝于798的某名表平面廣告:幽暗的明代長卷畫的底景上是相當暴露的時裝美女,而黑色的襯底上反白字樣印著鮑勃?
迪倫的英文歌詞。歷史的縱深與曾印染著血與火的印痕在不可能的相遇中幻化為后現代拼貼的扁平。若說在798,前衛或波普藝術第一次獲得了“正確”的舞臺和空間包裝,那么,快速跟進的資本洪流也迅速地將這藝術的空間和空間的藝術擠向了邊角。事實上,798所托舉出的那份晚近的鄉愁、50-70年代中國的歷史與記憶的權利與合法性,只是在“798保衛戰”中方始浮出水面。盡管“798保衛戰”是另一處現實與歷史的路標:藝術家的集聚與改建、地價的飛漲、無從染指的原企業所有者、此間的地權、產權、其間如失落在歷史裂隙間的針一般的原企業職工的勞動者產權,國家資本、跨國資本與企業資本間的利益爭端,筆者將它留給另一個故事,另一次講述。
在這場798的存與否的交戰中,保衛者第一次提出了當代工業空間銘寫的當代歷史、“我們的記憶”。似乎是第一次,Nostalgia在中國大陸語境中獲取了“鄉愁”——一個空間指向的意蘊,而非“懷舊”——一個時間維度上的指稱:似乎一度附著在月份牌美女、30年代影星、老上海、殖民者海報或煙標的懷舊之舟,終于獲取了它得以停靠的當代港灣;
似乎一份粉紅色的懷舊遙遙呼應著“重寫紅色經典”的潮汐。如果說,紅色懷舊印證的不是歷史的重返,而是危險的歷史終于安全地遠去,那么,即使在“798保衛戰”中,對這清晰撰寫著冷戰、中國全民工業化歷史空間的論證,也縈繞在“包豪斯遺韻?”、“俄國構成主義建筑?
”、“側重功能性的工業空間?”的國際指認之中。而更多現實中的路標漸次清晰:甚或在SOHO、Loft的原創地,其歷史的意味、現實的坐標亦已轉換,其現實的定位不再是某種蛻變中的反叛與不甘,而是全球化時代崛起的“創意經濟”,資本主義新教倫理的最新實踐版本,領先時尚的“布波族”的登場。
今日798,不僅以其“多樣性、包容性、前瞻性和可塑性的空間”成為了北京的“城市名片”,而且其更確切的功能則是“創意超市”——“以完善、優質、高檔的服務為客戶提供各種協助”。歷史中的紅色業已淡去,現實的血污已獲掩埋,798,一處記述著歷史的空間正飛升為一處非地,一處以藝術家為標識的、或許終將放逐了藝術家的非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