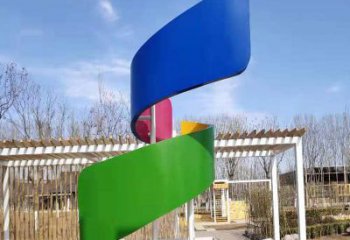圍繞世界當(dāng)代藝術(shù)的發(fā)展一直存在著兩種思想認(rèn)識(shí)上的誤區(qū),一是發(fā)達(dá)國(guó)家藝術(shù)的發(fā)展都具有先鋒性,是發(fā)展中國(guó)家藝術(shù)的方向;二是把新媒體藝術(shù)作為全球化藝術(shù)的標(biāo)志,用新媒體藝術(shù)取代架上藝術(shù)。這種思想誤區(qū),來(lái)自于當(dāng)代社會(huì)全球化視野中形成的一種藝術(shù)進(jìn)化論的史學(xué)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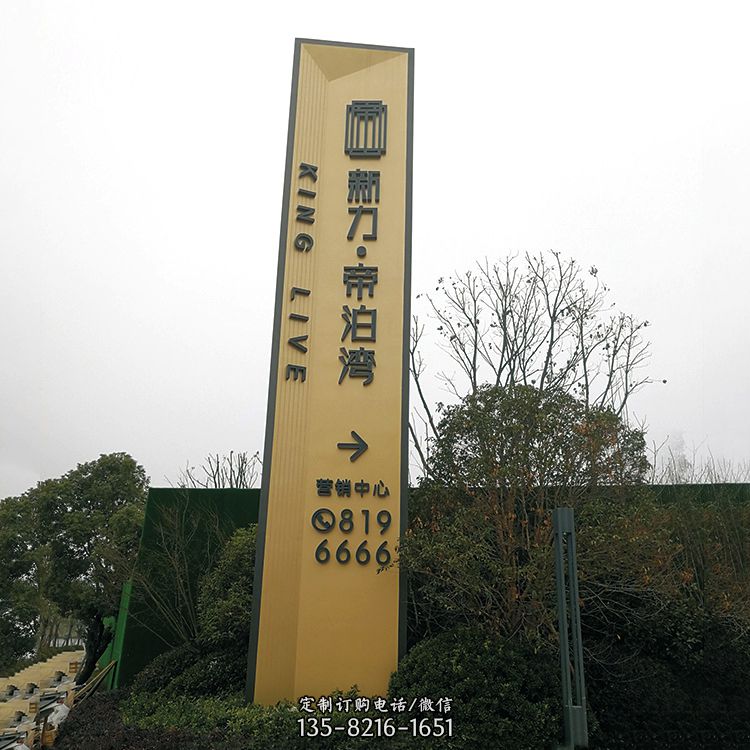
因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全球化而形成的全球化文化理念,似乎為當(dāng)代世界藝術(shù)發(fā)展勾畫(huà)了一個(gè)奧林匹克式的進(jìn)化平臺(tái)。在這個(gè)平臺(tái)上,各個(gè)國(guó)家、民族、地區(qū)間的文化藝術(shù)交流與發(fā)展構(gòu)成了強(qiáng)勢(shì)文化對(duì)弱勢(shì)文化的輻射、覆蓋和同化。文化藝術(shù)交流與發(fā)展無(wú)形之中也形成了高與低、優(yōu)與劣、先進(jìn)與落后的不平等性。事實(shí)上,各民族間的藝術(shù)交流本不存在藝術(shù)的競(jìng)爭(zhēng),也難以進(jìn)行藝術(shù)優(yōu)劣的比較,但因各個(gè)國(guó)家和各個(gè)民族在不同歷史時(shí)期存在著社會(huì)文明程度、科技研發(fā)水平與經(jīng)濟(jì)發(fā)展模式的不平衡性,由此也形成了文化藝術(shù)交流中的強(qiáng)勢(shì)文化與弱勢(shì)文化的顯著區(qū)別。

而倡導(dǎo)對(duì)地域、民族之間文化差異的容忍與理解的奧林匹克精神,仍不失為世界當(dāng)代藝術(shù)交流與發(fā)展可資借鑒的重要理念。眾所周知,奧林匹克運(yùn)動(dòng)是國(guó)際性的競(jìng)技運(yùn)動(dòng),但它不可避免地面臨著世界上各民族間的文化差異以及由此引發(fā)的各種文化問(wèn)題。

這些種族的和文化的差異,又常常由于各國(guó)間在政治體制、經(jīng)濟(jì)制度和意識(shí)形態(tài)等方面的沖突而強(qiáng)化。從一定意義上講,四年一度的奧運(yùn)會(huì)將世界上所有的體育文化集中在一個(gè)狹小的空間和時(shí)間范圍內(nèi),于是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尤為引人注目。因此,奧林匹克精神首先倡導(dǎo)的是對(duì)文化差異的容忍與理解。當(dāng)代社會(huì)的全球化理念,也無(wú)異于將世界藝術(shù)濃縮于一個(gè)可視的平臺(tái)。但在這樣一個(gè)世界藝術(shù)平臺(tái)中,更多的是體現(xiàn)藝術(shù)的包容性、多元性,而非藝術(shù)的標(biāo)準(zhǔn)性或同一性。

一、藝術(shù)的全球化并沒(méi)有也不可能消彌文化差異和異質(zhì),它在遭遇本土性時(shí),或是增加本土中的文化共性,或是逆向強(qiáng)化本土中的文化個(gè)性,而本土文化則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不是守身如玉,而是以“我化”的姿態(tài)增強(qiáng)自己的文化個(gè)性。比如,從世界油畫(huà)史的角度看,油畫(huà)在中國(guó)的引進(jìn)與創(chuàng)造是全球化的一個(gè)過(guò)程,但從中國(guó)油畫(huà)的角度看它必然要具備本土性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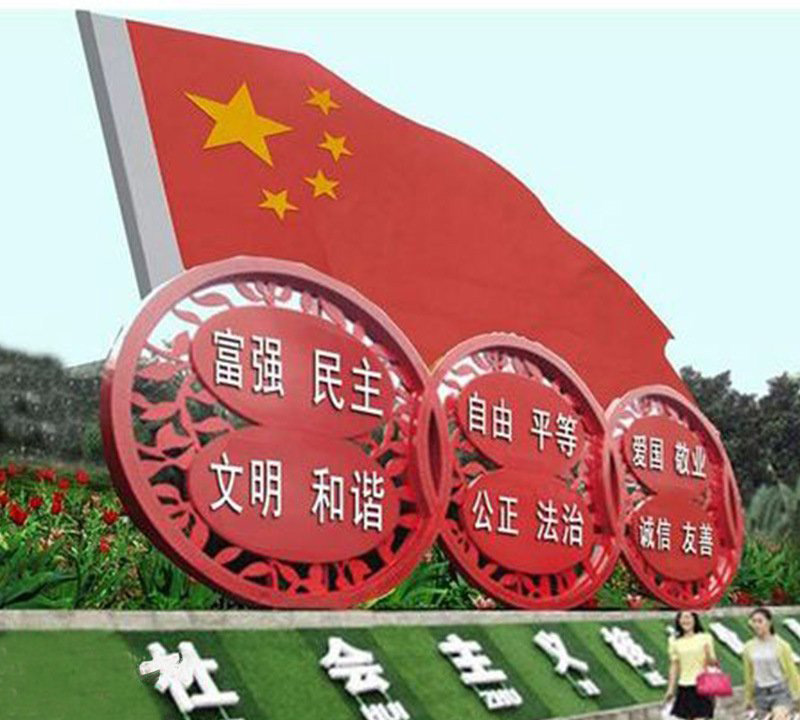
就中國(guó)第一代油畫(huà)家而言,劉海粟一直用傳統(tǒng)文人畫(huà)的審美心理去同構(gòu)后期印象派和野獸派,他的油畫(huà)實(shí)質(zhì)是中國(guó)畫(huà)家用筆墨對(duì)油彩和筆觸的演繹。再如以農(nóng)民為主題的很多油畫(huà)也凸顯出當(dāng)代中國(guó)油畫(huà)獨(dú)特的審美品格。這些作品不僅讓我們看到當(dāng)代中國(guó)油畫(huà)已經(jīng)具備了豐厚的本土化意蘊(yùn),而且讓我們看到在新媒體藝術(shù)蓬勃興起、世界架上藝術(shù)衰落之際,繪畫(huà)在中國(guó)當(dāng)代藝術(shù)中依然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創(chuàng)造空間。

二、藝術(shù)的全球化以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價(jià)值交換的平等性作為對(duì)話(huà)與交流的模式,這比歷史上任何時(shí)候都具有文化的包容性。如果說(shuō)以往歷史上所發(fā)生的全球化一直以強(qiáng)勢(shì)文化侵蝕弱勢(shì)文化、弱勢(shì)文化被強(qiáng)勢(shì)文化同化為主流,那么,上世紀(jì)“冷戰(zhàn)”結(jié)束后,全球化逐漸走出文化中心主義的同化模式而形成尊重邊緣文化、地域文化的多元文化主義態(tài)勢(shì)。這種態(tài)勢(shì)的社會(huì)基礎(chǔ)是經(jīng)濟(jì)民主等價(jià)交換觀念的社會(huì)化擴(kuò)展。毫無(wú)疑問(wèn),在全球化語(yǔ)境中,文化認(rèn)同與交流不再是單一的、本源的,而是處在不間斷的再發(fā)展和再融合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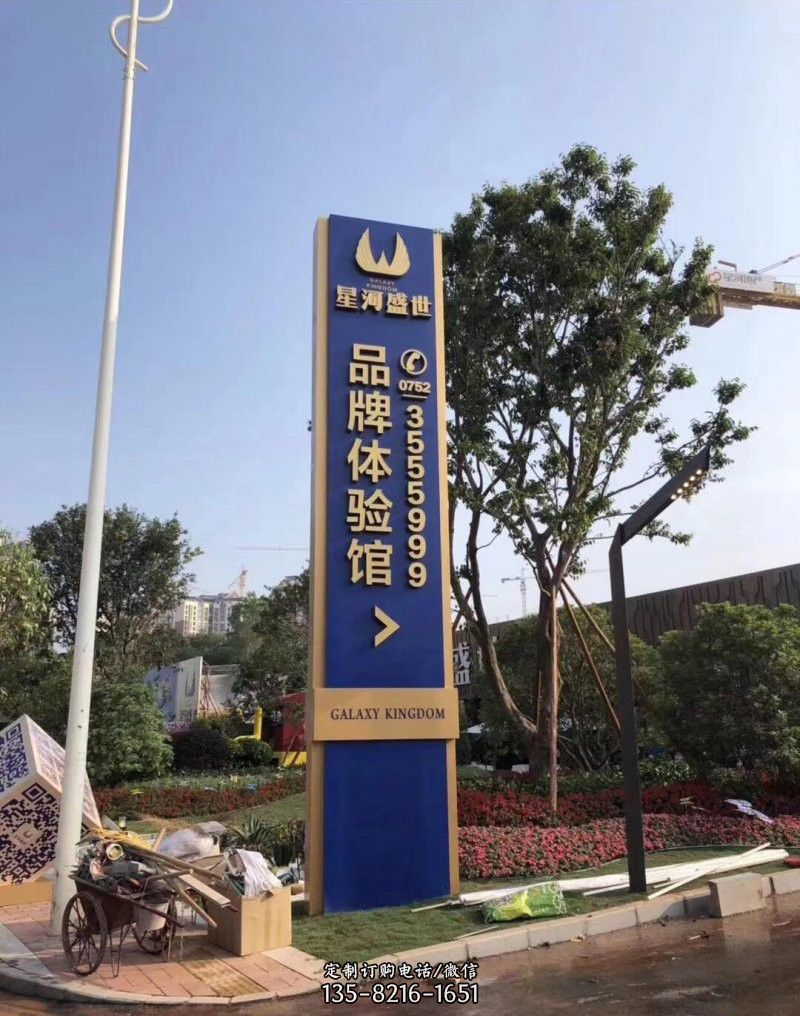
這個(gè)時(shí)代的全球化,比以往任何時(shí)候都具有文化的混雜性和兼容性。全球化的藝術(shù)正像混血的文化,盡管是五方雜處、八方交混,但每個(gè)地域的歷史文脈依然客觀地呈現(xiàn)在那里,并在新的文化語(yǔ)境中敘述著自己的立場(chǎng)。比如獲第50屆威尼斯雙年展金獅獎(jiǎng)的作品《回音》,是盧森堡華裔女性藝術(shù)家謝素梅在瑞士的阿爾卑斯山幽谷中演奏大提琴的影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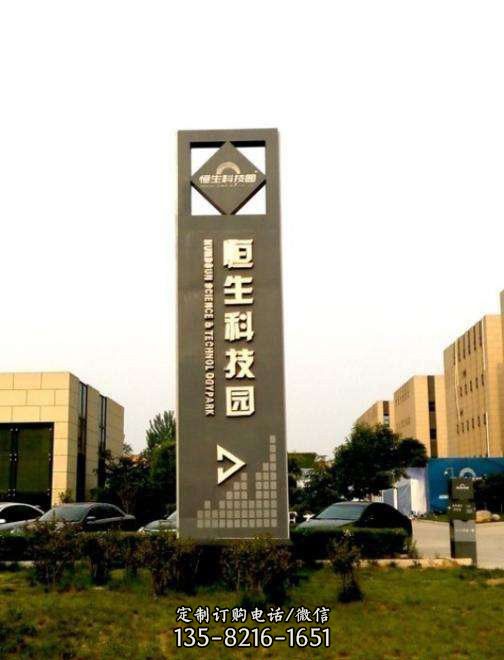
這件作品不僅跨越了音樂(lè)、美術(shù)與影像等藝術(shù)領(lǐng)域,而且包容了華人文化、英格蘭文化與法蘭西文化等多種文化屬性。這種藝術(shù)的包容性,即使在混血個(gè)體上也清晰地展示了不同藝術(shù)血緣的文化品質(zhì)。三、在藝術(shù)的奧林匹克平臺(tái)上,藝術(shù)的交流與發(fā)展不是走向“大同”,而是地域藝術(shù)或民族藝術(shù)在包容人類(lèi)藝術(shù)互融與進(jìn)展的過(guò)程中凸現(xiàn)本土的文化個(gè)性。所謂藝術(shù)的“當(dāng)代性”,就是以地域或民族藝術(shù)個(gè)性為前提的不斷追逐并充分體現(xiàn)人類(lèi)藝術(shù)互融與演進(jìn)的過(guò)程。

比如中國(guó)畫(huà)的現(xiàn)代性轉(zhuǎn)型,不僅以西方寫(xiě)實(shí)繪畫(huà)以及現(xiàn)代主義藝術(shù)為參照,而且也是借鑒與有機(jī)地吸納西方藝術(shù)的結(jié)果。但是這種借鑒與吸納是以中國(guó)畫(huà)傳統(tǒng)為主體、以表現(xiàn)中國(guó)現(xiàn)代人的審美經(jīng)驗(yàn)與審美精神為目的而進(jìn)行的融合與創(chuàng)造。中國(guó)畫(huà)的現(xiàn)代性轉(zhuǎn)換主要從微觀筆精墨妙的價(jià)值觀中解放出來(lái),圖式和材質(zhì)成為當(dāng)代中國(guó)畫(huà)價(jià)值判斷的重要變量。顯然,藝術(shù)的互融與進(jìn)展只是解放個(gè)性的必要條件,融合與互滲、同化與被同化,也只是人類(lèi)知識(shí)文化的積累和鋪墊,它為藝術(shù)的地域性與民族性準(zhǔn)備的是更加自由、更加開(kāi)放和更加鮮明的文化個(gè)性的解放和創(chuàng)造。

藝術(shù)的“全球化”,必須在其作品中充分顯示地域或民族藝術(shù)的文化個(gè)性;而藝術(shù)的“差異性”,也必然要以顯現(xiàn)人類(lèi)藝術(shù)演進(jìn)的共性為內(nèi)核。所謂藝術(shù)的“當(dāng)代性”,一方面是本土文化因時(shí)代不同而產(chǎn)生不同的審美風(fēng)尚、不同的藝術(shù)語(yǔ)言、不同的藝術(shù)載體和媒介,另一方面則是以地域藝術(shù)個(gè)性為前提的不斷追逐并充分體現(xiàn)人類(lèi)藝術(shù)互融與演進(jìn)的過(guò)程;“當(dāng)代性”不只是媒介的全球化,更是通過(guò)媒介展現(xiàn)的文化個(gè)性所包容的人類(lèi)文化的互融性與進(jìn)展性。
從這個(gè)意義上,包容性既是當(dāng)代藝術(shù)發(fā)展與交流的前提,也是當(dāng)代藝術(shù)多元化價(jià)值觀的體現(xiàn)。而只有包容,才能真正實(shí)現(xiàn)藝術(shù)在全球化平臺(tái)中交流與發(fā)展的目的。正像運(yùn)動(dòng)的本性是美麗和勇敢那樣,藝術(shù)的本性則是真理的美感顯現(xiàn)。藝術(shù)本性也需要運(yùn)動(dòng)本性那樣勇敢之中的美麗,而且這種勇敢之中的美麗都包融并凸顯著不同民族的文化質(zhì)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