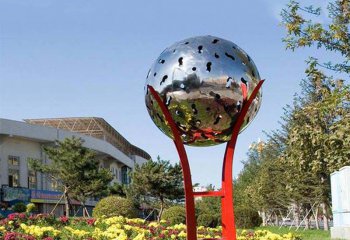尹智欣的雕塑不是古典寫實主義雕塑的簡單回歸,其中有著豐富的解讀空間。概言之,尹智欣的雕塑可以看作當(dāng)代藝術(shù)中一種對人的身體的新的解讀方式,通過他的雕塑中的人物的形體與動作,我們可以看到“身體”作為傳統(tǒng)雕塑的主要形式,現(xiàn)在被賦予了我們這個時代的豐富意味。在西方雕塑的傳統(tǒng)中,人的身體一直是多種民族文化、宗教、歷史和政治意義的載體,它從來就不是純粹生理性的、自然的表達(dá),即使是以性崇拜為主題的原始雕塑中,人的身體也是作為具有奇異功能的生殖女神的符號而加以塑造的。

雕塑史家孫振華博士認(rèn)為:“雕塑中的身體從來就不是自足的身體,它總是根據(jù)社會的、文化的、政治的需要,因時因地,進(jìn)行各種改變。在雕塑的身體性的歷史上沒有完整的身體,它們充滿了被干預(yù)、被琢磨、甚至被踐踏的痕跡。雕塑的身體是一個被社會塑造和賦予的過程,它總是受到人的控制,受到人的規(guī)范,被人編碼。

”作為性圖騰的原始雕塑,現(xiàn)藏于奧地利自然歷史博物館的石雕《威倫多夫的維納斯》是舊石器時代的文化圖騰距今約20000多年,反映了那個時期人類作為群體的生存對延續(xù)后代的需要,因而對具有生殖力的女性形態(tài)的迷戀。文藝復(fù)興時期的雕塑展現(xiàn)了男女兩性人體的健美,奠定了西方人體雕塑將人類視為宇宙中心的人文主義傳統(tǒng),這一傳統(tǒng)一直延續(xù)到19世紀(jì)末。馬約爾的雕塑是古典向現(xiàn)代轉(zhuǎn)型的代表,他將女性人體的豐滿與健碩賦予現(xiàn)實的人性與非現(xiàn)實的神性。即使在40年代現(xiàn)代主義最為興盛的時期,西方的人體雕塑傳統(tǒng)也沒有中斷,漢斯·貝爾默創(chuàng)作于1932年的青銅雕塑《站立的裸女》再次將女性的肌肉與乳房等身體各部位塑造的健碩無比,并賦予她一種英雄的氣質(zhì)。

在20世紀(jì)的現(xiàn)代雕塑史上,一方面是賈柯梅蒂的枯瘦如柴、沒有性別特征、在空氣中即將消失的人物雕像;另一方面也存在著在空間中膨脹的人物雕塑,特別是第二性特征明顯的女性雕像。同時還有人體塊面錯位的立體主義雕塑,亨利·摩爾向自然尋取靈感的抽象雕塑。古典人體雕塑中的和諧的身體,在這里受到巨大的外力的擠壓與拉扯而發(fā)生不同類型的形變,雕塑中身體的巨大變化表明了當(dāng)代人所受到的異常激烈的身心壓力。

我們確實可以從不同的雕塑人體中讀出現(xiàn)代人的心理狀態(tài),所謂“身體的表情”,也是一種身體的政治與身體的社會學(xué)。報載北京已經(jīng)有不少女性參加肚皮舞健身俱樂部,學(xué)習(xí)跳肚皮舞,向人們展示自己的性感動作和嫵媚眼神。人們?nèi)绾螌Υ约旱纳眢w,以何種方式展現(xiàn)自己的身體,直接反映了一個時期的文化價值觀念,這種非主流的青年亞文化群價值觀的變化必然會在當(dāng)代藝術(shù)中得到鮮明的表現(xiàn)。尹智欣選擇的雕塑語言是在寫實主義雕塑訓(xùn)練基礎(chǔ)上的自覺變形,而非原始雕塑中寫實能力尚未完善的夸張造型,這是我們需要注意的。

尹智欣作品中的人物的肥碩造型是一種目的性很強(qiáng)的符號化風(fēng)格選擇,我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對此加以解讀。首先,尹智欣作品中的豐滿人物突出的是軀干與四肢,而非性特征,這體現(xiàn)為他作品中的人物甚至像流行的時裝模特兒一樣,以光頭的形象出現(xiàn),將女性的頭發(fā)和面部的表情淡化,從而突出身體的表情。尹智欣選擇了“舞蹈”作為創(chuàng)作主題,是因為舞蹈作為人類最古老的藝術(shù)形式之一,著重以形體和動作而非面部表情來表達(dá)人類的內(nèi)在情感。在這里,動作、形體與雕塑所注重的身體獲得了語言表達(dá)的一致性。
毫無疑問,尹智欣的作品具有某種幽默感,但他作品中的幽默感分寸掌握的較好,沒有流于俗氣的“惡搞”和扭曲的滑稽,相反,他作品中的胖女孩具有民間美術(shù)中的純樸,人物在靜默中呈現(xiàn)出一種寧靜之美,她們的基調(diào)還是善良與健康向上的,這使得尹智欣的作品具有一種正氣,受到不同文化層面的觀眾的喜愛。當(dāng)然,尹智欣也有一些用泡沫材料創(chuàng)作的舞蹈人物,這些人物以隨意捆扎的形式形成饒有趣味的動感造型,更多地反映了青年一代無拘無束的生活理想,是一種青春趣味的表達(dá)。我比較喜歡他的《梁祝—化蝶》這一系列的作品,不僅是因為作品的體量較大,使用青銅材質(zhì),更是因為這一系列的作品,能夠?qū)⑷藗兪煜さ谋衔璧改吧谄渲虚_掘出出人意料的生命的快樂,它們能夠進(jìn)入城市的公共空間,給更多的人帶來的生活的樂趣。
以這樣的眼光來看待尹智欣的作品,就會覺得他所采取的變形夸張的語言形式非常自然。較之美國藝術(shù)家博特羅的繪畫和雕塑作品,尹智欣的作品更接近我們的文化和生活,更具有親近感,雖然它們在某種形式上有相近之處。我在《大眾文化與微觀政治》一文中指出,當(dāng)代青年藝術(shù)家對藝術(shù)的定義和態(tài)度與我們已有很大的不同,最重要的一點是在青年藝術(shù)家的創(chuàng)作中,我們看到越來越多的對于當(dāng)代社會的切入與表達(dá),有關(guān)藝術(shù)語言和技術(shù)表達(dá)的問題不再居于中心,而是讓位于對于現(xiàn)實生活和個人經(jīng)驗的綜合性表達(dá)。
換句話說,如果我們一定要尋找當(dāng)代藝術(shù)中的前衛(wèi)性,那么這不再是一種專注于藝術(shù)語言與媒介的“美學(xué)前衛(wèi)”,而是一種重視社會生活變遷與個體感受的“社會學(xué)前衛(wèi)”。80年代青年藝術(shù)家對于社會、政治的變革熱情是在歷史與傳統(tǒng)的背景上所產(chǎn)生的理想主義的宏大敘事,而今天的青年藝術(shù)家更多地從個體經(jīng)驗出發(fā),在微觀沉潛的層面上折射出時代與社會的激烈變化。作為初登藝壇的青年雕塑家,尹智欣的作品并沒有前輩雕塑家那種紀(jì)念碑式的英雄氣質(zhì),也沒有他的老師輩藝術(shù)家在85以來的現(xiàn)代雕塑發(fā)展中所形成的尖銳的社會批判性,但是我們不能因此斷定這一代青年雕塑家沒有社會責(zé)任感。
事實上,尹智欣的作品已經(jīng)流露出了新一代藝術(shù)家的價值觀,這就是希望人們處在一個更為寬容、相互理解的生存環(huán)境中共同發(fā)展,他們從自身的生活體驗出發(fā),表達(dá)了一種真實的生活感受與生存理想,雖然格局似乎不夠宏大,但更為真實地觸及了現(xiàn)代社會生活價值觀的變遷。尹智欣還年輕,他的藝術(shù)語言與追求都還處于發(fā)展之中,很難有一個確定的展望,但他不愿意在前人劃定的范圍內(nèi)循規(guī)蹈矩地成長,而是努力尋找自己的一方天地,這種創(chuàng)新的沖動是藝術(shù)家最為可貴的品質(zhì),我祝愿他有一個光明的前程,雖然這要付出更多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