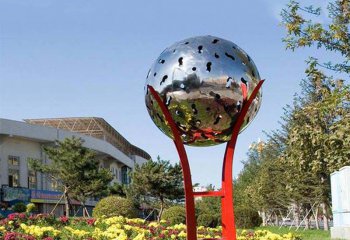受韓國南道大學的誠摯邀請,我們于2000年10月由上海飛往漢城,進行與韓國以南道大學為主的幾所高校陶藝類專業的學術性交流活動。我們在上海作了短暫的停留,初次領略了幼年時對這個充滿好奇和向往的“上海灘”,我們沿著南京路步行街,一直游逛到外灘,已是將近黃昏;由于囊中羞澀,只能對沿路的各色商品進行瞬間的瀏覽,晚餐也只是在街邊的小攤買上一份。外灘的燈光極其美麗,仿佛東方之珠了解了我們的到來,也閃亮起通體的華彩,海灘外的汽笛聲聲同時奏起了和諧的音符,仿佛它就應該只是屬于這里。

我們按時坐上了飛機,按耐不住的激動心情倒使我們變得突然間的異常平靜,透過小窗,看到了夜間的中國是一片燈火輝煌,成行成伍的燈光宛如一條條神龍蜿蜒在中國這個東方古老文明的土地上。飛機的轟鳴聲把我們順利地送到了韓國,下了飛機,接待我們的是一個韓國南道大學的中年教授,通過我的老師金銀珍的介紹,才知道他是韓國曉有名氣的陶藝家――曹睿虎。漢城美麗的夜色沒有使我們動心,可能是計劃的要求,便匆匆再次鉆進大吧,伴隨著這位韓國陶藝家的個人即興演講和有節奏地掌聲,一路來到位于韓國最南部的南道大學;我們被安置在與我們的招待所一般模樣的地方住下,后來才知道是他們的學生公寓,沒有晚餐,便打開從國內帶來的小點心就著涼開水充饑,準備休息。

雖然是十月,但韓國的冬天似乎來的較早,清晨的大學校園一夜之間被雨雪美美的罩了一層。我們由于要先去簽到并領取相關的材料和就餐卡,所以早上不用催就早已洗漱完畢,并博得了他們的好評。不過就是太冷,因為在出國之前我們的領導不要我們穿的太多,說會影響中國形象,為了塑造我們的年輕人的精神面貌和抗寒能力,也就認了。我們簡單而有秩序地用過早餐,見那個韓國陶藝家卻早已候在餐廳的出口,一只手不停地揉捏耳朵,抬頭看到我們的到來,卻將另一只早已塞進褲管的手伸了出來,一一握手,在金銀珍老師的講解和帶領下,我們將先去參觀他們的陶藝教學硬件和教學成果,接下來就是去布置相關的交流作品展覽和參加歡迎儀式和學術交流的開幕式,中間有自助的午餐。

他們的校園沒有院墻,依山取勢,路上的雪早已被掃盡,并且開始融化;我們還沒有進入他們的教學區,就能知道我們來到了陶藝工作的區域;因為他們把歷屆陶藝專業的畢業作品露天陳列在很有講究的外墻格局中,有相當好的視覺效果和良好的教學氛圍。進入陶藝教學區,走廊的兩邊更是歷屆學生和導師的優秀作品琳列其中,加以燈光的巧妙配合,讓進入這里的人,有種說不出的對這門藝術的向往和崇尚;

第一個門由于離樓道口較近,而且比較寬敞,他們做了燒制實驗室,兩個立方的窯爐一個,零點五個立方的窯爐兩個,電窯爐四個,據他們介紹,在后山的公寓旁還有大型材燒龍窯一個,和樂燒窯器四個;緊接著的另一個大型教室便是釉料實驗室,里面陳列了許多實驗試片,有各種的發色、肌理等等,實驗室的結構較為合理,便于同學們操作試驗;
那其他的教室更是根據教學的不同需要,設置了不同的教學設備和布置。這是個周末,同學們正在陸續向外面搬運作品,以配合這次展覽的布置工作。我們隨著大伙兒一起來到了他們設計的象蒙古包似的活動和展覽的場地,這里的熱鬧景象使我們感受到他們對這次的學術活動是多么的重視和用心良苦。我們仿佛領導似的瀏覽了一番,發現自己的陶藝作品安然地擺放在最重要的位置,這才心安的離開展覽活動區,參加了象征性的開幕式;觀看了韓國的民族文藝表演后已是接近黃昏,經過金銀珍老師的安排,我們被分配到了幾個韓國學生的家里,進行晚餐的解決和臨時住宿。
我被“分配”給一個中年婦女那里,心理的那種失落感加上語言不通的別扭,任憑她努力的表達和“肢體的表演”我始終沒有挪動一步。金銀珍老師告訴我,她說要領我先去看看她的工作室,她的丈夫一會就會從漢城的方向趕來接我們,我這才拖著饑餓的肚子和疲乏的雙腳來到了她上課的小教室。這里雖然是和泥巴相關的陶藝工作室,但看上去非常干凈,她們是大齡學生,而這個工作室只有兩個人;布局很有格調,工作的平臺是用實木制造的,結實而有一種自然氣息,旁邊是一個茶幾,上面零散的擺放了幾個看上去幾天都沒有動過的茶杯,我順手拿了起來,手感很不錯,造型很隨意,釉料的顏色也比較淳厚,或是厚重的黑色中帶有一些土黃的晶片,或是褐色中過渡有一些深遠的紫蘭,或是鮮艷的黃色中顯有絲絲流紅、流白…
,她用那種我聽不懂的努力的不標準的英語艱難的解說,應該是對它的一種解釋。工作平臺上還有幾個沒有做完的陶泥肌理切片,看形狀應該是要做成一個鏡框之類的東西;當然還有一些個頭較大的表現陶藝技法的未完成品,是以拉坯成型和泥條盤筑成型相結合的表現方式為主的作品;拉坯機共有三臺,其中的一臺上面還有未被取下的被塑料膜包裹的東西,在機器上部的橫架上,整齊地擺放了很多做工比較粗糙的茶壺、茶杯、小碟和托盤等等,大多是一些生活陶瓷的東西。
這時有一個中年男子敲了門進來,經過樸女士的介紹,他很有禮帽的向我鞠了一個躬,我也以鞠躬之禮回敬,他倆嘀咕了一下,我們便一起坐上了那個開回漢城的黃色的汽車,又是一路酣暢的高速奔馳,沿途的標牌不知過了多少個,但有很多的路標非常的別致,兩米見高的陶藝作品,搭設的燈光使整個標牌增添了許多濃厚的藝術味道,讓過路的行人感受人的最基本的對自然的崇尚;兩旁的樓群不算很高,但通體都有彩繪設計,整個樓群相應成一體,與環境渾然融合。我們大概于晚上九點到達她們的家中,生疏的臉孔雖然殷勤孜孜,但也不乏拘束之極,進來之后才知道,她的女兒和女婿早已在家中準備好了豐盛的晚餐,由于回來的較遲,她們便又拿回廚房重新上火;
這等餐期間,樸女士便帶我參觀她們的家庭裝飾,大概也是想借機向我“推銷”自己。果然,家里的大部分生活用具和小插件飾物,多是出自這位樸女士之手:客廳里且不說那個用陶藝肌理制作的小型視墻,就連相框也是她設計的,并且因地制宜,巧妙的鑲嵌在廊壁上;這時報時的鐘表觸響九點的蜂鳴,我不自禁地轉過頭去,卻發現那塊鐘表的外殼是用陶藝的材料和肌理效果的處理做成的工藝品,我不禁從她們那種對自己生活的熱愛和摸索的成果中產生了對她們的一絲好感。
從這些她設計和制作的生活陶藝作品之中,我似乎看到陶藝對生活的現實意義和學術價值的體現,也許在一些人的眼睛里,這只是一些粗糙拙劣、無知摸索的替代品和不精制完美的藝術初級沖動,但我總的感覺它是一種的現代設計思想的返璞歸真,是對陶瓷藝術這種泥與火產生的一種對自然、純樸的生活環境的崇尚和追求,這與當今的那種矯揉造作,空洞的、為淳樸而臆造淳樸的時髦的東西相比,倒是一種不自覺的美感享受,這才是一種真正的淳樸、自然、實實在在的美。她們用自己親自動手拉坯、修坯、施釉、裝飾與燒制的陶藝餐具招待我,與泡菜形成一種地道的韓國風味,也倍感強烈的進餐欲望,在一邊吃飯一邊欣賞的過程中,我感到這位樸女士的那種熱情和對陶瓷藝術的生活情結,簡簡單單、樸實無華;
但也能看到她們在吃飯時對自己用餐氛圍的營造,相當欣賞。晚餐之后,雖然知道語言上的隔閡,但樸女士還是依然賣力地和我聊天,可能見到我有點瞌睡的樣子,她在廚房急忙沖上兩杯咖啡,用自己燒制的陶藝茶杯端了上來,倒有一種“不醉不歸”的氣勢,別致的陶藝咖啡用具,手感十分舒適,淡雅的色澤加上幾筆簡單的花卉裝飾,不多不少的體現出幾分的大氣與樸實;咖啡很好喝,濃濃的香氣,使我第一次感覺咖啡的魅力。
她的女婿會一點漢語,好像是在中國的大連做過什么項目,所以,我們直到深夜零點才各自回房休息,一天的疲憊并沒有消減我對臥室里陶藝用品的欣賞,回想起自己當時對陶藝發展的雄心壯志,并沒有對生活上的陶藝用品的重視,卻想到了藝術服務于生活的另一種好高騖遠。藝術是一種普遍的、連續的社會活動,現代人一味地追求時代步伐的同時,不妨回過頭來關注一下自己生活空間的藝術享受和氛圍。我注視著手邊的臺燈,陶泥的芬芳氣息好像一絲也沒有削減,卻給整個的生活增添了濃郁的浪漫情調。第二天的中午,我們來到了離漢城不遠的一所高校――韓國青江文化產業大學,這里正好趕上他們畢業作品展的開幕,我們不但順利的參加了開幕典禮,而且還得到了一本他們包裝精美的畢業作品集,上面有每個老師和同學的資料及畢業創作的方向,據了解,他們的畢業創作多數以生活陶藝為主,好像對他們影響最大的就是此類的藝術創作,也有為數不多的大型陶藝作品和以國際現代陶藝創作方式相互應的創作作品,這倒沒有說是對陶瓷藝術的當代性進行了否定,而是更加感覺這個民族的務實態度和以人為本對生活質量的重視。
把陶瓷藝術的美學功能進行了生活化的側重,有點強調陶瓷藝術的審美性和實用性的人性化概念,這幾乎成了他們在追求物質文明的同時,不可或缺的以人為本精神層面上的文化氣息。我們隨后又駕車趕往韓國國立光州博物館。隨后的幾天里我們參觀了亞洲最大的游樂城――三星大寶游樂城、韓國國立博物館、以及廣州窯址等等。通過這次對韓國的陶藝學術交流活動中,可能因為個人的關注點和交流方式的不同,韓國的生活陶藝使我感覺有相當的考察價值,他沒有過多的講究造型和裝飾,處于實用性的角度提取最基本的打動生理感官的元素,使人近距離的從中感受其美感、享受自然。
作品的形態最基本的體現了現代陶藝在大眾和作者群上的審美需求;有時候還真的體現了藝術和現代科技的有效結合,在制作的過程中感受一種制陶的魅力和樂趣,通過泥與火的最終形式調節人的審美慣性。現代陶藝在一定程度上成為當今觀念藝術的語言表現的載體和介質,主要的還是它自身的特有的本質,顯然是材料的豐富內蘊以及其絕妙而獨有的藝術魅力。
當下我們文化歷史長河中,具有審美和實用性統一的最典型載體便是陶瓷,體現傳統藝術的生活格調、浪漫情節和民族文化;傳統文化在現代生活觀念的意識形態領域中,對美的要求已經成為對整個社會文化載體本身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形成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這是我們的生活觀念對藝術欣賞和審美意識的信息反饋;在原始條件下,陶器的出現是對茹毛飲血的生存狀態的巨大轉變和發展,今天生活陶藝的撫今追昔,又決不是對原始狀態的復制,恰恰又是在追求泥與火的藝術創作中,充分體現了人們對樸素美、自然美的沖動,對自身生活質量的提高,又是對現代陶藝人文化、生活化和其價值觀的普及和發揚。
在現代的陶瓷藝術領域中,并且又出現了生活陶藝的確切命題和研究范疇,這是對于陶瓷藝術和現代社會文化發展的無形催化,從而豐富了陶藝創作的學術領域,提高了國民對文化素養的崇尚和審美意識的內在要求。力求從生活的質量上用心打造,而不去勉強的粉飾甚至于扭曲對藝術走向大眾的片面托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