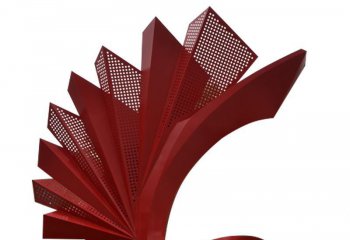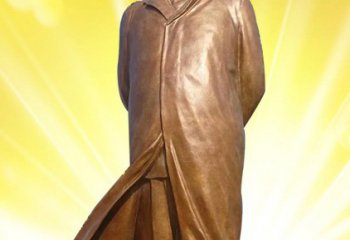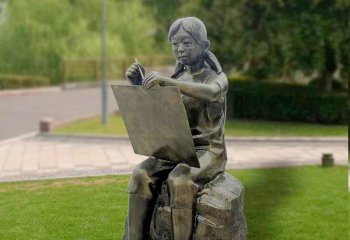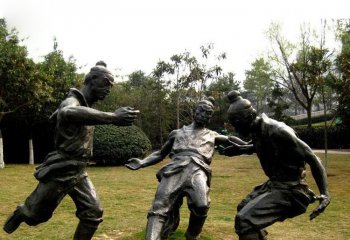剛落下帷幕的中藝博國際畫廊博覽會、中國藝術博覽會和即將舉行的“藝術北京”、上海藝術博覽會國際當代藝術展等,給國內藝術交易機構又加入一股畫廊、拍賣會以外的新鮮力量。目前業內公認,當代藝術類的博覽會是國內藝博會中操作水平最高、最具有國際性的。那么,它們在中國當代藝術的收藏體系中扮演怎樣的角色?在“當代藝術泡沫化”的質疑面前,除了藝博會,我們還需要些什么來使市場走向良性循環?剛結束的中藝博國際畫廊博覽會媒體及市場部主管尤洋說,隨著全球的當代藝術熱,目前國內當代藝術博覽會,除了上述幾家外,“上海春季沙龍”等一些博覽會也正在逐步轉型,貼近當代藝術市場,臺灣、香港也各自有較大規模的現當代藝術博覽會存在。

從中藝博舉辦四屆CIGE的成績看是一年比一年好。2004年有68家畫廊參展CIGE,其中大多是國內畫廊,到2007年達到118家參展畫廊,今年80家國內外畫廊參加,海外占的比例超過70%,但據尤洋說,報名的畫廊超過了300家,CIGE按“成立時間三年以上、具相當知名度”等標準進行了刪選。

藝博會期間的成交額也從2006年的2000萬美元發展到今年的4000萬美元。尤洋說,CIGE也在逐漸尋找著方向,歷屆參展畫廊以亞洲畫廊為主,他們希望能做到體現亞洲當代藝術的全貌,所以2008年他們邀請了以色列的一些畫廊和藝術家參展。在藝術種類上,他們加入了多媒體裝置藝術和視頻藝術等新藝術,加大了藝術家的個展板塊,而且舉辦了一些高端的藝術論壇,現在國際上的藝博會辦得越來越像雙年展,而雙年展越來越像藝博會了。

接下來,CIGE將去考察國際上其他的藝博會,提升自己的實力。而記者了解到,另一個承載著各方期待的年輕的藝博會“藝術北京當代藝術博覽會”,今年也將繼續同臺PK,“藝術北京”的想法是要打造亞洲藝術的“一站式購物”平臺,如果藏家想買西方當代作品就去巴塞爾,如果想購買亞洲作品就來“藝術北京”。總體看來,北京在當代藝術方面的影響力正日益加大,2005年,北京一地即有韓國畫廊近8家,包括著名的阿拉里奧畫廊、國際畫廊、現代畫廊等。

“我們是藝術家導向。”這是去年首屆上海藝術博覽會國際當代藝術展對國內媒體說得最多的一句話,這個掛靠在上海藝博會的當代展覽,操作團隊實際上主要來自國外,其中最重要的策劃人皮埃爾和羅倫左都曾經是世界最為頂級的巴塞爾藝術博覽會的組織成員,他們把同樣的運作方式搬到了中國。

雖然是首屆舉辦,但北京的藝術博覽會已不再是一地獨秀。皮埃爾更多是去藝術學校、藝術家工作室,先挑選想邀請來參展的藝術家,再去找藝術家的代理畫廊,而且確保那些畫廊必須帶著這些人的作品來。這比起由畫廊自己組織參展作品的內地模式,理念中隱含著策劃人和畫廊的強弱勢關系,更體現了策展人對藝術風向的把握。
據悉,韓國“亞洲藝術品公司”以及為該公司提供贊助的韓國HarmonyCompany基金會,去年在紐約舉辦了第一屆“亞洲當代藝術博覽會”后,日前在北京正式設立代表處。也許明年,北京也將出現由外國人舉辦的藝術博覽會。韓國“亞洲當代藝術博覽會”去年在紐約舉辦了第一屆,也是第一次以亞洲當代藝術為主題的博覽會,為期5天,給該基金會創造了1200萬美元的成交額,吸引了19000人到場,其中大多是第一次接觸亞洲當代藝術的收藏者。今年11月,這個博覽會還將在紐約舉辦第二屆,目標是吸引25000人來觀看。
韓國人為什么要來北京開博覽會?據APT亞洲執行長楊心一分析,一是地緣關系,第二是中國當代藝術在世界上日益上升的地位,而且之前韓國Sumsung集團用藝術品進行逃稅一案,使得韓國民眾對購買本國的藝術品信心不足,韓國的一些畫廊生意甚至都受到了影響。其實從幾年前開始,北京藝術圈就一直盛傳外國人要來中國開博覽會,傳言甚至包括瑞士的巴塞爾當代藝術博覽會。
毫無疑問的是,“上海當代”和此次韓國基金會來北京辦藝博會,會給中國的當代藝術收藏市場帶來一些新氣象。著名音樂人、北京現在畫廊老板黃燎原參觀了去年首屆“上海當代”,他直率地表示,它是目前在中國市場舉辦的當代藝博會里辦得最好的。因為從國際號召力看,確實來了一些西方和日本、韓國比較好的畫廊,比如日本最好的洗澡堂畫廊、韓國的國際畫廊。
這跟外國團隊的運作很有關系,他們會不遺余力地邀請一些國際重量級畫廊來參加。中央美院人文學院副教授趙力也曾參觀首屆“上海當代”,他覺得“上海當代”增加了對畫廊展覽內容的考量,是種新的標準,但不能說與北京本土的藝博會誰優誰劣,各個藝博會應該有自己的性格,多些競爭,能使藝術展示的平臺更豐富,也更能反映世界性的藝術潮流。他覺得,國內本土力量操作的國際性藝博會還沒幾年,不能拿國外團隊十幾年的經驗來要求。能否達到真正國際化,這是個過程。
黃燎原的“現在畫廊”今年成為中國第一個參加巴塞爾藝博會的畫廊,同行的還有上海的香格納畫廊,但是是瑞士人經營的。去國外參展的成本就達幾十萬,參展品的運費、關稅、人員開銷、場租等價值不菲,而且參加巴塞爾不能虛報價值,所有展品得上全險。但黃燎原覺得值,上一個好的博覽會的無形效應是巨大的,從中能了解到國際藝術的最新走向,雖然參加國外博覽會要花很多錢,遠超于坐地銷售,但這個國際窗口能讓別人認識你,也能讓你認識新的人,能為未來發展提供機會。
黃燎原說,國外也有很多很濫的博覽會,但以他多次參觀巴塞爾國際博覽會的了解,它好到幾乎能跟藝術雙年展抗衡。巴塞爾會舉辦重要的收藏家、美術館的館長、策展人、機構代表等洽談會,挑選參展畫廊的標準很嚴格,有專門的評選委員會,但參加的是世界最著名的畫廊,所以從中能看到世界當代藝術的走向。
而在中國自己舉辦的藝博會上,目前能看到的還只是中國藝術的走向,還只能算是區域性的博覽會,吸引的還主要是日本、韓國的畫廊,整體看中國的藝博會也在學習過程中,正在朝著“亞洲藝術代表”的方向努力。但很多細節強行學了并沒用,國內博覽會的程度代表著國內畫廊、拍賣會的總體發展程度,而這些行業都屬于剛起步階段,所有水平就都體現到博覽會上了。國內各機構舉辦的當代藝博會,反映了在“當代藝術熱”面前抓住的機遇,但博覽會經濟現在已經被藝術界廣泛認為是新興經濟模式,它將對國際市場產生非常大的推動作用。
“中東幾個富裕國家已經開始把藝博會當成一種‘軟經濟’來對待”,APT亞洲執行長楊心一走了幾趟迪拜藝博會后感慨地說。中東國家的石油資源正面臨危機,因此它們必須和時間賽跑。這時藝術博覽會成為它們經濟發展的替代方案。迪拜現在正在快速發展其旅游等休閑行業;另一個中東國家阿布達比,也是阿聯酋的成員國之一,雖然它的石油還能開采120年,但現在也把下一個經濟增長點定位在藝術產業上。阿布達比擬建立一個藝術特區,其中將包含5個美術館、13個藝術展場、幾個雕塑公園、畫廊區和20個藝術家工作室,它的雄心壯志博得了法國盧浮宮和美國古根海姆美術館的支持,紛紛在阿布達比成立分館,不夸張地說,正如同中國一樣,當代藝術已成為中東國家的軟經濟。
剛剛在迪拜舉行的第三屆藝術博覽會是一個明顯的信號,它吸引了全球各地約70家畫廊參加,數量較去年增加了20家左右。黃燎原4月份剛剛去了趟日本,參觀了日本“101”畫廊博覽會、ARTTOKYO等幾個博覽會。他的感覺是,博覽會賣瘋了。日本藝術在海外買家的刺激下,近年來價格飛速增長,而且海外藏家對日本藝術的關注度已經大大超過了本土藏家。
日本創造的卡通風景線和插畫藝術成為日本美術的堅強基礎,小山、小柳、洗澡堂、東京、山本現代、西村、三潴、兒玉、SHUGOART、KAIKAIKIKI等畫廊構筑了日本美術的脊梁。“101”畫廊博覽會是一個新興的藝術博覽會,在一所學校里舉辦,場地也很小,參展畫廊不多而且大多是一些新畫廊,但無緣無故的買氣很旺,很多和他相熟的臺灣藏家都在瘋狂地進貨,因為日本藝術品比起中國藝術品的確相當便宜。ARTTOKYO是日本最重要的藝術博覽會,雖然也不是很大,影響力還遠遠不如中國的CIGE、藝術北京,但是也為國內外觀眾奉獻了一臺日本年輕當代藝術家的精彩展示會。
在中國,當代藝術品博覽會的興起只是近兩三年來的事,和拍賣行、畫廊比起來顯然晚了許多,為什么中國需要它呢?換句話說,它未來會在當代藝術圈中有什么重要性?楊心一給記者介紹了西方藝博會的一些歷史案例,它確實是引進新藝術品和提供收藏家、藝術品交易商直接接觸新式藝術品的重要平臺。最有名的例子是在20世紀初期,在美國舉行的博覽會ArmyShow,在當時,這個博覽會引進了歐洲主要的畫廊,展示了畢加索、杜象、馬蒂斯等歐洲年輕畫家的作品,美國收藏家從不認識這些藝術家到漸漸收藏這些現今公認為大師的作品的過程中,博覽會起了重大的作用。
雖然美國收藏家因為他們總是能在拍賣場上舉出最高價而成為眾所周知的藝術品收藏大鱷,但是在七八十年前,他們對藝術還只是一知半解。通過藝術品博覽會的持續舉行,他們也練就了眼力,豐富了知識,培養了膽識。現在,ArmyShow博覽會還在持續進行,規模和影響力已不可同日而語。每次一舉辦,全球藝術界就像是趕廟會般蜂擁而至。
這樣的情況也在另一個著名的博覽會中可以看到,瑞士的巴塞爾是歐洲最主要也是級別最高的當代藝術博覽會,每年6月舉行,每到開幕式,全球富豪收藏家都乘私人飛機前來,在短暫的幾個小時內就花數億美元將最好的作品收入囊中。毋庸置疑,這已成為全球富豪的年度Party。幾年前,它瞄準了美國邁阿密,現在,已成為當地的藝術旅游和其他相關產業發展的助推器。
楊心一覺得,中國的藝術博覽會和上述兩個全球最重要的博覽會比起來,還算是發展的初期階段,但它已起到推廣中國當代藝術和引進西方經典作品的作用,在中國的主要當代藝術博覽會中,我們已經可以看到國內最重要藝術家的作品,也可看到少量西方大師的作品。
接下來,國內藝博會還需要大量收藏家的參與和其他相關藝術機構的配合,這樣才可以成為一個藝術產業。藝博會這個集中表現的平臺已經成為收藏市場體系里的重要一環,中國比較有國際影響力的當代藝博會也給近幾年的中國當代藝術熱再燒一把猛火。但在兩年前舉辦的CIGE上,世界著名的Marlborough畫廊的中國藝術負責人PhilippeKoutouzis曾對中國迅猛成長的當代藝術市場非常尖刻地評價,中國不能和某些發達國家比,即使發達藝術國家市場進入低迷期,但大量基金會和博物館的存在,依然給藝術提供了一個雄厚的底座。
中國一旦跌下來,幾乎沒有任何防護和依靠。當時中國臺灣誠品畫廊經理趙琍認為:“內地藝術品市場狀況跟世界是反過來的,只有投資者、炒作者和拍賣會,沒有博物館和基金會,我們沒有辦法預測這個市場將會是什么樣,因為世界范圍內沒有可參照的例子。”一語驚醒夢中人,在投資者、拍賣會一路把當代藝術炒得過于火熱的時候,大家開始想象一旦某些身價狂高的畫家某天作品價格一落千丈,市場中的人們會是個什么樣子?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藏界專家說,現在公共機構和國家機構對當代藝術的收藏十分薄弱,市場的支撐主要靠民間的大團體和強大的藏家隊伍。
現在大家都在追逐當代藝術品的主要心理是投資和投機,收藏市場真正的繁榮應該是藝術家的創作水平提高和收藏真正普及的時候,能夠真正地收藏于民,就像如果一個國家的發展是靠炒股市而不是靠生產力的基礎,肯定是危險的。黃燎原認為,這個問題得分兩方面思考。現在很多媒體都在討論“中國當代藝術泡沫化”、“拐點論”的話題,理由是美國“次貸危機”和西方收藏家拋售中國藝術品的個別舉動。但據他了解,現在很多收藏古董的人都在籌備進入當代藝術領域,也有一些人在做私人博物館、私募基金,國外基金會也要進入,主要是進入當代藝術領域。
從另一方面看,憑空炒作出來的東西確實比較危險,應該從市場中擠掉,要調整畫廊、拍賣會在市場中的話語權。中國當代藝術家們在畫廊銷售的價格是完全可以接受的,現在大家都是沖著拍賣會的價格變動去說話,其實應該一級市場更重要,二級市場中應該呈現的是一級市場買不到的、經過市場認證的大師作品,或者處于收藏家收藏體系中的藝術品。趙力拿出了2007年英國《ArtReview》推出的一份“ThePower100:2007”的調查。
在對全球藝術界影響力的年度盤點中,其范圍涉及藝術家、建筑師、博物館美術館館長、藝術批評家、藝術策展人、畫廊、藝術博覽會、拍賣行、收藏家、收藏機構等各種角色,收藏家或收藏機構在數量上名列榜首,由畫廊、拍賣行、藝術經紀人、藝術博覽會等相關藝術市場人士所占比例也達到了30%。中國目前已經有了何香凝美術館、今日美術館、證大美術館等私立美術館。
誰在收藏體系中占主要角色,誰具決定力,這還很難說,需要各個環節的互相扶持和配合,但公共、私立機構的系統性收藏,和一批有保護中國文化責任感的大收藏家出現,確實能對市場起正面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