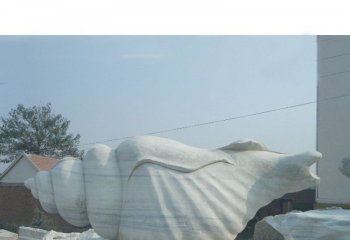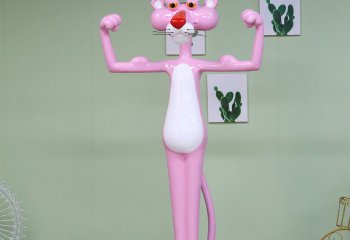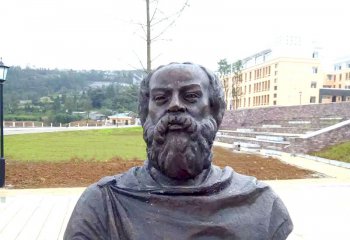后殖民理論作為一種學術話語乃至思想文化思潮進入中國,離不開大陸學術界對賽義德《東方學》一書的介紹,賽義德的《東方學》一書出版于70年代末的西方,但是在80年代末大陸文學研究界最高級別的刊物《文學評論》就介紹過此書,同時也有一些學者在文章中涉及到一些后殖民理論;

但準確地說,它在中國學術界引發一場波及面相當大的"風波"則是90年代初期的事了。1993下半年到1995年短短兩年多的時間內,國內各種有影響的刊物集中推出了不下50篇相關的文章,這這反映了在新的世界格局下,特別是經濟全球化,世界一體化之后,學術界對的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國家在意識形態上的文化沖突的反思和憂慮。

后殖民主義批評也由此在中國理論界愈演愈烈。在90年代以來,關于國學研究熱的興起,文化研究轉向對中國“五四”文化革命的反省,中國知識分子從新評價中國“五四”以來構建的中國現代性之旅以及啟蒙話語。80年代末到90年代,掀起的文化尋根熱,弘揚黃土文化正是這種反思的結果,這與“五四”時期以及80年代批判傳統以及對西方現代性精神的崇尚態度形成鮮明對比。特別是在90年代中期,有關東方主義以及后殖民批判的大批學者卷入其中,時任教北大的學者張寬在《讀書》上發表了《歐美人眼中的"非我族類"》文章,據張寬自述:“同時期的學者有此外北京的王岳川,王一川,王寧,陳曉明,戴錦華,上海的朱大可,成都的易丹,海外的張隆溪,周蕾,劉禾,陳小梅,劉康,徐賁等也早寫有重要論著,再加上日裔學者三好將夫和土爾其裔學者德利克,海內外的批評界有關中國研究與后殖民的討論原本就十分熱烈,”那么東方主義在中國,學術界又找到了新的熱門話題:關于東方主義與文化殖民主義和第三世界批評的討論,關于文化與學術的全球化和本土化問題的討論,以及關于人文科學如何建構本位話語的問題的討論。

但正如鄒躍進教授所言,知識分子一邊接受著西方影響,同時又要擺脫他,來樹立自身的民族性和現代性。這確實是一種兩難境地,正因為這種矛盾,如何實現這種轉化,是中國知識分子懷有的焦慮,而后殖民主義提出問題的尖銳性而引起的文化現實,對知識界無疑又是一種恐慌,尤其是在建樹民族現代性以及本土性上。近兩年來,中國藝術界與東方主義以及后殖民主義有關的展覽和文化活動比比皆是,這顯示了后殖民主義理論的巨大威力。

我在此列舉了主題特別明確的直接宣言東方主義理論并具有代表性的兩個美術展覽,以此說明美術批評知識分子對東方主義的態度。第一個是2006年3月在中國美術館舉辦的“東方想象2006年首屆年展”,學術主持鄧平祥在展覽前言中介紹說:“展覽旨在立足于中國人的文化立場上,弱化油畫的西方身份的理念,把油畫只當作繪畫的工具材料,畫出有別于西方油畫的富有東方文化特色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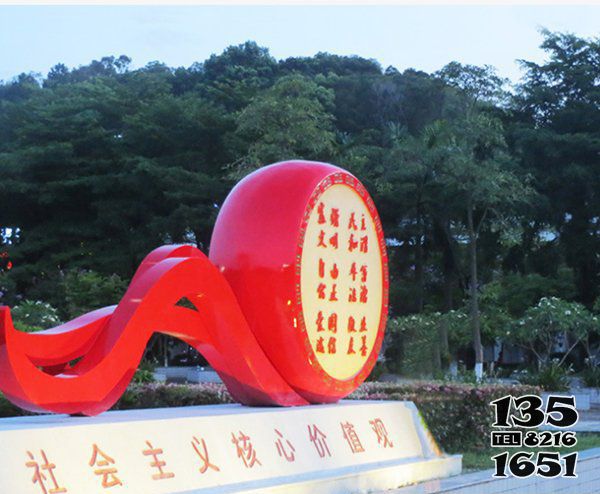
展覽雖以最原初的東方神秘主義哲學為邏輯起點,卻以一種超前的“表征”直接定位于“后現代”。策展人殷雙喜將展覽命名為“東方想象”是要區別東方主義中的“想象東方”,以中國人自己的身份近距離“真實想象”來拒絕西方中心主義的妖化。他說:“將展覽命名為“東方想象”,表現了他們強烈的回歸藝術與確立自身而非“他者”的愿望。這種藝術強調個體的想象力與傳統藝術文脈的血緣關系,強調一種自由的藝術創造力,它也許是在西方強勢文化下的百年覺醒,是一種“東方既白”的自信與腳踏實地的藝術態度。經歷了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藝術的涌入與洗禮,新一代中國藝術家開始用更為獨立的眼光觀察急速變化的現實,中國當代藝術對西方的想象又回到了自身的文化情境中。
”另一個展覽是鄒躍進策劃的2007年“‘狂歡’東方想象五人展”。這是第一次“東方想象”展覽的延續,但是這次展覽的主題雖然也名以:東方想象。但是這只是在圖示上的傳承性,而策展人的出發點不僅只是在展現一種‘東方想象’,而是要揭示一種中國知識分子的兩難境地。他說:“當中國藝術家以東方的文化身份自居來想象東方時,其復雜矛盾的心態、無法逃避的困境,以及張揚自我族類的決心,都會展示在藝術家們的想象和形象的描繪之中。
在此意義上,我們完全可以把參加《狂歡——東方想象五人藝術展》的五位藝術家作品中的藝術特征,看成是二十世紀以來,中國藝術在中西文化碰撞、交流、對抗和沖突中的一種象征。”那么這兩種不同的言說方式和出發點表明了對東方主義在中國的兩種不同看法與策略。前者是可以說對東方主義是一種反抗性陳詞,這正如張法、張頤武、王一川提倡的“中華性”,為了對抗西方中心主義而采取的自救。
在他們看來,“中華性”不試圖放棄現代性中有價值的目標與追求,相反,中華性既是對古典性與現代性的雙重繼承,同時也是對對古典性和現代性的雙重超越。"它的核心是:1、它不再象現代性那樣以西方的眼光看中國,而是要以中國的眼光看西方,用共時的多元并存取代線性史觀,強調文化的差異性與發展的多樣性。
2、以突出中華性的方式為人類服務。3、中華性具有開放的胸懷,它用是否有利來取代是中是西的標準,它包容萬有,而最后達致中華文化圈的產生,中國在這個文化圈中將可望成為中心。針對一種文化自尊以及民族主義的對西方中心主義的反抗策略,后者觀點的理論在后殖民主義語境下,更顯示出一種客觀時事的陳述性。因為不管如何,歷史給予我們的經驗已經與西方經驗融為一體。張頤武在>一書中討論了“人民記憶”問題,他認為“‘人民記憶’是文化機器和意識形態爭奪的關鍵領域,也是第三世界文化發展的關鍵”。
在張頤武看來,目前中國“人民記憶”的最現實的壓制力量來自第一世界,因為后者的意識形態已經滲透進中國文化的“形式”和“無意識”之中,并把中國文化淪為一種“派生之物”,中國人民除了存留在“母語深處”的“刻骨銘心的‘記憶’之外,已經不再擁有什么了。
”鄒躍進的觀點在他的《文化身份的焦慮——西方化語境中的文人畫、中國畫和水墨畫》文中闡釋的非常清楚,對于中國知識分子而言,為了民族文化的純化以及國際化策略,在對待中國傳統文化——中國畫的再三命名上采取了不同的策略。歸根結底,這種策略正是反映出了自我民族身份的焦慮,處在中國——西方,傳統——現代的二元定格上的中國知識分子感受到西方沖擊的力量,而中國作為傳統的滯后性。
鄒躍進提出了一種新的看待角度,揭示了一種中國知識分子所處的雙重身份的尷尬,那么要如何來對待?他提出了一種“求同存異”的戰略。在他的邏輯中,如果西方主義作為一種“人們記憶“再也抹不去了,那么我們只能在不斷的反思中受到它的影響,“隨著這種西方主義在全球的迅速擴張,也同時為中國的東方主義藝術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空間,中國東方主義藝術將真正成為一種全球性的國際性的語言而傳到世界每個角落。它的精神文化成為世界公民普遍認同的新的人文價值——不是征服自然,而是與自然和平共處。
”我們暫且把這種策略稱為“共生型”。近期有關周彥和王南溟的關于后殖民主義的爭論很是熱鬧。源于85時期的藝術家在90年代初期紛紛導向國外,并在國際上取得了很高聲譽,被譽為中國海外的“四大金剛”利用了中國傳統的四大發明的文化符號而國際上奏響中國藝術,王南溟在批判蔡國強的文章中,出于一種文化自尊,把蔡國強的“龍”符號轉換為一種中國文化的賣弄與獻媚。
周彥《“去中國化”的殖民心態——兼談后殖民主義下的當代藝術》一文,就直接對中國當下的這種民族主義的批判提出質疑,在他與王南溟的針鋒相對中,周彥完全不同意把在國際上走紅的藝術家的罪名歸結于對中國符號的販賣和對西方趣味的迎合。他認為去“中國化”本身就是一種后殖民主義的恐慌,對民族文化的焦慮,這種見“中國符號”“中國性”“中國文化身份”就上火的偏見,其實有落入到了與西方后殖民主義如出一轍的殖民心態。
他分析了一個藝術家具有的民族文化的印記和經驗,周文認為,中國符號不在于要不要用,而在于怎么樣運用,王南溟所批判的“符號”和“標簽”是不一樣的,符號承載了所指與能指,而標簽只是一種膚淺的外在指涉。中國符號的運用不是給中國文化貼標簽,而包含了一種現實,四大發明文化符號運用,契合了后殖民時代的中國文化的處境和新實踐。那么周彥提出中國當代藝術應該如何應對后殖民主義大環境和中國自身的文化環境?那么在他看來,符號不重要,重要的是對世界共同問題的參與性,去除一元論,而主張從中國實際來構建現代性,那么就是說后殖民主義話語只是我們思考問題的一種方法論,不管黑貓還是白貓,能抓到老鼠的就是好貓。
后殖民主義文化是個“文化拼貼型”的文化世界,對不同的文化類型就有不同的改良方案,我們暫且把以上三種歸為1,對西方主義的反抗型,2,共生性,3,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型。當然,在文化界關于對后殖民主義對中國現代性構成的威脅中還有內部的分歧。在反抗型中,就有兩種不同的側重點。第一種就是對西方中心主義的反抗,這已經敘述過,而第二種,則是側重在反思對中國本土性的反抗,張賁在反對張頤武的“人們記憶”時就說,這種后殖民壓迫不是來自第一世界,而是本土自身。徐文指出,在今天中國流行的、由官方與商業聯手造成的第三世界批評,就其對抗性而言,同西方及其他第三世界國家的后殖民批評似乎有一致性;
但是在西方與印度,第三世界批評的關鍵是"反壓迫"而不是"本土性",它的出發點是"特定生存環境中人們所面臨的切膚壓迫與現實反抗。"比如在印度,第三世界批評的主要對象包括民族主義和官方話語的結合,包括表現于本土政權中的殖民權力。而中國的后殖民批評的核心是本土性而不是反壓迫,或者說它只反第一世界的話語壓迫而不反國內本土的文化壓迫。
在徐文看來,來自第一世界的所謂"壓迫"實際上根本不是當今中國所面臨的主要壓迫形式,因而中國的第三世界批評"有意無意地掩飾和回避了那些存在乎本土社會現實生活中的暴力和壓迫。"中國的這種只有"國際性"而沒有"國內性"的"反抗性"批評"不僅能和官方民族主義話語相安共處,而且以其舍近就遠、避虛就實的的做法,應順了后者的利益,提供了一種極有利于官方意識形態控制和化解所謂’對抗性’的人文批判模式。"徐文進而對第三世界文化批評所說的“潛歷史”、“人民記憶”等都作了深入分析,認為造成對中國歷史與人民記憶的真正壓抑的,恰好是已經成為中國官方意識形態的特種西方話語,但是中國的后殖民理論對此卻避而不談,因而它的"主要潛能還遠遠沒有釋放出來。
尹吉男在他《絕非野生動物的眼光》精到的道出了一種在后殖民主義語境下的審視眼光,“我們是自我馴化了的動物…我們首先是要攻讀一大堆的有關西方現代藝術的經典著作,然后再一本正經的解讀西方現代藝術作品。”但是知識的生成遠不是我們想象的那么簡單,今天西方的電視人的“特別貢獻”就是把我們引入到一個文化的國度,并已經規定了我們想象的空間,非洲是野生動物的世界,亞洲是民俗的。鄒躍進教授的《他者的眼光——當代藝術中的西方主義》也揭示了這一內在邏輯,如果用福柯的話語權力來說,就是知識不等于真理,而是一種權力。
那么如何去解構這種權力,在后殖民主義理論窠臼下如何超殖民心態,那是持不同意見學者正在不斷論證的課題。二元對立不能解釋后殖民主義的混雜行,張頤武在解釋別人的二元對立批判的理論時是如此清醒,卻忘記了自己在《從現代性到中華性》中恰好制造出了現代性/中華性的新的二元對立。
這種弊端容易陷入到新一輪的后殖民陷阱中。我認同鄒躍進提出的策略,求同存異。也贊同邵建的“進口問題“進口理論”的區分。當然,后現代的混雜性也具有包容性,那么,正如張頤武批判的那樣,二元對立的觀點將失去威力。
在檢視西方中心主義或東西方文化關系時,必須有一種超越于民族主義之上的文化價值取向,不能完全以民族的標準或文化相對主義來消解文化價值的普遍標準。我們不必因為西方文化曾經并仍然是世界文化的中心,就對之盲目崇拜;也不必因此而對之心存戒心、時時提防,唯恐上當受騙。西方文化的中心地位既不應是它受到崇尚的理由,也不應是它受到排斥的原因。
如果中心的文化中確有好東西,就該毫不猶豫地學,確有壞東西也該毫不猶豫的拋棄。這個原則同樣適用于東方文化或中國文化。我們不能因為它是東方的、中國的或邊緣的就加以蔑視或弘揚。在此,與文化的民族主義相關的文化的相對主義也應受到應有的反思。文化相對主義既有抗拒文化霸權主義的進步意義,也可能成為維護民族文化中的糟粕理由、甚至為專制主義提供借口。
必須看到,文化相對主義是有它的效度域限的,超過了這個域限,相對主義就不再有效。比如在非洲的一些部落,至今還存在這樣的習慣:殺死他們的父母以釋放其靈魂,幫助他們轉世。從文化相對主義的立場看,這是特定民族的一種特定的文化習慣,應加尊重,否則就是文化霸權主義。我想,在面臨這種選擇的時侯,一個稍有常識的人都會寧要"霸權主義",不要相對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