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梓:1994年的時候,您在北京做過一次個展,我們看到在很多刊物和有關雕塑的文章中都記錄和評價了這次展覽。傅中望:是的。展覽在北京的中央美術學院畫廊,我和隋建國、張永見、展望和姜杰一起做了一個雕塑系列展,叫“雕塑1994”,也就是五個個展,每人展10天,我的展覽名稱為“臨近的新關系”,展出了《天柱》、《地門》、《世紀末人文圖景》三件作品。傅中望:那時候和現在不一樣,電腦尚未普及、也沒有手機。我和隋建國他們都是靠書信交流,討論展覽要怎么做、都有哪些展品,這些書信我都留著,現在這個年代不可能再有了。

曾靜:是的,現在是被電話、郵件轟炸的時代,雖然效率很高,但似乎比“親筆書寫”的交流方式少了些人情味。當時展覽為什么取名為“臨近的新關系”?1994年正是您“榫卯結構”的創作期,是為了說明榫卯是一種關系的藝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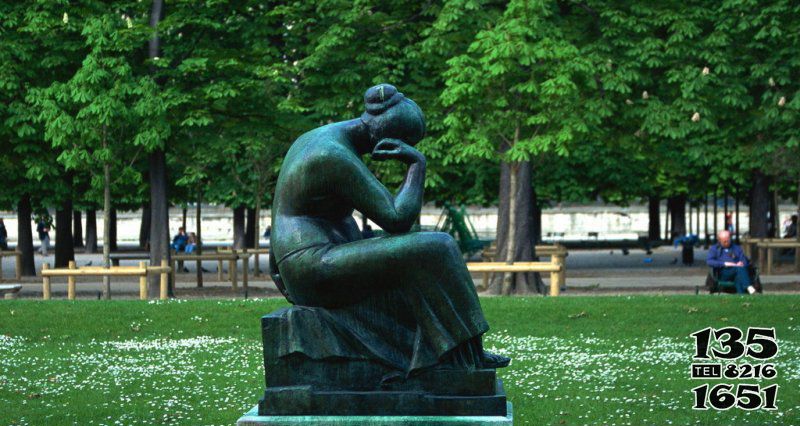
傅中望:不是為了說明,而是為了表達。我從1988年開始提出“榫卯結構”的概念,并從事以此為母語的創作近十年,在我看來,它并不是我個人的創造,而是一種中國文化傳統的物化形態,是傳統資源的當代轉換,我只是發現了這個符號,并選擇了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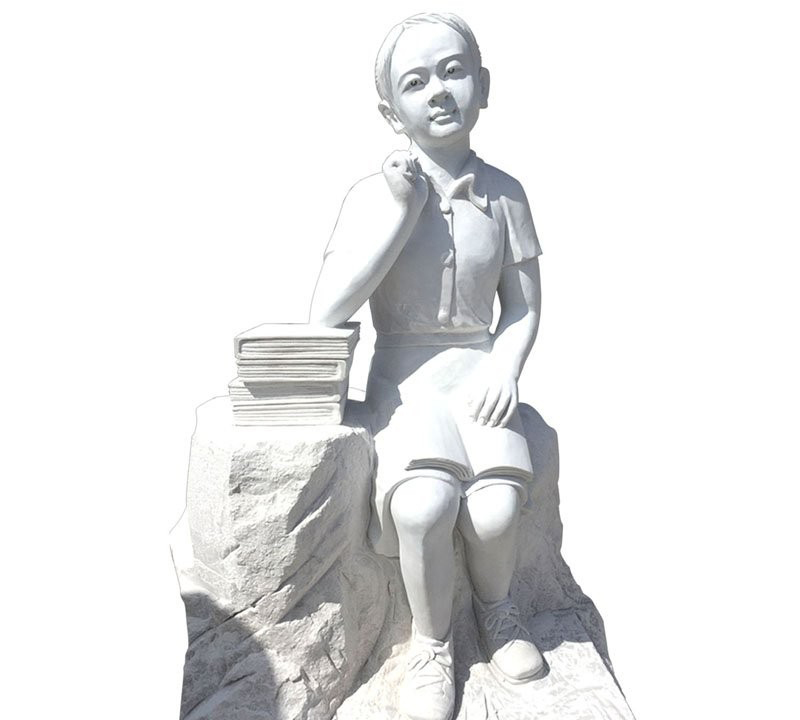
榫卯是結點的藝術,有結點就必然產生關系。在古代建筑中,工匠賦予榫卯不同的結構方式,造成了不同的結點的關系。延伸到我的作品上,我也并不希望它們僅僅成為傳統文化的圖解,而是想強調它與現實社會、與人類生存狀態的某種關聯性。所以我強調榫卯是一種關系的藝術,關系在今天是有意義的。自然關系、社會關系、國家關系、生命關系等等,都在一種矛盾、對立、無序、游離、不確定的狀態中生存。

胡鶯:重要的不是造型,而是關系。您當時還寫過一篇文章:《關系與關系的藝術》。傅中望:是的。我那時在嘗試“榫卯結構”中各種結點的可能性,對一位藝術家來說,資源可以利用和改造,但不可重復。我不希望我的作品淪為一種樣式化、風格化的造型模式,它必須承載藝術家對生命、對社會的思考。所以“關系的藝術”正是我對“榫卯結構”思考的縱深,由結點的關系,引發了今天存在于每個人身邊的關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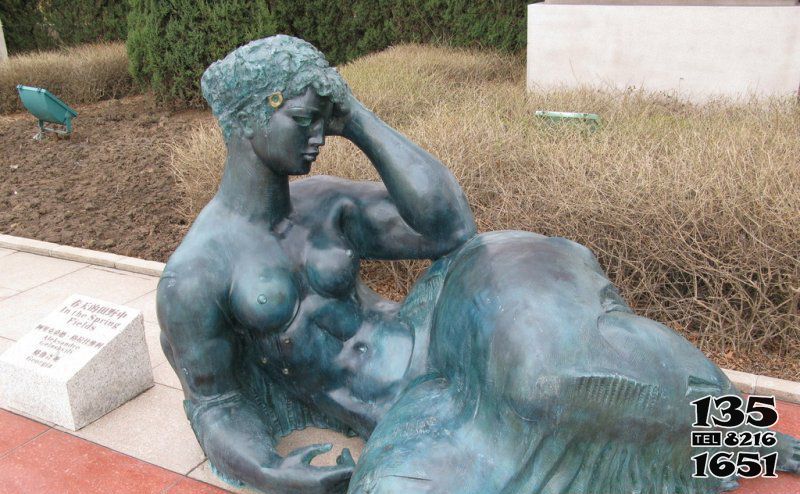
夏梓:“臨近的新關系”就像您在當時所發布的一個訊號。這樣一隔就是17年,現在和當時的心境肯定也不一樣,這次在西安做個展,有什么期待?傅中望:我這個人很隨性,對于個展,也沒有刻意地去強求,但是一直都有這樣一個愿望,這幾年自己在做美術館,不斷地給藝術家做展覽,也很希望能有個自己的個展。剛好這次的機緣巧合,有社會關注,有許多朋友幫助與支持,又有這么多知名理論家為我撰文策劃,我個人是非常感動的,也非常感謝。
雖然這幾年我一直專注于做好美術館,但創作方面是沒有懈怠的。也可能是推廣力度不夠,大家對我的后期創作不甚了解,大多對“榫卯結構”的印象比較深。我不希望大家停留在過去的記憶中,不希望做成一個回顧展。胡鶯:所以這次展覽會展出您的許多近期作品?我相信對外界而言,他們對您的新作也有一種期待。傅中望:這是我所希望看到的。當大家看到我的展覽時,或許會說,傅中望這些年除了“榫卯結構”,除了做美術館以外,并沒有停滯,他仍然在思考問題,為藝術創作在不斷地工作,他的作品沒有去一味迎合市場與潮流的痕跡,而是一直在期待原創、提出問題。
曾靜:您在17年前的個展提出了“關系的藝術”,這次的展覽主題定為“軸線”,乍看之下,您的創作似乎有了大的轉變,但其實本質上還是保持了文化意義的一致性,是“榫卯結構”的一種深化、提升。您的作品不管是“榫卯”還是“異質同構”,都是嵌入的方式、并置的形態,而“軸線”則在嵌入、并置的同時貫穿所有。
“軸線”這個概念在某種程度上幫助了我們理解您的新作以及新老作品之間的邏輯關系。能跟我們聊聊您對于“軸線”的理解嗎?傅中望:縱觀中國的文化、經濟、政治的變化,我們可以看到很清晰的一條中軸線,中國的文化傳統、整個體制都是沿著這一條軸線展開,甚至我們普通人的一生在特定時代背景下,也是難以偏離其主流的發展。反觀我自己的人生道路也是如此。我兒童時代的夢想是做一個畫家,到后來“文革”期間寫標語、辦畫報,1974年參加“黃陂泥塑”,到后來上中央工藝美院系統學習雕塑、從事雕塑創作,直到現在,我很慶幸一輩子沒有離開過藝術。
所以我為這個展覽做一條很長的“軸線”——用椅子形成一條貫穿整個場館建筑的中軸線。其實中軸線的作用就是一種定位,中國人是特別講究中心對稱的,統治者的位置肯定是在中軸線的中心點上,在西安這個歷朝古都,中軸線的意識更是非常強化。此次展出的《軸線》是由很多把最普通的塑料椅子構成,我的想法是當今社會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位置、自己的軸線,這個軸線也許是在家里、在心里,但都有其自身的定位。
胡鶯:“軸線”自古就有,它貫穿人類文明的結構和走向,但不論是從您的作品還是從現實來看,我們都能隱約感受到“軸線”上發生的變化,以及您賦予“軸線”的新意。傅中望:《儀式》這件作品既是我的作品又是這次展覽開幕式的形式。
在中國古代,“儀式”是帝王專有的,它只能在軸線的中心點發生,平民百姓是不可以隨意舉行儀式的;在現代則不同,“儀式”變得很常見,日常生活中,每天不知有多少“儀式”。《打樁》這件作品在樣式上仍然有“榫卯結構”的印記,但在意義上跟“軸線”同源,是一種定位,無論是古建筑還是當今蓋高樓大廈都要先打樁,屬于空間的界定,從社會學角度來說,每個人也都在為自己所尋求的位置努力學習和工作,我們到美術館來工作即是人生選擇之后的定位。
夏梓:說到定位,手機的定位功能對于現代人來說已經是一種生活的必須了,您將“木樁”置換為“人手一部手機”、“人手一張IC卡”,表面看反映的是現代人的通訊方式和消費方式,更深層次上反映的是現代人與人之間、人與物之間的關系狀態,這也暗合了您之前的創作對于關系的藝術探討。傅中望:人手上拿什么物品,能反映一個時代的特征、與相應的時代背景有緊密的聯系。遠的不談,就“文革”時期,我們每個人手上都拿一本“紅寶書”,這種全民性的行為在那個年代是自上而下的,而現在,我們誰都離不開手機、離不開銀行卡及各種IC卡,這些物品可以說是全民所有、全民互動。
比如手機,其實一部手機就是一個人的話語權、它賦予每個人通訊的權利,這又是一次全民性的行為,只是在這個消費時代是自下而上的。紅寶書和手機是兩種不同背景下的集體行為,一種是盲目追隨和狂熱崇拜,一種是自覺的語言交流和生活必需。曾靜:隨著時代的發展,軸線產生了“質”變,現代人都能有自己的位置了,這體現了一種平等,是文明的進步,但是從通訊方式的快捷變化來說,手機、電郵都喪失了親筆書信所能攜帶的鮮活情境和珍貴情感,這是我們所不樂意的。傅中望:是的,過去我們領工資都是發現金,現在是一張工資卡,卡和現金的感覺是不一樣的。
我這個人很戀物,用過的東西壞了、過時了都難以舍棄。我用過的收音機、電視機、照相機、手機很多,一個都沒丟,都很好地保留著,把它們一個個排列出來就是一條線,就可以成為一件“軸線”的作品。我以前收到的展覽請柬、邀請函、展覽海報等,我都習慣收集起來,這些都是線索,但是近幾年大家都發電子請柬,有時候就是一個電話、一封郵件、一條短信息,雖然很快捷,但是這條線索就斷斷續續了。
現在,“軸線”也越來越分散不那么清晰了,“軸線”變成了天線。胡鶯:話說回來,地位的懸殊到地位的平等,人情味的濃厚到平淡,思維僵化又或是自由,都是圍繞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的,對于關系的探討還是您創作的一條主軸。
傅中望:對于現實社會中的各種關系的變化、新的關系形成,我是很敏感的,試圖通過作品及時地作出種種反映。從“榫卯”到現在,我始終希望我的創作能夠與整個社會的現實相關聯,用自己的語言方式與歷史、與社會對話。在我找到“榫卯結構”這一語言方式的時候,非常自信,因為我覺得這種轉換跟我所要表達的東西是很貼切的。選擇“軸線”這一概念,因為我覺得包容性更大、可能性更多,給了我充分自由的創作空間。曾靜:您參加了很多當代藝術展,總是能夠從中國最傳統的文化資源中找到一些經典的元素,比如榫卯、四條屏、花瓶、帽子等進行轉換并賦予新意,現在您利用“中軸線”這一資源,其實這種資源轉換方式也是您幾十年創作的一條主軸線。
傅中望:其實我的這種創作方式是比較投機取巧的,雖然我參加了一些展覽,但我并不是一個搞新潮的前衛藝術家,一直以來我都堅持中國藝術的本土化,在中國傳統的文化資源中進行轉換。我的“鋁鉑拓型”系列雖然拓的都是現代生活中的物品,但“拓型”這一方式本身是源自古代拓片和金鉑工藝傳統。
我一直有個想法就是要用鋁鉑把中國古代的碑刻全部都拓下來,包括邊緣的細節紋飾等,但這個工作太龐大而暫時無法開展。其實“軸線”這個概念打開了說,不僅是我30多年創作經歷的一條軸線,也是中國社會變革的一條軸線,更是我藝術創作的一條邏輯線。我現在做美術館工作,創作量減少,大家都覺得我犧牲很大,但實際上美術館在更大意義上來說是一件“公共雕塑”,做好了之后影響范圍將更大,美術館從某種意義上講,是一個區域文化軸線上的支撐點。
夏梓:我們剛剛談到了您的新作,談到它們被您所賦予的“軸線”的新意,還談到美術館的“公共軸線”。其實不難發現,您對自己這條軸線的把握始終清晰,也正是這條線讓您隨著時代的變革,在藝術創作上提出問題,將個人思考轉換為集體表達,從而更有影響力和社會意義。傅中望:我覺得藝術史就是不斷創造的歷史,其實我的每件作品背后,都打上了歷史變革的印記。
胡鶯:比方說您在“黃陂泥塑”時期,作為知青,在那個特殊的年代,創作了一批反映農村現實生活和時事政治需要的較為具象的作品;后來在中央工藝美院接觸到西方現代造型藝術和民間藝術兩個方面的教育,也曾有一段時間追求優美、裝飾性的唯美表達。
傅中望:上個世紀70年代作為知青下鄉,我參與了湖北黃陂農民泥塑創作活動,那是一個以“階級斗爭”、“路線斗爭”為綱的年代,沒有創作上的自由,也不知如何自由創作,因而產生了《木蘭山下的怒火》、《華主席送女務農》、《不干,喝西北風嗎?》、《除“四害”》等作品。
后來的作品《生命使者》、《跳》、《慧眼》等是在工藝美院學習的結果,是一種唯美形式的表達。曾靜:再到后來,1985年美術新潮開始,短時間內西方現代藝術幾乎在中國重演了一遍,整個狀態是比較混亂無序的,您是怎樣的介入狀態?您在這一探索階段,是如何把握語言、材料和觀念的?傅中望:我那個時期的創作也是很混亂的,而這種混亂來源于整體上的創作“自由”,似乎覺得沒有什么限制了,各種材料和形態我都想嘗試一下。
但當時還沒有找到一個合適的方向,只知道要摸索,什么好玩我就做什么,都覺得有意思。當時的創作量是很大的,金屬的、木頭的、石材的、陶泥的,抽象的、具象的都有,就是想創造不同的形態,探索藝術上多種表達的可能性。
總的來說,我在這一時期受西方影響深重,現在看來只是一種形式主義。我當時還沒有考慮觀念的問題,考慮的多是語言問題。試圖在尋找一種表達自身意義的述說方式。傅中望:“金屬焊接”是到了湖北省美術院后做的,就是85、86年。這是我創作中一個不確定的時期,就是很希望用一些西方的語言方式去表達,所以就想到一家廢舊金屬回收廠去找點感覺,當時去的是湖北美術學院對面的一個廢舊回收站。
當那些廢舊機械零件、舊式的鐵器工具等,全部凸現在你面前時,特別有創作沖動,我也做了很多嘗試。但在當時來說只是一種體驗,我想用這種方式傳達一種新的視覺感受。我覺得是雕塑還是裝置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通過材料來表達自己的想法。如果你能表達準確,用什么方式都可以。我的作品中的裝置傾向是由于我的雕塑結構方式導致的,是創作意圖的需要。
胡鶯:《天地間》影響很大,后來在中國美術館展出,《美術》、《江蘇畫刊》、《文藝研究》、《美術思潮》、《中國美術報》等多家刊物都登載過,也是這個時候做的?夏梓:在經歷美術思潮的熱度以后,中國藝術家逐漸開始意識到原創性、本土性的重要。您是怎樣找到“榫卯”這一具有中國傳統文化特質的符號,并以此作為切入點進入創作的?
傅中望:我1988年幾乎沒有做什么作品,當時很困惑,不知道怎么繼續往下做。我覺得我的作品中西方文化的烙印太明顯,受別人的影響太多,沒有自己的獨特性和唯一性,而這種個人的原創性是我一直追求的。后來我去聽了武漢大學辦的“中國建筑文化研討會”,開始思考什么東西既帶有中國傳統文化的特點又有現代意味。
一位建筑學者對我說,中國的斗拱就是最好的立體構成。于是我買了很多中國古代建筑方面的書來研究,發現東方文化的特點與西方恰恰相反,不僅是造型藝術,比如中國的文字都是一筆一劃搭接構成的,中國的建筑、家具、工具都是橫向平鋪用木頭搭接的,與西方的建筑縱向壘砌不同。我回憶起在博物館做文物修復工作時,接觸到的棺槨、漆器、青銅器等,都存在榫卯結構,而“榫卯”與中國傳統哲學中的“陰陽”又是很好的對應,我一下子就被啟發了,這讓我真正意識到榫卯結構在中國文化中的價值,也領悟到了東西方文化的差異和造物意識的不同。
長期以來,我們對傳統雕塑只是從表面的裝飾和造型上去理解,而真正形成中國藝術特征的是內部結構。中國的榫卯結構和西方的壘砌結構,形成了兩大結構體系。我想這就是我后來研究榫卯、將榫卯的結構關系作為創作切入點的原因。曾靜:看來人生的閱歷對您的創作影響非常大。
比如您出身木工世家,早期做木工活的經驗,導致您對中國古代建筑、家具、工具有一種天然的興趣與敏感;博物館的工作經歷使您有機會接觸到中國古代器物中存在的榫卯結構,以致更深刻地理解“榫”與“卯”、“陰”與“陽”之間的對應關系。傅中望:這些閱歷對我而言都是財富,對我的創作及人生選擇都是有著潛移默化的影響。
我的名字里有個“中”字,這對我的生活和藝術也有某種心理暗示,做什么事情都取“中”,這樣我的內心才能平和。夏梓:包括您后來當了美術館的館長,做起了這個大的、公共性的“社會雕塑”。傅中望:談到公共性,上個世紀70年代知青下鄉,我組織知青“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走進村村寨寨為農民演出,挑著泥塑擔到田間地頭為農民展示、解說。這樣說來在那個時候,我就已經開始做“公共藝術”了。
胡鶯:再回到您的“創作軸線”上來,10多年的“榫卯結構”系列創作,是以西方現代藝術的眼光,審視和發現了中國傳統文化中有價值的東西,并且加以利用和改造;而此后的“異質同構”則是這一切入點的拓展與延伸。傅中望:當做了很多“榫卯結構”的作品之后,我開始覺得重復,榫卯結構是木結構造物的方法,但純粹用這種結構造型的話,只是構造了一種形象,而沒找到榫和卯的本質。所以此后有四五年我的創作幾乎處于停滯狀態。
后來我想,為什么榫和卯非得要用木頭來做,這種材料能不能和石頭組合、和現成品相結合?早期的榫卯結構是對中國幾千年文化符號的凝練,只是將其符號化、現代化了,和現實生活沒有任何關系。而要保持這個符號特點就要打開思路,其實我們正處在東西方文化相互碰撞的時代,不同的東西重新組合、異質的東西太多了。于是我提出了“異質同構”的概念,此后產生了許多不同材質、不同接點方式的作品。
到現在我還在延續這種方法。我做“帽子”雖然沒有強調榫卯結構,但其實還是榫卯結構的關系,人戴帽子、穿衣服、穿鞋不都是一種榫卯關系嗎?當藝術家找到一個切入點時,就應考慮怎樣去完善,不斷去拓展,不斷去尋找可能性。夏梓:您后來的《中國帽子》、《鋁鉑拓型》等一系列作品,雖然沒有“榫卯結構”、“異質同構”系列那么強的符號性,但“虛與實”、“陰與陽”的含義仍舊存在,雖然您沒有重復具體的榫卯形態,但我們仍然可以感受其中的榫卯意識。
傅中望:就我本身來說,我不愿意成為一個“榫卯專家”,可是我的作品自然而然地就與“榫卯”有關系,包括我近期創作的一些漆藝作品,漆的材質決定了作品與中國傳統文化的聯接,作品同時也存在榫卯的結構。《中國帽子》利用象征中國人身份地位的帽子,帽子的文化意義大于榫卯的穿插意義。《鋁鉑拓型》系列則是借用了傳統碑刻、拓片的方式,將材料做了更換。曾靜:包括《打樁》、《儀式》、《軸線》等,其實都是中國傳統文化符號的轉換。您的幾個創作階段是存在前后邏輯關系的,也是一個自然的變化過程。傅中望:我反復在強調“軸線”的概念,也是如此。
“軸線”可以說是貫穿我整個創作的邏輯線,也反映了這幾十年來我在這條“線”上所作的努力,這條線仍在繼續延伸。胡鶯:您在從事雕塑創作的30多年里,所遭遇的最大的難題是什么?傅中望:我覺得在我的創作中沒什么難題,就我個人的目前狀況而言,最大的難題就是時間很緊,要做的事很多。當代雕塑不同于傳統雕塑,形體的塑造與雕刻必須自己親自動手,而現在,只要有想法、有構思、有圖紙,找到恰當的、匹配的技術資源就能實施。
如果一個雕塑家在思想上沒有難題,那么在具體操作上是不會有難題的。所以,對藝術家而言,最大的難題就是自身,難在有沒有新的思考,新的體悟。當然,一切思考、問題的提出,基于你對現實生活的領悟。傅中望:不同時代和時期,對“好的雕塑作品”的界定是不一樣的。從雕塑家自身來說,無論采用了何種形式、語言、手段,只要能傳達自己的思想、表達自己情感,對其個人而言都是好的作品;但從社會的角度來說,好的雕塑是應該分層次的,工人、農民、知識分子、政府公職人員,每個人的審美和喜好都不一樣,每個人的標準也不一樣。
所以好的雕塑的標準可能就掌握在藝術家自身,或在觀賞者的內心,一個雕塑家不可能滿足社會的所有階層,即便是米開朗基羅、羅丹,畢加索、亨利·摩爾這些大家,他們的作品也是從藝術史的角度、從創新的角度被判定為是好的雕塑作品,而不是從公眾的角度。好的雕塑作品是優秀藝術家的創造結果,但不見得滿足社會各個階層的精神需求,從某種角度來說,藝術家只能尋求一個大體的認同。好還是不好?
時間會作出判斷,藝術史會有評價。傅中望:就雕塑本身來說,它始終是圍繞空間、材料、形體而存在的,這也是雕塑不同于其他藝術門類的重要因素。從視覺現象上看,無論是傳統的雕與塑,還是當代的裝置、現成品,它都是通過形體語言、空間語言來表達的,雕塑家的思想與情感也只能通過這種表達方式才能傳達出來,而雕塑家作為個體,也始終是在創造一個符合他個體需要的形態語言。
“雕塑”在今天這個時代只是一種有形物態的代名詞,是否雕與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選擇合適并能夠傳達藝術家的終極思考。藝術只能提出問題而不能解決問題,藝術家就要善于表達,將個人的思考視覺化,而這種視覺化的方式是否具有創造性、是否能感動人、是否能影響社會,就體現了一個藝術家利用媒介、運用材料的一種智慧。胡鶯:說到底,您創作的核心,繞不開您對文化的不斷思考與對這個時代社會現象、現實狀況的深層關注,而這些可能源于您這一代人與身俱來的歷史使命感與社會責任意識。
今天聊了很多,也談到很多問題,讓我們對于您作為一個藝術家的思想有了更全面、更細致的體會,同時也加深了對您作品的認知。謝謝您跟我們分享,預祝展覽取得圓滿成功。曾靜:湖北美術館在您的管理下,短短3年時間就被評為全國重點美術館,其成績有目共睹,期待這件“公共雕塑”在您的雕琢之下不斷完善,也期待美術館這條城市文化的“公共軸線”在您的導向之下不斷延伸、覆蓋更廣的范圍。
夏梓:從“榫卯”到“軸線”,您的藝術之路是越走越寬廣。“榫卯”揭示了中國文化方式的內核,同時提出了一種新的藝術語言;而“軸線”則在更高層面上,將個人的命運、文化的發展、社會的變革、藝術的創造都串聯起來,沿著這條歷史的軸線展開,就如同一張巨大的網,將世間萬象一網打盡。可以說“軸線”是您繼“榫卯”之后提出的一個新的視覺符號。我們希望在這條“軸線”上能衍生出更多更好的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