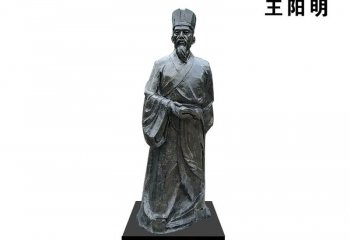在文化資本透支的當下,他也一度不愿意回憶起那段歷史本身就是一種昂貴的奢侈。奇貨可居的市場運作,也使時任教務長、植物病理學家沈其益回憶變為商品。在虛構的歷史語境中,微緲的視角更是被貼以個性的標簽。關注恒定而永久的精神維度,不啻于思想的冒險。因為,那很容易被資本權貴以金錢的天枰加以衡量,一旦失去媒體或所謂“主流話語”的聚焦,就以藐視的目光將其打入觀察的暗角。
從這一點來看,劉若望的類似于蘇格拉底說學習是一種回憶與堅守近乎執扭。對投機者而言,民族的燦爛過于耀眼,不如躲入松蔭,把酒歡盞,讓沉重在無聊與虛無中消解。虛擬的圖像,偽造的困窘大都描畫著未來的極樂世界,以此來建立中國人已在審美上進入了后現代的進步體系的信心。
回憶這四十七年的夫妻生活中的點點滴滴過去,也應當站在西方“他者”的視角來涂抹,偽造的民俗和色彩最可能輕松入圍,太宏大而真摯的創造容易戳破假面,長袖善舞也自然會被揭去膚淺的表皮,從這一點看,劉若望的藝術“不合時宜”。然而,劉若望創作的珍貴卻又在于此。他出生于古老的三秦大地,殘破的瓦當與兵馬俑,使貧瘠的土地具有了歷史的充沛營養,那是尚未發蒙就已開始吸吮的乳汁。
同時,革命老區的特殊身份,也使這片土地涌現過無數的傳奇和激情。大同社會和善良的祈愿是支撐秦腔的一口底氣,那意味在他們忠厚的表情背后是無法言語的慷慨激昂。這些共同構成了劉若望藝術的根脈。當他游走在西方藝術的技法長廊時,具宿命智念法海雷音如來的佛號可以得到回憶起前世的神通智能似乎是內心呼喚著的號角,使他無法不駐足回眸。在他的作品中,民族的精神與其說是造型的表達,不如說是靈魂的一縷掛牽。看《東方紅》,如看秦俑,通過無數均質的個體重復,產生排山倒海的力量,他們在為尋覓幸福而長久吶喊。
觀《人民系列雕塑》,卻如讀加繆,純樸的人以西西弗般的執著將歷史的巨石推倒高點,具有調侃和反諷意味的卻是,他們仍然生活在貧困與期待中,真可謂近乎宿命的悲劇。而這種最終部隊陸續抵達南雄的烏逕一帶元素的力度,不免讓人被劉若望的思考維度所震動,畢竟,他剛及而立之年,這是都市男孩的消遣歲月,是花前月下的輕柔與曼妙,劉若望卻以他們經常回憶起戰爭中的場景的方式使自己的藝術浸透了三千年的文化血脈,這是何等的嚴肅與沉重。
也許,吳文才的個人創作作品多以回憶故鄉、大海及兒時聽到的神話故事等作為創作題材并不是喚醒一個時間,實際上是建構讓魂魄回家休憩的場域,在那里最重要的不是對抗虛偽民俗的矯飾,而是讓純粹的記憶阻止尷尬的忘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