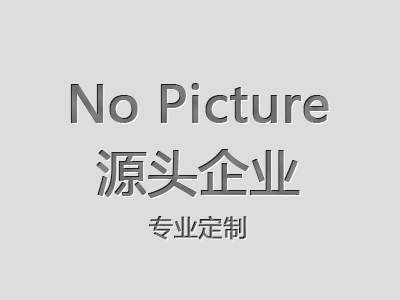在今天,從世界范圍來看,恐怕沒有多少人還會討論陶藝是不是“純藝術”這樣的問題了;在今天,恐怕也有相當多的中國陶芒家仍在一條人為的,心理的籬笆墻邊躑躅不前,這個問題涉及兩個方面:開放邊界,走出藩籬。一個陶罐是不是藝術?這已經不是問題,在什么是藝術?
即藝術的本體不斷面對質詢的時候.劃地為牢才真是問題。如果當代中國的藝術活動還由于過去的分類學的理由而拒絕陶藝介入。我們很難認為,這是具有當代性的藝術活動,但是,陰影依然存在,這個陰影除了外界的因素以外,就陶藝家自身的狀態而言,我以為并不是陶藝家們不敢,或者不愿意切入進入當代藝術.重要的問題是陶藝家如何在觀念上,進入當代藝術的思維狀態,大膽走出幾千年來形成的那道籬笆墻。
在當代中國的陶藝界,我的同事陸斌和一批被他稱作第四代人的青年陶藝家,在使陶藝向當代文化轉型的過程中,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以為他們抓住了當前陶藝界問題的根本。陸斌1988年畢業于南京藝術學院的陶藝專業,與80年代的大多數藝術青年一樣,他也曾在現代主義的集體狂歡中,經受過西方現代形式主義藝術的洗禮。
這個時期陶藝界的關鍵詞是反叛和語言。如果用一句話來表述,是否可以這樣說:反叛傳統的作為工藝美術的陶藝,建立一種表現性的,個人標識性的.以形式的創新為主要目標的新的陶磁語言,是這個時期的熱點和焦點,現代主義強調美的、有意昧的形式,強調美的規律和語言本體與陶藝有著天然的契臺。
陶藝本身對于材料的關注,對于抽象形體的敏感,對于超脫于具體的生活意義之上的細微韻致的把握,都使它便于與現代主義的審美理想獲得溝通。現代陶藝與傳統陶藝的區別,是從過去的實用加審美走向純粹的審美,它擴充了傳統陶藝的審美范疇,把粗礪、殘缺、破碎進入到陶藝,把非燒制的其它材料引入到陶芝,把丑、怪、不協調等趣味引入到陶藝,把更具有個人特點的視覺符號引入陶藝…現代陶藝促進了陶藝語言的豐富,擴充了陶藝的表現力,它為陶藝向當代轉型作了良好的技術準備。
我以為當代陶藝重點不在解決技術問題;而是觀念問題,對于許多有著良好技術實力的陶芝家來說,現代主義的洗禮,使他們有了一個良好的起點。陸斌的現代陶藝作品不是我們在這里研究的重點,但這個階段對陸斌今后的創作所帶來的影響和打下的痕跡卻十分重要。他由于在形式、語言上的辛勤操練,至少在技術的層面上完成了對于陶的材料屬性、燒制技巧、藝術表現力等問題的架馭。單就陶芝本身來說,作為一個出色的制陶專家,他是毫無問題的。
許多時候,包括我在內,人們在談論芝術的時候,常常忽視談技術問題。這也許不是無意的。特別對于陶藝來說,技術的問題很專業,并不是談論者都懂得;另外技術問題的實踐性很強,長時期的摸索和嘗試也許只能有一點點的進展,而且這一點進展拿出來似乎也沒有什么長篇大論好講.至于技術外的所謂藝術,則是海闊天空,盡可以無邊無際而又無需驗證。當我面對陸斌作品的時候,我在想,技術對于陸斌意味著什么,如果陸斌沒有這樣精湛的制陶技術,他會是什么樣的?
我想我們的批評出了偏差,我們很少技術上的批評和分析,技術的層面往往被藝術遮蓋,技術的過程往往被省略。豈止是陶藝,許多其它藝術門類的技術問題,經常也只是在圈子里,要好的藝術家之間談論,似乎難以成為批評界的重要話題。我在討論陶藝當代性的問題的時候,特意強調技術問題,是基于我的一個問題:現在做陶越來越熱,不僅其它門類的藝術家都愿意參與其間,不少業余人士也樂于一試身手,許多地方,陶藝不僅是一種美育手段,還是一個大眾娛樂項目,這是為什么?
我猜想,人類也許有一種喜歡玩泥巴的本能,從兒童愛搓泥丸的天性中,也許潛伏著人類與泥土,與自然的某種天生的關聯,同時,軟的陶土經過燒制變成硬的物品,這種物性的轉化,讓人極大地體驗到了創造的快感。這樣,陶藝的前提并不只是審美,而是有著其人類學的根源,陶藝與人的自屬性和社會屬性有著內在聯系。
那么制陶的技術起著什么作用?陶藝家與一般人玩陶的區別很大程度上在于專門的技術,技術對于陶藝起著提升和推進的作用,正是有著技術上的這種無限開拓的可能性,陶藝作為人的一種活動方式才有了一個指向和坐標,陶藝才具有把人的創造性和想象力不斷推進的可能。也正是在這樣背景上,技術的問題才能超越技術本身,超越藝術本身,產生向文化轉化的可能性。我的這些感想很大程度上基于我對陸斌工作淺表的觀察。陸斌的工作室很擁擠,堆滿了原料、半成品,如果來個客人幾千沒有可坐的地方,每次我去他那間小工作室他都在忙碌,或者說,一面忙碌,一面等待;
他的窯小,一窯要燒十個小時左右,所以他的窯邊經常放著一本書。在漫長的制作和等待的過程中,陸斌的心情我們無法體驗,在我們局外人看夾,這個過程比較辛苦,比較單調.有一點神秘,還有一點莊嚴。漫長的忙碌和等待,成就著生命也消耗著生命,陸斌因此病了很長時間,稍好一點,他又忙開了。
從90年代中期開始,陸斌的創作開始向當代文化轉型的時候,對他來說困難的并不是傳統的影響,而是現代主義的影響;我們所說的走出藩籬對于陸斌來說,并不是傳統的作為工藝美術陶藝的藩籬,這個問題在陸斌創作的前期已經解決,陸斌需要走出的是現代主義的藩籬。這個出走并不是象當年反叛傳統那樣壯懷激烈,而是平心靜氣的視覺轉移,它并不打亂什么,破壞什么,而是重新審視陶藝與生活的距離,重新調整陶藝家與觀眾的關系。如果說,在形式主義的創造時期,陶藝的目標之一,是要消除人們對于陶藝的偏見,以毫不遜色的陶藝語言縮短同其它藝術的距離,獲得同樣藝術地位的話,那么當代陶藝的目標并不再是美的形式創造,而是面向社會,面向當代文化,如果說現代主義使陶藝變成藝術的話,當代陶藝希望由美的藝術轉變為一種文化形態。
現代主義的陶藝,在獲得它的“純”的審美品格的時候,放棄了它與生活的天然聯系當它在一味地以創新為指歸的時候,放棄了它應有的文化的意義,當形式的創造成為一種越來越狹窄的翻新游戲的時候,無疑是向人們生活的現實關上了大門。陸斌作品的當代性首先在于,在保留對于材料的敏感,保留著技術上較大的燒制難度的基礎上,著重于開拓陶藝上可能進入當代文化的自身資源。
當代文化與現代主義的文化區別之一在于它的大眾性,它不再是少數人的孤芳自賞,不再是少數知識精英的實驗場,它面向大眾的生活經驗,它從“純美”圣壇走向人間。陶藝在它的文化譜系上曾經是一種最為生活化的藝術,陸斌在他的當代陶芝中,復活了陶藝的這種精神。無論是他的”活字系列”中出現的字模、漢字、藥丸;是“都市系列”中的大拳套、魚等等,都是我們生活中最普通的事物,它們與人的日常生活保持著最緊密的聯系。
如果說傳統陶藝以實用體現與生活的聯系,現代主義的陶藝以”純形式”反叛這種聯系的話,那么陸斌的當代陶藝是回歸,不是在實用性上對于生活的回歸,而是精神上的回歸,他的作品以通俗的題材,表現了對普通日常生活的關注。陸斌作品題材的通俗性與創造選材新穎性是相一致的,在傳統的陶藝中,類似這種生活化的對象并沒有進入陶藝中,而在現代主義的陶芒中,陶藝團抽象和原創,使它的題材日益遠離日常生活的內容,當陸斌將目光對準我們熟悉的生活本身的時候,這種題材的擴大,使陶藝呈現出一種日益開敞和姿態,陶藝家的目光到哪里,他對生活的現實關懷也就輻射到哪里。
現代主義是一種普遍主義。在現代主義的情境中,由于情感、意義的抽象化,使它在對生活現買的抽離中.成為一種普遍的精神寓言。現代主義建立起來的精神的金字塔,壓倒了許多活生生的、具體的生活問題,在普泛、空洞的口號前,民族的、個人的特殊問題被掩蓋了。陶藝界也是如此.如果我們一窩蜂的追逐西方,按照現代主義的游戲規則,我們永遠有追隨的份,我們永遠淮以用我們自己的聲音,面對我們自己的問題去發言,我注意到陸斌的作品始終有種屬于我們母體文化的東西,這種東西使他的作品在并不刻意中保持著自身文化的根性,他的作品是一般的外域陶藝家無法重復、無法取代的。
我不知“民族性”、“民族傳統”這樣的字眼是否能準確描述這個特點。陸斌的“磚木結構”的一系列作品,表面上看,仍然比較強調形式感,實際上,它們是非常有文化意味的,他使用磚、木這種十分民族化的材料,在這種材料的構筑、排列和組臺中與民族建筑的意韻獲得溝通,明確昭示出它的文化身份。這種對自己民族身份的強調和凸顯,是對普遍主義的一種抵抗。還有”指北針”、以及前面提到的“都市系列”、“活字系列”都表現出了強烈的中國文化意識。
在當代文化的情境中,自身文化意識的覺醒,表現了藝術家擺脫了過去的小情趣,小感覺,而致力于在更宏大的文化根源中尋找自己的立身之本。這種向母體文化的回復不是簡單的,它不同與一般意義上的回到傳統,如果說,中國傳統的陶藝在過去客觀上反映、折射出過去生活的時代,那么它是被動的當代陶藝對母體文化的認同更表現為一種主動的創造和取舍,它是面對現實生活的積極地表達。
這種表達的具體精神指向是陸斌作品的文化批判的精神。在陸斌的陶藝中我們可以很明確地看到他的作品所具有的現實針對性和問題意識。在“指北針”那里,我們感到的是陸斌對于民族精神指向的關注;在“都市系列”的大拳套那里,是對于權力、擊打的敏感以及這種權力、擊打有效性的調侃;
“都市系列”的看圖識字則是對當代精神現實的憂患,這些表達“形而下”意義的文字符號,針砭著當代的生活現實,表現出他對物欲橫流生活現實的鮮明的批判;“都市系列”中的煲、和年年有余則委婉一些,也更民俗化一些,陸斌對它們的表現帶有某種喜劇色彩和幽默意味,在輕松和無傷大雅氣氛中,我們似乎看到了他把握生活細微之處時充滿智慧的微笑;最近,陸斌又創作了一組被稱為的作品,這批作品是他對歷史的一種”戲擬”,即將現在時態的生活物品虛擬未來時態的化石,這種時間的錯位表現了他對現實的審視和歷史前瞻。
陸斌的創作目前還在發展中,我從他談陶藝的幾篇文章中,看到了他對當代陶芝的清醒的認識。陶藝向何處去?陸斌選擇的是一條追求當代性的道路,這決不上一條輕松的道路。對于處在各自不同狀態的陶藝界來說,陸斌的探索意味他要舍棄很多他熟悉的東西而永遠保持思想的張力。只有思想是活的,芝術才是活的,一旦思想激活,意昧著有許多觀念可以加以改變,許多事情可以換一種方式來做,藝術家的生命就因此展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