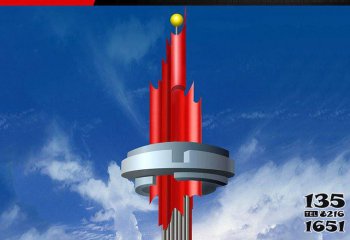20世紀(jì)80年代是中國(guó)藝術(shù)朝向西方的時(shí)期,“85新潮”之所謂“新”,不過是現(xiàn)代主義藝術(shù)西方已有而中國(guó)尚無。其中最有價(jià)值的東西乃是以個(gè)體創(chuàng)作沖擊集體主義乃至集權(quán)主義文藝思想,至其極即是文化大革命。但千萬不要忘記,文革藝術(shù)是以文藝為工農(nóng)兵服務(wù)、以藝術(shù)大眾化的名義進(jìn)行的,用今天的話說,它并不拒絕公共性。
80年代中國(guó)雕塑家都在向錢看,在美術(shù)界他們和搞裝修的人一樣,屬于“先富起來”的那部分人。從名義上講,他們做的全是公共藝術(shù)。官方意志加上致富要求,再加上一點(diǎn)先是來自前南斯拉夫、前蘇聯(lián)、前東歐然后是來自西方的形式構(gòu)成,便造就了80年代中國(guó)城市的雕塑景觀。客觀地講,雕塑家把國(guó)家的錢賺在個(gè)人口袋里,也并非不是好事,因?yàn)榈袼軇?chuàng)作所需的花費(fèi)遠(yuǎn)遠(yuǎn)大于繪畫,有了錢個(gè)人創(chuàng)作才可能起步。
80年代的視覺革命是經(jīng)濟(jì)成本低廉的運(yùn)動(dòng),繪畫界風(fēng)起云涌而雕塑界晨星寂寥,是可以理解的。當(dāng)時(shí)為數(shù)不多的前驅(qū)者,如王克平、吳少湘、朱祖德、張永健、付中望、宋海冬、隋建國(guó)等人都是在極其艱難、極其窘迫的狀況下進(jìn)行個(gè)人創(chuàng)作的。還有些木雕、陶藝的探索,也是因投入小而易于出彩的緣故。據(jù)我所了解,朱祖德的所有幾十件鍍銅雕塑都是在他家住房陽(yáng)臺(tái)上的洗衣槽內(nèi)完成的,后來他不幸遇難,也是為了找點(diǎn)錢而去考察一個(gè)城雕業(yè)務(wù)。最近美術(shù)界大炒85,給人的感覺是國(guó)際還鄉(xiāng)團(tuán)在爭(zhēng)奪第一把交椅,農(nóng)民造反有了山頭便火併王倫,這不足為怪。
我一點(diǎn)不反對(duì)花大力氣去整理歷史,但歷史闡釋一是要鉤沉,二是揭示歷史對(duì)于今天的意義,象朱祖德這樣代表了80年代形式探索成就的雕塑家為人所忽略,是極不公平的。我想雕塑界應(yīng)做的事情是梳理80年代以來中國(guó)雕塑的個(gè)體創(chuàng)作,給予中國(guó)現(xiàn)代雕塑的探索者以應(yīng)有的歷史地位。事實(shí)上,正是80年代為數(shù)不多的幾位現(xiàn)代雕塑家引發(fā)了90年代一大批人從城雕轉(zhuǎn)入個(gè)人創(chuàng)作或?qū)⑾喈?dāng)一部分精力投入。
也正是這些個(gè)人創(chuàng)作影響了藝術(shù)院校的雕塑學(xué)子,以至世紀(jì)之交雕塑界呈現(xiàn)出個(gè)人創(chuàng)作活躍、雕塑批評(píng)興起的大好形勢(shì)。在這一過程中,產(chǎn)生了不少卓有成就的雕塑家、如展望、劉建華、向京、李占洋等等,他們的個(gè)人創(chuàng)作非常值得關(guān)注。但關(guān)于他們的作品評(píng)論往往局限于個(gè)人語言風(fēng)格的討論,很少?gòu)纳鐣?huì)空間和精神空間的角度,去言說個(gè)人創(chuàng)作對(duì)公共性的介入。相反,雕塑界關(guān)于公共性問題的研討仍然集中在城市雕塑,公共性問題幾乎全等于公共藝術(shù)問題。
然而,這是兩個(gè)不同的概念,必須加以區(qū)別。公共藝術(shù)是指出現(xiàn)在日常生活和公共場(chǎng)合中的藝術(shù),而公共性則是指?jìng)€(gè)人在社會(huì)生活中分享的權(quán)利以及實(shí)現(xiàn)這種權(quán)利的可能性,責(zé)任和義務(wù)。對(duì)雕塑創(chuàng)作而言,公共性含有雕塑家個(gè)人創(chuàng)作與公共空間、公共權(quán)利的關(guān)系。請(qǐng)注意,這里所謂公共空間,不光是指公共環(huán)境,場(chǎng)地、場(chǎng)所和放置雕塑的所有地理?xiàng)l件,而且包括社會(huì)空間和精神空間,也就是說包括雕塑家個(gè)體意識(shí)對(duì)社會(huì)文化和精神意識(shí)的介入。但在中國(guó)雕塑批評(píng)中,這種介入被關(guān)于集體主義的公共權(quán)利所遮蔽,于是公共性問題變成公共藝術(shù)即城市雕塑如何得到訂單、如何通過方案、如何完成工程、如何分配利益的問題。
從某種意義上講,雕塑創(chuàng)作正面臨兩個(gè)市場(chǎng)的誘惑。一個(gè)是公共雕塑市場(chǎng),在這個(gè)市場(chǎng)中國(guó)家資本以權(quán)利資本的方式運(yùn)作金錢資本,官方意識(shí)形態(tài)和利益潛規(guī)則起著主導(dǎo)性作用,此一范圍內(nèi)討論藝術(shù)的公共性其意義極其有限。在尚未真正樹立公民權(quán)利的中國(guó)社會(huì)中,這種討論不過是紙上談兵,更需要思考的是“紙”而不是“兵”,是公民權(quán)利問題,是藝術(shù)自由創(chuàng)作即個(gè)體意識(shí)的呈現(xiàn)問題。另一個(gè)市場(chǎng)是正在開始的個(gè)人作品收藏,其運(yùn)作從個(gè)人風(fēng)格開始,受經(jīng)濟(jì)規(guī)律和市場(chǎng)規(guī)則的制約,是有利于個(gè)體創(chuàng)作的。
但操作過度則容易將雕塑家凝固在既成風(fēng)格樣式之中,逐漸失去和當(dāng)下文化現(xiàn)實(shí)的直接聯(lián)系。所以,我們不能把關(guān)于中國(guó)雕塑創(chuàng)作的討論全部納入市場(chǎng)范疇。創(chuàng)作問題是一個(gè)精神問題、也是一個(gè)社會(huì)問題,這才是批評(píng)關(guān)注的焦點(diǎn)與重心。如今學(xué)術(shù)界大談后現(xiàn)代,奧登伯格和杰弗·昆斯成為中國(guó)藝術(shù)的楷模。
其實(shí)對(duì)中國(guó)雕塑而言,在和西方對(duì)話的時(shí)候,是在人家已多跑了一圈的情況下并肩而行的。人家在反省啟蒙主義,我們也在反省啟蒙主義,但啟蒙之于中國(guó)還是一個(gè)巨大而沉重的歷史任務(wù)。80年代一批前驅(qū)者所突現(xiàn)的個(gè)體意識(shí)在今天依然至關(guān)重要,只不過個(gè)體性面臨的問題發(fā)生了變化,并且個(gè)體性本身也因此而發(fā)生了相應(yīng)的變化。雕塑作為傳統(tǒng)架上藝術(shù),在觀念藝術(shù)特別是裝置藝術(shù)的沖擊下,其藝術(shù)形態(tài)變得越來越開放,以至于有些職業(yè)雕塑家發(fā)出了“我雕故我在”的呼吁。其實(shí),“我雕不一定我在”,因?yàn)椤拔摇痹诮裉煲巡幌?0年代,其人格是假定完整的、是自以為確定的。
當(dāng)代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理由是我們生活在一個(gè)充滿問題的世界里,這些問題即使現(xiàn)實(shí)生活不能解決,也必須在精神生活中加以面對(duì)。然而問題不只是對(duì)象化的,不只是屬于環(huán)境、社會(huì)和傳統(tǒng)的,問題同時(shí)也屬于我們自己,我們就是問題的一部分,就是問題本身。對(duì)于這個(gè)世界的問題而言,沒有人是干凈的。生態(tài)問題跟你的出行沒有關(guān)系么?人口問題跟你的存在沒有關(guān)系么?農(nóng)民工問題不只是農(nóng)民的,農(nóng)民工是城市人的需要,是我們的需要造成的。
正是在問題的共同性、共生性和共犯性之中,主體和對(duì)象的關(guān)系發(fā)生了變化,成為互相介入、互相交流的互動(dòng)關(guān)系。在這種情況下,雕塑創(chuàng)作再固守于現(xiàn)代藝術(shù)的樣式主義,難免削足適履。用一句簡(jiǎn)單的話來表述,那就是風(fēng)格必須針對(duì)問題。也許雕塑創(chuàng)作因?yàn)橘|(zhì)材的恒久性,反應(yīng)問題的方式有所不同,但抽離于問題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肯定會(huì)落入政治權(quán)利、慣性意識(shí)和資本運(yùn)作的操控之中。最近弄得甚囂塵上的奧運(yùn)雕塑就是這樣一種操控的典型案例。
個(gè)人創(chuàng)作的國(guó)有化必然會(huì)演變?yōu)檠谏w問題的宏大敘事,而當(dāng)代藝術(shù)的價(jià)值恰恰是因?yàn)樗囆g(shù)家能夠直面問題本身。關(guān)于公共性的討論,必須把問題意識(shí)植入社會(huì)空間和精神空間之中。藝術(shù)問題是知識(shí)、權(quán)利和空間的三位一體,職業(yè)雕塑家的提法在當(dāng)代藝術(shù)中之所以難以成立,就是因?yàn)樗鼉H僅立足于知識(shí)來爭(zhēng)取權(quán)利,忽略了知識(shí)權(quán)利是在社會(huì)空間和精神空間中形成的,是在問題意識(shí)中實(shí)現(xiàn)的。
空間不僅以物質(zhì)營(yíng)造的方式存在,而且以精神想像的方式、以個(gè)體創(chuàng)造的藝術(shù)方式存在。這種存在之于社會(huì)實(shí)踐,則是批判、否定、不認(rèn)同以及邊緣、外圍、底層、野地、另類等等。在這樣一種精神空間同時(shí)也是社會(huì)空間之中,充滿了統(tǒng)治、服從與反抗、斗爭(zhēng)的關(guān)系,充滿了身體、心理、感覺與感受的矛盾,但只有在這個(gè)空間中才有爭(zhēng)取人的自由與解放的可能性。
所以,在關(guān)于公共性問題的討論中,不加分析地排除自由主義思想常常是另有所圖的。自由主義是集權(quán)體制的最大障礙,對(duì)個(gè)人自由優(yōu)先權(quán)的強(qiáng)調(diào),使一切操控人心的力量面臨被暴露的危險(xiǎn)。而個(gè)性的自由生長(zhǎng)和全面發(fā)展,作為一種理想,始終是藝術(shù)所由發(fā)生的起點(diǎn)。我們不能用含糊其辭的大眾話語權(quán)來掩蓋公民話語權(quán)尚未樹立的事實(shí)。
許多公共性討論的參予者“王顧左右而言他”,乃是因?yàn)樗麄円殉蔀楝F(xiàn)行體制的既得利益者,或者,正在期待朝庭招安的金牌詔令與三顧茅廬的知遇之恩。美術(shù)界關(guān)于公共性問題和大眾化問題的討論,顯露出20世紀(jì)90年代以來中國(guó)知識(shí)分子整體坍塌與解構(gòu)的事實(shí),這是好事而不是壞事。解構(gòu)的意義正在于我們真正回到了問題本身,回到了存在問題的思想主體本身。也就是說,我們必須在自我反省中思考現(xiàn)實(shí)問題、文化問題和精神問題,我們才能作為知識(shí)分子而真實(shí)存在。我們只能以個(gè)體的、自由的、互動(dòng)的藝術(shù)創(chuàng)造和批評(píng)寫作,才能證明自我的存在并尋找自我的本質(zhì)。
不管是在社會(huì)實(shí)踐空間,還是在自我精神空間,公共性只能存在于個(gè)體性之中,而大眾化也只能存在于自由化之中。因此我的問題是:沒有個(gè)體性哪來公共性?沒有自由化哪來大眾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