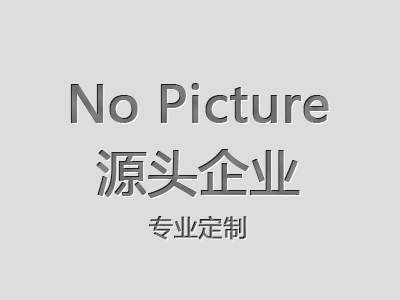自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時起,玩世主義藝術(shù)在中國掀起了一浪高過一浪的高潮,從微小邊緣的群體,發(fā)展到如今主導(dǎo)當代藝術(shù)的時尚風潮,如王朔的小說、賈樟柯的電影、方力鈞的繪畫等等。由于89之后,文化界喪失了整個八十年代已有激情理想和自由氛圍,主流知識分子普遍出現(xiàn)了龜縮,原有文化奴性隨之激活。玩世主義作為一股冷對抗的策略手段,在體制外的文化小群體中萌發(fā),他們以一種曖昧晦澀的藝術(shù)手法,避開正面與主流文化進行交鋒,并獲得少數(shù)文化人、年輕群體和海外人士的追捧。

除了不直接觸及政治神經(jīng)之外,只對精英文化的“偽崇高”表現(xiàn)出一種戲謔性的嘲諷。正是這種民間草根的前衛(wèi)姿態(tài),使玩世主義藝術(shù)成為當代藝術(shù)的主導(dǎo)地位,當影視與美術(shù)在國外取得了成功,尤其一些畫家在商業(yè)上的成功,于是,玩世主義美術(shù)變成了批量出口的時尚藝術(shù),從陣營規(guī)模到風格樣式都出現(xiàn)了多樣化。邊緣前衛(wèi)藝術(shù)從早期反精英走向現(xiàn)在的自身墮落,形成體制內(nèi)“假正經(jīng)”與體制外“偽當代”的一團和氣,生財?shù)墓餐康氖勾蠹叶挤艞壛怂囆g(shù)立場和文化交鋒,連昔日前衛(wèi)自居的藝術(shù)家也共打“祖宗牌”和“民族牌”。

可以說,今日中國藝術(shù)在商業(yè)氛圍下變得極度貧血,喪失了當代性的實質(zhì)意義。李占洋雕塑作品吸收了民間雕塑的語言風格,陋俗形態(tài)和濃艷色調(diào),突出粗俗的欲望趣味,這些都是“冷對抗”的灰色藝術(shù),今天它已變成風格化的時尚趣味,不再具有前衛(wèi)性的藝術(shù)意義,因為它們失去生效的相應(yīng)語境。李占洋近期《收租院》是典型的噱頭作品。象王朔的小說離開那個特定時代的社會語境,便徹底失去了意義,可小說與美術(shù)的載體材料完全不同,后者具有收藏、觀賞和擺設(shè)的價值,并滿足了資本博弈的增值作用,這是有型藝術(shù)品的另一種社會功能。

從方力鈞、李占洋、岳敏君等人的玩世主義風格作品,幾乎一種俗套得不能再俗套、無聊得不能再無聊、乏味得不能再乏味的符號化工藝品,這絲毫不影響資本從中運作所帶來的好處。因此,玩世主義成了一種方興未艾的偽當代藝術(shù),其商機引發(fā)了一股強大的跟風浪潮。李占洋的《新收租院》從當代藝術(shù)江湖中尋找噱頭對象,表面看上去具有“惡搞”的批判姿態(tài),這便是玩世主義的擅長策略,實質(zhì)上比那些赤裸裸的正搞更為肉麻露骨,如栗憲庭、高銘路、艾未未等圈里的大大小小人物,全然成了熱手貨。

這便是反精英的玩世主義藝術(shù)走向一種集體互相打托的墮落局面,它從本質(zhì)上與那些墮落精英群體毫無區(qū)別,難怪方力鈞公開宣稱不再“犯傻”,賈樟柯在一個電視節(jié)目中說:“我不為任何人拍片子,我只是為自己拍片子,我想做商業(yè)就做商業(yè),想怎樣做就怎樣做”。這便是中國當代藝術(shù)內(nèi)在貧血的根源,一切似乎沒有信念原則,所謂“前衛(wèi)精神”、“當代藝術(shù)”不過是玩世的策略手段,如同張藝謀給曾經(jīng)支持和愛戴他的人們一個個響亮的耳光,打得大家都語塞。必須承認,中國精英文化的普遍墮落,同時也不能指望靠“反精英”起家的玩世藝術(shù),他們?nèi)鄙偎枷胝媲榈氖姑校缬嗲镉旰屯跛穼Ξ敶幕饔檬强捎锌蔁o的,類似張藝謀這種歷史機會主義者,他們可以背叛任何一切,根本不在乎藝術(shù)精神或文化良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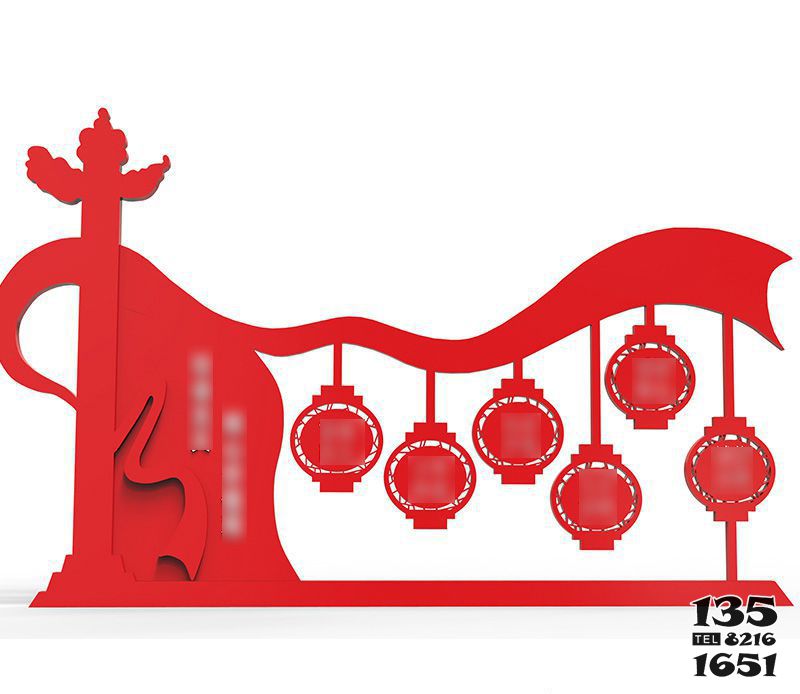
當他們?nèi)〉靡稽c成就,頂上光環(huán),在沒有吃盡老本是絕不收手的;一個王朝如此,一個藝術(shù)家也如此。這便是中國歷史始終不長順的根源,嚴格意義的文化人、藝術(shù)家實在少之又少,只能靠烏合之眾支撐整個歷史命運的輪回轉(zhuǎn)換。毋容置疑,玩世主義藝術(shù)始終都是軟弱的表現(xiàn),它一方面對權(quán)威的不滿而不敢公開對抗,轉(zhuǎn)而采取曖昧的表達方式。
這顯然是缺乏民主制度所引發(fā)文化藝術(shù)的扭曲現(xiàn)象。事實上,玩世主義對主流文化的冷對抗,其中隱含著對權(quán)威的渴望,它自然容易滋生機會主義,這完全符合玩世主義藝術(shù)的性格特點,說明缺乏內(nèi)在的思想真情。20年來主流與邊緣的文化對壘中,藝術(shù)文化沒有進步;社會思想沒有解放;廣大人民沒有勝利;
專制權(quán)力沒有倒臺,假正經(jīng)的文化精英們和偽當代的邊緣藝術(shù)家們卻是贏家。當藝術(shù)家褻瀆藝術(shù),這涉及藝術(shù)起碼的倫理精神。誠然,作為當代藝術(shù)圈的理論家、批判家則很清楚這一點,可他們還繼續(xù)哄抬“偽當代”藝術(shù),象玩世主義藝術(shù)已腐朽得毫無文化意義,如同死水里的惡臭爛魚。以“捧派”自稱的王小箭先生,把李占洋近似“二人轉(zhuǎn)”玩世主義系列作品《人間萬象》、《新收租院》,比作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和史詩敘事方式的荷馬作品,還說它們具有后現(xiàn)代特征“文脈主義”,這種虛夸不失“捧派”本色,以為如今還是“85”期間。
高銘路先生應(yīng)該是位美術(shù)理論大家,可他牽強地將李占洋玩世主義藝術(shù)描述成一種“巴洛克精神和理想”,誰都清楚巴羅克藝術(shù)追求一種高貴典雅的莊嚴,跟李占洋地“二人轉(zhuǎn)”趣味和洛可可風格沒有內(nèi)在統(tǒng)一性。還是王林先生與李占洋的對話道出了一些本質(zhì)。李占洋:“有很多人問我,你這個《收租院》是什么意思?是批判,諷刺還是調(diào)侃?你認為是什么?”王林答道:“我覺得什么都有,也什么都不是,就是作品本身,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去探討分析。
從現(xiàn)在作品給人的感覺來說,有些作品的語言方式應(yīng)該注意。你的雕塑人物塑造與眾不同,帶有一種特別世俗甚至是低俗、惡俗的味道,故意不做到位,有點垮塌,比較肉感,表面上有些凹凸不平、疙疙瘩瘩的東西,著色以后帶著病態(tài)的情色。這種塑造方式很重要,就是你的藝術(shù)觀念的體現(xiàn),也就是觀念性本身,因為所謂觀念就是切入問題的創(chuàng)作方法。但這一組中的有些作品,也許是助手幫忙的緣故,做得太光、太實,回到學(xué)院寫實功夫上去了。是不是放大成真人大小以后,需要對原有技法加以調(diào)整,但不能放棄個人創(chuàng)作中與眾不同的東西。
用學(xué)院寫實功夫來做,觀念很容易變成概念,變成反諷的圖解。藝術(shù)是很微妙的東西,過猶不及,稍縱即逝,要抓住那種洛可可式的虛假感和中國暴發(fā)戶的粗俗性,不要急于求成。今天的中國人太急功近利了,中國美術(shù)界尤其如此。”艾未未和李占洋對話似乎反映出中國“當代藝術(shù)”圈內(nèi)的自戀與無聊。
盡管艾未未認定李占洋作品是“很黃很暴力的敗壞世風之舉”,但卻說“栗憲庭撞車”、“艾未未喂羊”等小泥人作品是“偉大的作品啊!”。可謂是“官官相護,名家互捧”,足見當下的前衛(wèi)藝術(shù)家多么缺乏批判精神。總之,不論吳冠中還是羅中立,方力鈞還是李占洋;他們的藝術(shù)已不再有任何當代性的文化積極意義。
假如中國社會文化還需要前進的話,必須徹底拋棄這些腐朽而扭曲的偽當代藝術(shù),重新構(gòu)建一種嚴肅、真情、健康的藝術(shù)生態(tài)。這一切,只能寄望于年輕一代人,一代人不行便兩代人,兩代人不行就三代人。只要一代代藝術(shù)青年的意識覺醒,充滿激情勇氣、創(chuàng)造精神、思想真情,中國總有成為制度健全、思想自由和文化發(fā)達的文明社會。李占洋:我的《“租”——收租院》《超二人傳:李占洋的新編收租院》《“租”情節(jié)還是“租”精神?
——李占洋…》《歷史的在場與在場的歷史——李占洋雕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