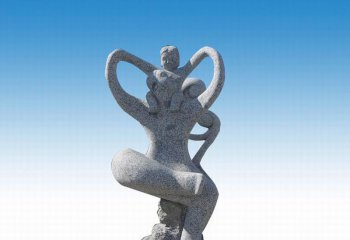西方前衛藝術早已凝固為歷史,二戰后直到70年代歐美當代藝術持續爆發的震撼,也早過去了。八九十年代迄今,他們的當代藝術越來越干凈、好看、聰明、多元,但真的缺乏“野性”,后起而遲到的中國當代藝術因此顯得生猛奪目,令人興奮,就像中國的經濟奇跡一樣。“中國龍”崛起。“印度媽媽”蘇醒。“越南小老虎”仰天一吼,辨認自己的嘯音…在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大陸,如果試圖在被資本照耀的各個角落尋找傳奇和童話,定能如愿。這其中,當代藝術尤其像“灰姑娘”。4月9日香港蘇富比2008年春拍會上,劉小東的十八聯油畫《戰地寫生:新十八羅漢像》以6192.75萬港元的價格成交,成為中國當代藝術僅次于蔡國強《APEC景觀焰火表演十四幅草圖》的第二高價。

一位阿根廷收藏家擁有數量最多的中國當代影像作品。她說,不要誤認為亞洲藝術品是靜態的、老掉牙的東西,它們正在反射藝術家們所處的劇烈變動的時代。收藏家們愿意為“承載歷史片斷”的那些物件動用百萬英鎊。從80年代中期一路走來,中國當代藝術家從模仿西方,到發明出一套個人符號,進而將各自的符號變成巨大榮耀和巨額利潤。

他們試探了令人眼花繚亂的國際最新樣式和手段,究竟能在本土刺激出怎樣的創造力和怎樣新鮮或者怪誕的產品;試出了商業利潤和收藏家的錢袋,究竟有多驚人;更重要的也許是,在如此擁擠的這片土地上,他們中的一些人終于能將個性的觸角向著遠處伸展。仲春,上海,“仍然在野”的藝術家陳丹青與本刊記者探討了這個話題。

記者:最近,紐約某雜志在一篇介紹中國5位當代藝術家的文章里說,張曉剛是早期畢加索、馬格里特和Pixar的混合體;艾未未是杜尚、杰夫·昆斯和搖滾樂隊“性感小子”的混合體,等等,雖然有搞笑的成分,卻能啟發我們思考中國當代藝術的血統問題:它是怎么來的?陳丹青:這很有意思。

問題是,譬如,中國目前至少有30種以上比較像樣的藝術雜志,每期上市,少說也得300篇文章,多有談及美國藝術的,然后有位美國人引述其中一篇的一小段話,對美國人說:看哪,中國人這樣評價美國藝術!——你會覺得準確么?張曉剛確有馬格里特的被稀釋的影響,但和畢加索可不沾邊;艾未未得自安迪·沃霍遠多于杜尚,而他比杰夫·昆斯高明多了。以上也只是我的個人偏見,不足道。幾代中國油畫家的“血統”,或者說“輸血管道”,當然全部來自西方,部分來自日本——日本也來自西方——我要隨即糾正:輸管內并不是真的“血”,而是西方各種藝術的復制品。

記者:紐約國際攝影中心策展人克里斯托弗·菲利普斯1999年在北京初見中國當代藝術家和他們的作品,感受到“一種野性,并且充滿力量;被作品的想象力和獨創性所震撼”,他意識到這樣的盛況在藝術史上屬于一個世紀只會出現一兩次的“井噴”。您覺得這個判斷言過其實,還是恰如其分?陳丹青:菲里普斯說得對。“野心”、“力量”、“想象力”的確是優秀中國當代藝術給予外人的印象。不過有個前提:西方前衛藝術早已凝固為歷史,二戰后直到70年代歐美當代藝術持續爆發的震撼,也早過去了。
八九十年代迄今,他們的當代藝術越來越干凈、好看、聰明、多元,但真的缺乏“野性”,后起而遲到的中國當代藝術因此顯得生猛奪目,令人興奮,就像中國的經濟奇跡一樣。記者:您在《退步集》中將劉小東和方力鈞稱為豪杰。
平心而論,今天出現在西方收藏家名單上的那些人,是被這個時代“選中”的偶然,還是一種個人特質的必然結果?陳丹青:單論寫實人物油畫,我不知道劉小東能否在當今世界同類畫家中找到對手,他遠遠超越了佛洛依德和艾瑞克·費雪。
部分因為小東的強悍“特質”,部分是因為世界范圍內寫實人物畫早已沒落了。陳丹青:3月間,紐約古根海姆現代美術館為蔡國強舉辦大型回顧展,參觀人數為該館舉辦德國波依斯個展以來所僅見。同時,紐約頂級畫廊瑪莉·布恩上城分廊為劉小東舉辦個展,下城分廊為艾未未舉辦個展——西方藝術家不可能得到比這規格更高的展事了。
我以為這三位同志恰好是最精彩的中國當代藝術家。記者:真巧,蔡、劉兩位正分坐中國當代藝術拍賣紀錄的頭兩把交椅。這些天文數字對藝術家會產生怎樣的影響呢?陳丹青:就我與小東和國強的接觸,他們不談錢,同時正在旺盛的狀態中。我沒辦法鉆進他們肚子里考察究竟,但市場好,無論如何會增添自信,但對真正的強者,沒市場照樣激發自信,自信是內在的稟賦,它會伴隨焦慮,但不為外界左右。困難的是初出道的新人,藝術市面外表看來太像賭博與夢境,但很少有人愿意細忖一個所謂成功藝術家背后是怎樣孤單而猛烈的工作。記者:那位菲利普斯先生還有后話,他說:“世界發現了中國當代藝術,但它改變的速度之快讓人難以置信。
有些藝術家,1999年我見到他們時幾近貧困,但現在他們極為富有,常常雇傭大量助手來幫助完成作品。然而,金錢的席卷僅僅拉動了作品的‘價’,卻沒有使中國當代藝術變得更好或更有意思。令人沮喪的是,現在我去訪問藝術家,已經很少聽到關于藝術的談話了,通常是最近一次拍賣的結果,或誰和誰的作品有沒有被薩奇那樣的百萬收藏家買去。”您對此作何感想?陳丹青:不論生熟,我結識的美國藝術家大約20多位吧,其中包括來自歐洲、日本和中東的移民,幾乎都有畫廊。
不論什么場合、氛圍,各自介紹后,話題立即進入藝術,從不相互打聽或談論價格,更不談拍賣市場。媒體報導拍賣專訊有上百年歷史,早已是公眾熟悉的日常新聞,所以純資本主義社會的藝術家非常清楚市面,但不熱衷談錢。他們大約三群人,三種話題:一類是廣義的藝術家,不論窮、富、著名、無聞,只談文藝,或者政治與性;一類是畫廊業人士,議論市場,但口吻絕不聳動,只是平靜的信息交流;再一類就是拍賣行中人,精明鋒利,高度專業談生意,我根本聽不懂。
以我的寡陋,以上經驗很可能片面。股票、拍賣,在美國是一小撮人的話題,中國市民街頭巷尾談股票,中國藝術家群相談價格談拍賣,人家會鬧不明白。除了很年輕的藝術家,我已不太能遭遇只談藝術的傻逼。為了不犯傻,我也學會東拉西扯,盡管除了多年師友,我和藝術圈久已不來往。記者:也有一些藏家認為某些當代中國藝術家的作品被低估了。您認為50年后,會追認出幾位中國的杜尚或者安迪·沃霍么?
陳丹青:假如真有誰被埋沒,那是浪漫的故事。眼下的劇情足夠跌破眼鏡,但并不浪漫。大欠公正的是對老前輩。民國畫家、共和國第一代老畫家,許多名角至今不在市場名單內。西方則除了凡·高、塞尚那一輩,此后幾乎沒有委屈過哪位真正的天才。記者:據薩奇畫廊統計,中國現有兩萬多位畫家,每年至少1萬名學生從美術院校畢業。但北京和上海的當代藝術畫廊加起來不到200家。如果您現在剛畢業,會是什么心態?陳丹青:中國藝術學院的增長比畫廊數增長快。如果把全國各省市非人文類大學的藝術生源算進去,再劃去設計類實用美術學生,每年純藝術畢業生不止1萬名吧?
我的學生求職時找的都是林業、政法、農學院等等大學屬下的美術學院。我不知道當今世界哪個國家有這么多藝術學院。我要是現在畢業,心態大約就跟一條野狗一樣。雖然我不確知野狗有沒有“心態”,但我記得它們的眼神。從成才率看,千分之一的畫家能賣畫,能自謀生路,便是謝天謝地。
目前中國年輕藝術家的機會既不太多,也很不少,我剛回國時還在上學的青年,好幾位已經一幅畫能賣數萬元,甚至更多,當然,這些個例畫得很不壞。總之,一個曖昧的成功游戲忽然降臨,但一個淘汰機制還沒以正常方式出現。何止藝術,太多曖昧的行業和個人在中國受惠于近年夢境般的市場,如藻類…論人口概率,西方藝術家遠多于中國,論藝術家的成功概率,則中國人似乎高于西方同行,別忘了,沒一個國家有如此龐大的學院系統和官方機構長期承受千萬藝術家的職業“流量”,而且還會承受很久。
就稅收看,美國政策對藝術家優惠,因為貧窮藝術家占絕大部分,年收入往往低于交稅額。記者:巫鴻曾經提到過“作品化”的危險,他說現在的年輕人著急,沒事兒就要做大作品,這很讓人擔憂。您怎么看這種情況?陳丹青:誰要畫得大,請盡管大吧。繪畫的驅動力部分是體能而不是智力。只是再大的畫大不過廣告,如今電腦噴繪廣告可以大到覆蓋整座摩天大樓。八九十年代歐美也作興制作超尺寸大畫,原因很簡單,現代畫廊和美術館展覽空間是過去的數倍甚至數十倍。
近十多年大畫不那么時興了,我在紐約畫廊見過郵票大小的油畫,畫得好極了。我是畫大畫的一代,14歲就在大型工廠制作的六七米甚至十來米大鐵板上畫領袖像,毛主席的眉毛就有一米多長。中國藝術家眼下興致正高,加上著急:瞧著同班或下屆畢業的哥們發跡發財,你便是菩薩投胎也難裝得若無其事。往大了畫吧,要是賣不了,很快你會發現沒地方存放這些又大又沉布滿灰塵的廢物。記者:在策展人馮博一眼里,確實有一批80后、90后的當代藝術作品新鮮、有激情、富有創造力。
就您視野所及,有沒有發現可以燎原的種子?陳丹青:青春不等于才華,但才華靠青春壯膽。青苗一撥撥竄上來,總有才華橫溢的人。我所以痛恨藝術學院這一套,那是青春的屠殺。拿什么鳥學位!20歲左右就該放手創作,美術史上多數經典是25歲前后的小青年弄出來的。
至于燎原不燎原,我可不知道。吃掉70年代生人的是80后,而今90后眼瞧著竄上來,一嘴汗毛,皮嫩肉緊。代際的緊張感是近年趨勢,我在校園常遇見20來歲的女孩說:啊呀,我老了。整體看,每一代藝術學生的百分之九十九會成為魯迅所謂的“一盤子綠豆芽”。記者:您覺得中國當代藝術的致命問題是什么?它和現實是一種怎樣的關系?陳丹青:中國當代藝術就是中國的現實。
真的“當代藝術”有內在邏輯,自為自律,“中國當代藝術”則整體上是國情的肌理之一。它長期被壓抑、被扭曲,因為它既來自國情又受制于國情;它騷動、富活力,竭力拱破國情;它跳躍猛進,但看不清從成長走向成熟的軌跡;它幾乎無所不為,但并不自由;
它對它所追趕的西方典范滿懷廂愿,但始終以自己的方式滋生蔓延;它被忽然夸張放大,但總比不曾發生,或被嚴厲管制要好得多;它遠未發作,但切忌亂來、翻船,不然很糟糕…這些癥狀不都是國情么?改革開放是條活路。中國式當代藝術如今又酷又蠻,一臉青春痘,是不是有點像計劃生育政策外非法降生的孩子?
怎么辦呢,看來還得在“科學發展觀”指引下看看能否“可持續發展”,雖然種種必備條件其實很可疑,但“致命”一詞怕是言重了。哪個領域都和國情綁在一起,當代藝術只是其中之一,目前它正被歸結為經濟指標,任何清醒的意識均難抵御數據的暈眩,暈眩總不是常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