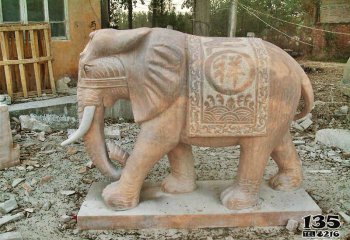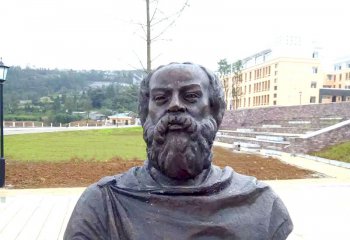杜尚和博依斯以后,當藝術的能指逐漸被泛社會化,實際上藝術與生活的嚴格界線已經被撤除,生活成為藝術完全是可能的。所以前衛藝術逐漸出現了“藝術就是生活”或“生活就是藝術”的藝術觀念,博依斯的“一切都是藝術”、“社會就是雕塑”本質上也與這樣的藝術觀念類似。但這樣的藝術觀念在整個前衛藝術階段只是使藝術獲得了生活的形式,藝術家做的是具有生活形式的藝術,或者強行將某種生活宣布為藝術。前者如謝德慶的“做一年”的行為藝術《囚禁》、《戶外》、《藝術/生活》和《不做藝術》;

后者如杜尚將其晚年的整個生活當作藝術。它們要么就是將生活作為藝術的形式,而不是藝術本身,藝術與生活還是分離的;要么就是失去了對生活的“意義”判斷,使藝術不再是對“有意義的生活”或“生活的意義”的發現,藝術成為“平庸的生活”而不是“有意義的生活”――自由與尊嚴的生活,此時的藝術表面上很生活,但實際上早已遠離了生活,藝術與生活同樣是分離的,因為“無意義的生活”本質上不是人的生活。

前衛藝術發展的這兩種情況,由于藝術的能指仍然是“不明確性”的,所以藝術最終還是“無意義”的。前衛藝術從開始發展到后現代藝術階段,在不可避免地走向藝術的“生活化”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藝術的“平庸化”、“虛無化”、“無意義化”,它其實沒有發展出藝術新的可能性,藝術實際上面臨深刻的困境。

這樣,以藝術能指的“不明確性”為藝術本體論的歷史前衛藝術、后前衛藝術以及后現代藝術,實際上只是樹立了“藝術就是生活”或“生活就是藝術”的表面藝術觀念,但卻無法真正使“藝術就是生活”或“生活就是藝術”的藝術觀念成為有效的藝術實踐,即它們還無法找到藝術何以成為生活或生活何以成為藝術的方法論。生活如果要真正地成為藝術,或藝術要真正地成為生活,需要改變前衛藝術的本體論結構,即需要將藝術能指的“不明確性”,改變為藝術能指的“語境化”的“問題傾向性”。

在“問題語境”中,藝術因能指的“問題傾向性”而產生意義,藝術避免了“平庸化”、“虛無化”和“無意義化”。而在“問題語境”中的藝術行為本質上就是生活,因為生活本質上就是問題的生活;而且生活行為也完全可以處在“問題語境”中,同樣可以因行為能指的“問題傾向性”而產生意義,從而成為藝術。于是藝術和生活無法再行區分,它們實際上成為同質的事物。這個時候,我們才能說“藝術就是生活”或“生活就是藝術”。

這是一種新藝術方式的本體論和方法論,這種新藝術方式就是我所說的“問題主義藝術”,它實現的方法論就是“問題社會學”。“問題主義藝術”已經是對傳統藝術、現代主義藝術、歷史前衛藝術、后前衛藝術在本體論和方法論上的超越了。傳統藝術是能指與所指的合一,方法論是能指的固定典型化,所以傳統藝術是“來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現代主義藝術是能指與所指的模糊對應,能指離開固定所指,方法論是能指的無限想象,所以現代主義藝術是“生活中的夢幻”;
歷史前衛藝術是能指與所指的兩極分化,方法論是能指的陌生化,所以歷史前衛藝術是“生活中的巫術”;后前衛藝術是能指與所指的若即若離、似是而非,方法論是能指的泛社會語境化,所以后前衛藝術是“平庸的生活”。而當代藝術應該是能指與所指的互動和衍生,方法論是能指的特定問題語境化,所以當代藝術是“有意義的生活”。
今天,在本體論的超越意義上,當代藝術實際上就是“問題主義藝術”,它就是“藝術就是生活”或“生活就是藝術”的有效實踐。因為“問題主義藝術”從獨特的角度對“社會問題”的提示,直接有利于人的進一步完善,從而在終極層面增加人之所以為人的意義。這種有利于人的進一步完善的行為,可以說是當代的人作為自由的人的生活的第一需要。這樣的藝術本就應該內在于我們的生活,只不過我們還無法覺悟到將“問題主義藝術”作為我們的自由的生活的必需,所以我們總是習慣地將“問題主義藝術”當作我們的藝術而不是我們的生活。
而當我們將“問題主義藝術”內化于我們的生活,或者說將我們的生活變成為了人的進一步完善――即為了讓人更成其為人的行為的時候,我們的生活就成了藝術――“問題主義藝術”,哪怕我們不把它當作藝術來看,它仍然是藝術,而且是更有意義的藝術。
這里,我們也有了一個很好的“生活就是藝術”的例子。最近,一名美國男子托馬斯·比提作為丈夫懷孕的行為成為新聞媒體的熱點。托馬斯·比提本來是一名女性,8年前做了“變性手術”,成為一名法律意義上的男性,后來與女性南茜合法結婚組建了家庭。由于妻子南茜患嚴重的子宮內膜異位癥,切除了子宮,失去了生育能力。而托馬斯·比提雖然做了變性手術,但只做了胸部改造手術和睪丸激素治療,而保留了內外生殖器官,因此他仍然具有懷孕生育的生理功能。托馬斯·比提為了滿足生兒育女、組建一個完整家庭的夢想,在法律意義上已經身為男性的托馬斯·比提決定親自懷孕生一個孩子。
由于“變性男人”的懷孕存在巨大的法律、宗教、倫理、生物學等爭議,托馬斯·比提的生育要求遭到了所有醫生的拒絕。因此他們只得從一個冷凍精子銀行購買了幾小瓶冷凍精子,在家中為比提進行人工授精,并通過第二次人工授精而成功懷孕。
上述“變性丈夫懷孕”的生活行為就是一個“生活就是藝術”的經典例子,之所以說它是“藝術”,那是因為它完全進入了“問題主義藝術”的本體論。“變性丈夫”的行為的能指明確地指向了當下世界文化針對“變性丈夫懷孕”的眾多復雜的法律、宗教、倫理、心理等方面的問題,并明確地以當下“進步”的人文立場質疑了世界范圍的有關法律、宗教、倫理等文化的既定秩序,從而有利于人的進一步解放――自由與尊嚴。“變性丈夫懷孕”行為的方法論顯然是“問題社會學”的,因為他的整個行為都要面臨和克服既定的法律、宗教、倫理等文化秩序的壓力,沒有一定的社會學準備,是不可能發生并堅持“變性丈夫懷孕”這樣的行為的。
所以,托馬斯·比提要向媒體公開說:“我是一個人,我有權生育。”;“我們想擁有一名生物學上的孩子,不管是男孩子還是女孩子,這僅僅是人的一個愿望。對于我的妻子來說,我是她的丈夫,代替她生孩子。我將是我女兒的父親。我的妻子將是女兒的母親。我們將組成一個完整的家庭。”。盡管托馬斯·比提夫婦并不是藝術家,他們的行為也并不一定是出于文化學的考慮,但在爭取自由與尊嚴的意義上,顯然他們并不是完全不自覺的,只不過他們對自由與尊嚴的爭取變成了習慣性的自覺行為。從這個意義上說,“變性丈夫懷孕”行為就是“人權藝術”。
而當人人對自由與尊嚴的爭取都變成了習慣性的自覺行為的時候,那種嚴格藝術意義上的藝術和藝術家將不再存在,或者說我們不再需要藝術和藝術家,因為“生活就是藝術”,“人人都是藝術家”。這就是藝術的“終結”――就像我在《圄于藝術的內部——金鋒的批評》一文的結尾所說的:“藝術‘終結’在人的自由與尊嚴的生活中。在人的自由與尊嚴的生活中,藝術的‘終結’就是藝術的‘永生’。
”。當然,由于生活永遠無法達到這種自由的終極狀態,所以藝術和藝術家永遠不會消失。但藝術本體的轉型及其對生活的介入已經極大地拓展了當代藝術的發展空間,藝術找到了新的存在方式――生活。在這樣的存在方式中,藝術才真正地回歸了人本身。藝術不再是藝術,而是人的有意義的生活,或者說藝術是“不是藝術”的藝術。
也許有人說,這一“變性丈夫懷孕”行為可能是一個騙局,就像幾年前,也有一個名叫李明維的男子便被一個“男性懷孕”網站報道為世界上第一個懷孕的男人。最后證實是畫家維吉爾·王“愚弄”世人的“杰作”。然而,無論真假,“變性丈夫懷孕”的行為都是一件“問題主義”的行為藝術經典作品。
因為,在前衛藝術的能指演變的“問題指向”中,藝術不僅重新獲得了先鋒文化的批判性,而且更獲得了一種新的具有無限可能性的存在方式――“生活”,而“變性丈夫懷孕”的行為的能指完全有了豐富的“問題指向”。所以在我的“問題主義藝術”理論中,“變性丈夫懷孕”生活行為不僅是藝術,而且是更前衛、更有意義的藝術。面對今天那些在陳舊的前衛藝術方式下的無聊藝術作品,“變性丈夫懷孕”這一“藝術/生活”的意義就在于:它告訴我們――藝術就是人的自由與尊嚴的生活。吳味《“問題主義藝術”爭論》,《雅昌藝術網》2008年3月“博客――吳味”欄目。
、、《美國“懷孕丈夫”電視露面:我有權生育》,《騰訊網》時尚頻道-首頁推薦/優品人生。吳味《圄于藝術的內部——金鋒的批評》,《雅昌藝術網》2007年8月“專欄作者――吳味”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