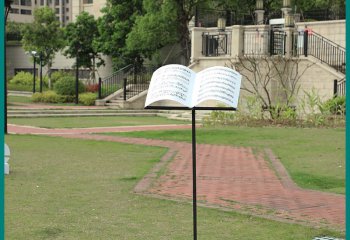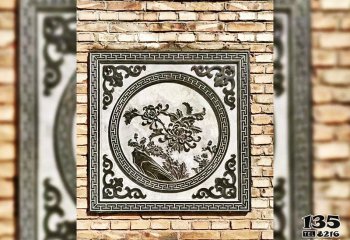麥積山石窟像是藏在西北大地密林深處的一座農(nóng)家柴垛,但是,在它“望之團團”“狀如農(nóng)家積麥之垛”的身體里,卻散發(fā)著佛的氣息。如果這可算作一個歷史之謎的話,我愿意以“無知者無畏”的姿態(tài)去破解其中的秘笈——假設(shè)歷史是一條沒有未來的小徑,然后,我從公元2006年夏日的一個午后沿路返回,返回到那個遙遠得幾近模糊的年代——公元前138年,張騫受漢武帝之命,出長安,翻關(guān)山,渡黃河,越河西,經(jīng)伊梨,過蔥嶺,進入西域。

風餐露宿,往返數(shù)次。終于,這條狂風吹刮沙塵飛揚野獸出沒的荒涼之道,因為絲綢而溫柔起來。佛,也沿著這條路,來到了中國大地。麥積山石窟,其實就是佛從遙遠的西域走向中原時留在秦州大地的一個巨大腳印。2杯度,一位“輕疾如飛”的高僧,一位因“常乘木杯流水,因而為目”而被略去真實姓名、戲稱為“度杯”的南北朝時期的冀州人。在他的不惑之年以前,奇跡般地在麥積山上“疏山鑿洞,郁為凈土”,成為麥積山石窟史的第一位賣力的“農(nóng)夫”。
他汗流浹背地在這里開始了一場漫長之旅。其實從開始,他就是為一座佛的遺址而埋頭工作。麥積山石窟,是佛的遺址,是時間的遺址手藝的遺址心靈的遺址。除此之外,它還能是什么的遺址呢?3我一直堅信,雕塑是一門心與手打造的大美而不言的藝術(shù)。麥積山石窟,自后秦始,歷經(jīng)北魏、西魏、北周、隋唐、宋元,至明清,在漫長的歷史之河里,當無數(shù)的人們用一把一把的泥為佛命名的時候,佛、菩薩、弟子、供養(yǎng)人卻在這座垂直高度142米海拔1742米的奇特山崖上,像走累的旅人一樣歇了下來。
其中的北魏、西魏、北周更像是麥積山石窟的一個個標點符號,像要把時間的影子拉長似的,甚至想讓時間如一塊壞掉的鐘表,干脆停下來。如果停下來,那是為了佛的休息。如果前進出發(fā),那是為了佛的上路。在這段中國歷史上堪稱風雨飄搖的時間里,佛的事,在紛亂戰(zhàn)事朝代更替的縫隙里異常地繁華起來。
當我一次次沉浸于被五代才子王仁裕形容為“萬軀菩薩列于一堂”的北魏石窟的宏大雄偉、西魏石窟童男童女的天真稚氣,以及北周飛天仿佛要飛出壁畫似的飄逸時,我十分愿意生活在那樣的朝代,遠榮利,安貧素,面壁誦經(jīng),潛心修佛。4我更加愿意和那個微笑著的小沙彌,在一場浩大的清風明月里相視一笑。它俯首,側(cè)耳,在麥積山石窟第133窟里靜若處子,在密如蜂房的麥積山石窟里,因面露憨厚且稚氣的笑而被譽為“東方微笑”——那笑得細成一條線似的雙眼,像靜聽,像回味,像領(lǐng)悟,更像一份對佛出自內(nèi)心深處的謙卑。
5在中國四大石窟中,如果說云岡石窟和龍門石窟是以或質(zhì)樸或圓潤的石雕為佛命名、敦煌石窟是以大量壁畫中豐富多彩的顏色為佛命名的話,那么,麥積山石窟就是用一把又一把細小而偉大的泥,為佛命名。泥塑,是麥積山石窟的典型特征。早在茹毛飲血的原始社會,燒陶的出現(xiàn)就已開了泥塑的先河。但是,麥積山石窟的泥塑,像是把這門手藝推向美的極致一樣——生動、逼真、傳神——其實,幾乎所有美妙的形容詞都會在這里顯得遜色無比——當一把一把的泥土和砂子、棉花、紙漿甚至雞蛋米汁在蓊郁葳蕤的麥積山相遇時,泥土的神秘熠熠動人,泥土的偉大品質(zhì)也毫無愧色地承擔起麥積山石窟作為“東方雕塑陳列館”的光榮角色。
麥積山石窟,面對你,蕓蕓眾生不僅要為佛三鞠躬,更要為腳下廣闊無垠的大地,三鞠躬。6想像中,在那舊得發(fā)黃的時光里,面對深山巨壁,青燈一盞,一筆一畫地為佛畫出說法圖、三佛圖、經(jīng)變故事圖以及城池、樓閣、龍、鳳等等,該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畫出第127窟壁畫的人,就更加幸福了。127窟右壁上部的“西方凈土變”圖,前壁上部的“七佛圖”,頂披后部的“穆天子拜見西王母圖”,窟頂左右的“”薩壤那太子舍身飼虎圖”,窟頂前披的“瞇子本生圖”——它們的聯(lián)手,才讓這座石窟成為中國佛教壁畫藝術(shù)的集大成者,成為中國繪畫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被后人仰首凝望。
我常常想,做一個麥積山石窟壁畫里高髻細頸削肩的女供養(yǎng)人,或者使勁擊鼓的伎樂,都是幸福的。7一個美好的夏夜需要月亮,需要星星,需要輕柔的夜風以及一閃一閃的螢火蟲——石窟藝術(shù)博大精深的美,除了一尊一尊大大小小的佛造像,除了五顏六色的壁畫,還需要檐、鴟尾、閣、柱這些名詞所賦予的深刻意義。而麥積山石窟中的崖閣建筑、壁畫建筑以及寺院建筑,猶如在這間巨大的房子里拉家常的窮親戚,互相取暖,并且構(gòu)成了整個石窟建筑的皇皇大美。
北周大都督李允信為其王父所造的被人們俗稱為第四窟的“上七佛閣”,外鑿面闊七間單檐廡殿頂?shù)?a href="/diaosu/3033-1/" target="_blank">大型佛殿,后壁鑿七座帳開帳形龕,前檐八柱,后壁七座佛帳列列如風。這是麥積山石窟中最為宏偉最驚心動魄的一座。從南到北足跡踏遍祖國大地的庾信,在其《秦州天水郡麥積巖佛龕并序》中不禁嘆曰:壁累經(jīng)文,合重佛影,雕輪月殿,刻鏡花堂,橫鐫石壁,暗鑿山梁。
一次次滿懷敬畏地走近它,一次次穿行在散發(fā)著古舊氣息的空間上的遺存時,我都會模仿著庾信的樣子,喃喃低語這二十四顆漢字。因為我藉此而懂得了朵樓,懂得了“對雷”,也懂得了火災(zāi)、兵燹,曾經(jīng)頻繁的地震以及小隴山特有的潮濕對他們身體以及心靈的巨大傷害。8一場風趕著另一場風,在時間的隧道里走——因為佛的盛大,麥積山石窟不知不覺地成為旅人們——漫漫長夜內(nèi)心無處安放的旅人們的避難所。
庾信、杜甫、胡纘宗走過——在他們的身后,還有王仁裕、王了望、任其昌…一個個低頭走過的影子,被落日重疊在一起,加重著一個又一個時代的苦難。而我隔著時間,仿佛聽到了他們出自內(nèi)心深處的嘆息,在歷史的小徑上響個不停,如同受傷的一只又一只蛐蛐。9不知道,唐乾元二年的秋天,當詩人杜甫一臉倦怠地登臨麥積山石窟的一天,天空干凈得有沒有云朵,但那年秋天的秦州古城,卻因為這一個自長安風塵仆仆而來的詩人,秋意里的憂傷,被加重了。
兩鬢染霜兩目蒼茫的杜甫,自秋花危石的東柯谷一路蹣跚走來,盡管他面對的是剛剛經(jīng)歷了一場地震的麥積山石窟,但還是撿拾起到了人間的小小快樂。他不禁低語了:“野寺殘僧少,山圓細路高。鹿香眠石竹,鸚鵡吸金桃。亂石通人過,懸崖置屋牢。上方重閣晚,百里見秋毫。”顯然,有一絲淡淡的喜悅掠過杜甫的額際,旋即,他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命運似的,內(nèi)心巨大的孤獨又一次將他置于荒草叢生的幽幽小徑,徘徊不前。
10秦州民謠曰:“砍盡南山柴,修起麥積崖。”秦州民謠又曰:“積木成山,拆木成功。”關(guān)于這些來自民間的謠諺,我曾經(jīng)在古代的典籍里找到了最好的注腳——據(jù)明代《玉堂閑話》載,關(guān)于麥積山石窟,“古記云,六國共修,自平地積薪,至于巖巔,從上鐫鑿其龕室神像,功畢,旋拆薪而下,然后梯空架險而上。
”一項浩大而繁復(fù)的工程。當麥積山石窟像一朵又一朵樸素之花漸次綻放在莽莽隴山時,一個傳奇被深深地鐫刻在了秦州大地。然而,歷史還是沒有記住它們的名字——盡管麥積山石窟也有開窟造像者的記載,甚至也留下了部分工匠的姓名,如明天啟年間的鐵匠王化明等——但是,更多繩墨規(guī)矩的工匠在歷史卷冊中因為名分闕如而三緘其口,沉默不言。所以,請允許我以佛的名義,向這些被文化藝術(shù)正史打入另冊的消隱的大師們致以崇高的敬意:你們,是侍從了藝術(shù)并最后歸真于藝術(shù)的大師!11麥積山石窟,一場風吹來,你身邊的落葉晃了晃,而你像一座巨大的石像巋然不動,低頭思考著什么。
可你在想什么呢?人類的卑微無法揣度出內(nèi)心純潔與澄明之間的距離,人類只有在被苦難擊碎了心靈的時候,才想起你。可你不怨恨,也不嗔怪,心靜若水。但我猜想,你一定看在眼里記在心上;你也一定思量著如何與麥積山以西的敦煌之佛聯(lián)起手來,共同為這個言不由衷的時代把脈會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