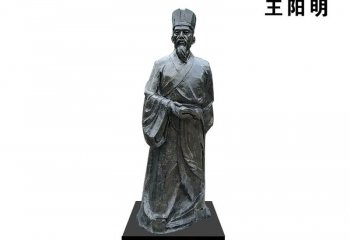《禮記》里說(shuō)的:“同門(mén)曰朋,同志曰友”,讓我真心稱(chēng)之為“朋友”的須得是同類(lèi),一起學(xué)習(xí)、共同進(jìn)步且志向相仿的人才是朋友。泛泛應(yīng)酬的那種,算不得。尚榮與我在同一間大學(xué)里教書(shū),他在哲學(xué)系,教宋明理學(xué)和禪宗思想,我在美術(shù)學(xué)院,研究中西方美術(shù)史。我們之間的交往,緣于工作;
而友情的產(chǎn)生,則源于相似的志趣——對(duì)知識(shí)的好奇和對(duì)藝術(shù)的熱愛(ài)。尚榮常讓我想到一個(gè)詞——“文質(zhì)彬彬”。雖說(shuō)這個(gè)成語(yǔ)已經(jīng)被現(xiàn)代人用成了一個(gè)陳詞濫調(diào)[cliché],幾乎等同于講文明懂禮貌,但它的本義是極好的:“質(zhì)”者,樸素的秉性;“文”者,華美的文采。
一個(gè)人既篤實(shí)可靠又才情橫溢,怎么不讓人歡喜,愿意親近呢?尚榮就是這樣一個(gè)人。他為人誠(chéng)摯,不妄言,無(wú)綺語(yǔ);做事踏實(shí),肯擔(dān)當(dāng),不怕艱難,不畏瑣碎。這些都是他的“質(zhì)”之所在。孔子說(shuō)“繪事后素”,他的文采便是在這樣厚實(shí)的生命底子上開(kāi)出的花,風(fēng)姿卓越,生機(jī)勃勃。尚榮的“文”體現(xiàn)在兩個(gè)全然不同的領(lǐng)域。
一是學(xué)術(shù),他是一位勤奮的學(xué)者,撰文、著書(shū)、做科研、帶學(xué)生,皆有為人稱(chēng)道的出色成果。另一個(gè)則是藝術(shù),恐怕很少有人知道這位哲學(xué)系的副教授曾是油畫(huà)和雕塑專(zhuān)業(yè)的科班出身,而且至今一直在默默堅(jiān)持著藝術(shù)創(chuàng)作。在南大這樣的高校里,科研、教學(xué)的任務(wù)頗為繁重,尚榮為什么還執(zhí)著于藝術(shù)創(chuàng)作呢?以我看來(lái),他不是簡(jiǎn)單地尋一個(gè)閑暇時(shí)的愛(ài)好,而是抱著“為生命而藝術(shù)”[artforlife’ssake]的信念。這既不同于王爾德的“為藝術(shù)而藝術(shù)”[artforart’ssake],更不同于“為生計(jì)而藝術(shù)”[artforliving’ssake]。
“為生命而藝術(shù)”,是把藝術(shù)與生命相融合,生活中的每一次感動(dòng)、每一點(diǎn)領(lǐng)悟都是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源泉與動(dòng)力,而創(chuàng)作出的藝術(shù)作品又會(huì)反過(guò)來(lái)滋養(yǎng)生命,塑造更好的自己。這樣的藝術(shù),才是讓人成為人的藝術(shù)[theartofbeinghuman]。《愛(ài)蓮說(shuō)》是尚榮為宋代理學(xué)大師周敦頤而塑的一尊全身像。
周敦頤手執(zhí)一朵香遠(yuǎn)益清的幽蓮,正仰首遠(yuǎn)眺,他神情蕭散,朗然如日月之行。我心下贊嘆:這雕塑風(fēng)骨內(nèi)含,神采外映,真得濂溪先生之髓者,不獨(dú)皮貌相肖也!尚榮告訴我,他塑周敦頤,是因?yàn)橹芏仡U解了他的惑。原來(lái),他在哲學(xué)系開(kāi)宋明理學(xué)課,雖然頗得同行及學(xué)生的好評(píng),自己內(nèi)心卻常常不安,他不斷地思索:在這個(gè)網(wǎng)絡(luò)發(fā)達(dá)的時(shí)代,信息的獲取十分便利,作為老師,除了知識(shí)之外,還能帶給學(xué)生什么?
一日,他在為講周敦頤而備課,讀到了這位理學(xué)大師的一則軼事,說(shuō)的是程顥的一個(gè)弟子在見(jiàn)了周敦頤后,感慨道:“如在春風(fēng)中坐了半年!”這句話(huà)讓尚榮豁然開(kāi)朗:“周敦頤叫我明白了,我能給學(xué)生的不只是知識(shí),還有我整個(gè)人。
做老師也要不斷修行,才能讓學(xué)生有坐在春風(fēng)里的感覺(jué)。”我至今記得,他在說(shuō)這番話(huà)時(shí),眼中閃爍的光芒。后來(lái)他便做了周敦頤的像,可我知道,與其說(shuō)是尚榮塑了周敦頤,不如說(shuō)是周敦頤塑了尚榮。我曾與他開(kāi)玩笑:希臘的皮革馬利翁愛(ài)上了自己塑的少女,你呢,正努力成為自己塑的周敦頤。人們或許認(rèn)為學(xué)者型藝術(shù)家的長(zhǎng)處在于知識(shí)領(lǐng)域的優(yōu)勢(shì),就像周亮工在《讀畫(huà)錄》中評(píng)價(jià)唐寅,說(shuō)他跟周臣學(xué)畫(huà),卻勝過(guò)了老師,原因就在于博覽群書(shū)。
(“子畏學(xué)畫(huà)于東村而勝東村,直是胸中多數(shù)百卷書(shū)耳。”)叫我說(shuō),無(wú)論做學(xué)問(wèn)還是做藝術(shù),僅有智識(shí)上的優(yōu)勢(shì)是不夠的,須得有高的情商,即移情的能力。尚榮所塑的人像多為古代的賢士高僧,與我們所處之環(huán)境,所受之背景皆不同,若缺乏移情的能力,哪怕胸中裝下好幾櫥柜的書(shū),也很難塑好。陳寅恪先生說(shuō)做學(xué)問(wèn)的人“其對(duì)于古人之學(xué)說(shuō),應(yīng)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筆。”要成為古人的知己,“必神游冥想,與立說(shuō)之古人,處于同一境界,而對(duì)于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表一種之同情,始能批評(píng)其學(xué)說(shuō)之是非得失,而無(wú)隔閡膚廓之論。
”做學(xué)問(wèn)如此,從事藝術(shù)創(chuàng)作亦少不了“了解之同情”。在尚榮塑的高僧像中,有一尊是以菩提達(dá)摩為原型的。尚榮對(duì)他有獨(dú)特的理解:“達(dá)摩是禪宗初祖,地位顯赫,可我卻覺(jué)得他很艱難。你想想,一個(gè)外國(guó)人遠(yuǎn)涉重洋,顛簸了三年才來(lái)到中國(guó)。語(yǔ)言不通,習(xí)俗不慣,與梁武帝交流又隔膜重重,還六次被人投毒,根本就屬于‘弱勢(shì)群體’。
一葦渡江,聽(tīng)起來(lái)好浪漫,個(gè)中辛酸又有幾人能了解!他必然是個(gè)極其堅(jiān)韌、樂(lè)觀的人,不然根本扛不住這一切。”尚榮就是懷著這份“了解之同情”去塑造這位高僧的:他披著長(zhǎng)袍,拄著筇杖,臉上刻滿(mǎn)滄桑,嘴角卻帶著達(dá)觀的微笑。尚榮將作品命名為《高僧圖》,他覺(jué)得雕塑雖以達(dá)摩為原型,卻無(wú)需拘于達(dá)摩本人,它一種象征——人生實(shí)難,但還是要一步一個(gè)腳印,踏踏實(shí)實(shí)地走下去,不抱怨,不頹喪,不放棄肩上的使命,顛沛必于是,造次必于是。
尚榮研習(xí)佛教哲學(xué)多年,對(duì)佛教藝術(shù)很有心得。不過(guò),他不雕佛祖,不塑菩薩,卻對(duì)僧人情有獨(dú)鐘。因?yàn)楦呱嗍欠踩耍麄冇旅途M(jìn),志愿無(wú)倦,不斷調(diào)適、完善自我,這正是尚榮所欽慕的人生態(tài)度。有人以藝術(shù)自?shī)剩腥艘灾異側(cè)硕浚鴮?duì)尚榮來(lái)說(shuō),創(chuàng)作就是一種生命的修行——在長(zhǎng)久的醞釀、涵泳之后,用最大的敬意去表達(dá)最深切最誠(chéng)摯的感動(dòng),即便技巧未能臻于完善,也能直指人心。修辭立其誠(chéng),藝術(shù)亦如此。尚榮的作品并不多,但都保持著一份可貴的真誠(chéng)。
當(dāng)你與它們兩兩相對(duì)時(shí),整個(gè)人便也莊重起來(lái)。歌德說(shuō)過(guò):品格呼喚品格[charactercallsforthcharacter],在尚榮塑的人像里,你可以看到他本人向往的品格和追求的境界。我漸漸明白他何以成為一個(gè)“文質(zhì)彬彬”的君子,是藝術(shù)創(chuàng)作助他見(jiàn)實(shí)相,令他思無(wú)邪。正如我的老師范景中先生說(shuō)的:“藝術(shù)不只是藝術(shù)家創(chuàng)造的一個(gè)靜態(tài)世界,它也是文明的一種積極力量,既塑造我們的感官,又塑造我們的心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