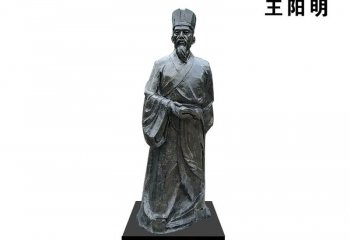曹繡國理凝結在皮毛上的信念蕭掌柜這個名字經常出沒眾多武俠小說的版本里。但這個蕭掌柜是身杯絕技的工藝美術師。他把“毛繡”,作為自己的畢生事業來做。毛繡是蒙古族傳統的手工藝飾品。追溯毛繡的歷史,毛繡品屬地元朝成吉思汗的兒子窩闊臺統治時期最為盛行。
隨著元朝的衰亡,這種工藝也隨著時間被淹埋。在前往百工坊路上,我遇到一對夫婦。憑直覺,我一眼就認出了蕭掌柜。當時,他們夫婦倆手牽手走在大街上,那是一幅完美的畫面,是一種親情,是一種互相扶持。帶著些許的興奮和心中對“毛繡”好奇心的驅使,我走進了神秘的百工坊,走進蕭掌柜的動物世界,去“察言觀色”。一心愛動物蕭掌柜是地道的東北滿族人,祖上一直從事木雕工藝,小時候,他就經常把自己玩耍時抓來的麻雀做成標本。年輕時,在烏蘭察布盟插隊當兵時,兵團的人多數是在內蒙和東北一帶生活的少數民族,他們長期和野生動物接觸,對動物懷有一種濃厚的感情。
從少數民族兄弟身上,蕭掌柜了解到有關毛繡的歷史。蕭掌柜有一顆追隨藝術的心。酷愛手工工藝制作的他,回到北京工作之后,憑著對動物熱愛的這股闖勁兒,向自然博物館的老師,系統地學習了動物標本的制作。從那以后,他就作出了大膽的決定:將神秘的毛繡技藝整理,恢復并使更多的人了解毛繡。蕭掌柜多年來一直有這樣一個愿望,就是將工業革命之后滅絕的幾百種動物,利用圖片把它們復制出來,辦一個展覽,使更多的人了解我們生存的自然界,熱愛現存的野生動植物保護我們的家園。
這無疑對青少年也是一種深刻、生動的教育活動。讓他們能近距離地感受已經滅絕的物種,從自身小的行為、舉動做起,來維護我們身邊的環境。蕭掌柜說:“我們一直在喊的口號就是腳踏實地,踏踏實實地做這個工作”。天南地北去選毛剛開始制作毛繡的時候,由于選取的家禽、家畜有限,所以毛色很難與要完成的標本達到真正的統一。在不得已的情況下,蕭掌柜采取了用化學藥劑染毛的措施。
這樣做,毛色是接近了很多,但是完成的標本身上那股化學藥品的味道始終退不去,失去了蕭掌柜所要追求的“原生態”。蕭掌柜經過反復的推敲之后,決定把選毛的范圍擴大,“這里的動物毛色不合適,我們就到其他地方找”。
但現在蕭掌柜的進貨渠道已經遍布大江南北。他的觀點就是:寧缺毋濫。不同部位要選用不同的材料,這也需要琢磨。舌頭和鼻子要求材料有彈性,有一定的手感。而牙齒和腳趾部分則是相對較硬,骨質感較強。經過無數次制作經驗的積累和對動物基本特征的琢磨,蕭掌柜找到了合適的替代品。他說:“我喜歡動物,所以我愿意花時間在毛繡制作上。
對動物有愛心是很重要的,一個不熱愛動物的人,是不可能熱愛毛繡藝術的。”懷著一份對野生動物的愛,蕭掌柜決定將毛繡事業進行到底。毛繡發展到今天,已經演變成一種全民族的藝術。蕭掌柜曾嘗試開廠,讓更多的人學習毛繡的制作。可他發現,做出的動物不僅沒有了靈氣,而且都像一個模子里刻出來的。做一百只狗都長得一樣。“這不是糟踐老祖宗的手藝嗎?
”曾經賠得一塌糊涂,但蕭掌柜并沒有后悔。藝術就是這樣,它不是一種商品化。要實現工廠化是不可能的。有了這樣的經驗,蕭掌柜開始踏踏實實地開起了作坊。“起初,我并沒有想過大家對我們的東西會不會認同,我只是做我自己喜歡的事情,從事自己熱愛的工作。但我陸續收到很多信件,都是向我訂購仿真動物。能有這么多人喜歡我做的東西,我當然高興。
就這樣生意便做了起來。”“我做毛繡是帶有一定的商業利益,但我不想把這份工作做成純商業的東西。”可以說,蕭掌柜憑借毛繡,生活上過得很富裕。但自始自終,蕭掌柜都把毛繡作為自己一生熱愛并追求的理想去實現與完善。直到現在,他仍在為自己設定的目標,仍在堅持不懈地追求。我不禁對他懷有這樣不滅的信念而感到欽佩。做事就應當像蕭掌柜這樣。
將毛繡事業進行到底蕭掌柜說:“毛繡不是一種追風,追潮。”由于掌握技術的人較少,工作難度較大,工作量較高等因素,決定了它的價值偏高,所以要一下子普及是不可能的,也不現實。現在市場對毛繡藝術品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很多人都喜歡他做的仿真動物,有為老人祝壽送的,有為企業開業送的,逢年過節也有人把仿真毛繡作為節日禮物的。
看來,已經有好多人認識到了毛繡的價值所在。“我們要把這個工作一直做下去。”堅持必定會有收獲。其實,動物和人是一樣的,人的相貌有千差萬別,動物也是一樣。所以,我要求每一只動物標本都有它自己獨有的特征。毛繡是無底稿制作,它的原生態是在你腦呂的一種印刻,全憑自己頭腦中對動物的形態、相貌和表情的勾勒。
在動物的基本特征基礎上,加入動物的喜怒哀樂,構成它的表情。“不管是做毛繡,還是做仿真動物,都有掌握他的表情。”制作仿真毛繡動物,首先要對動物的生理構造和體貌特征十分了解。比如說要做一只老虎,而你卻不知道老虎應該有多少顆牙齒?犬齒的位置在哪里?這是不行的。一般人看,只會注重這只動物“像不像”的問題。而懂行的人更注重的是制作的動物“對不對”的問題。
如果把老虎有多少顆牙齒都弄錯,即使做出的標本再逼真,客觀存在也是“錯的”。這樣的錯誤是不允許的。蕭掌柜在各個方面都對自己嚴格要求,這樣對自己是一種責任,同時,對動物也是一種責任。動物標本本身有很大的局限性。客觀存在需要以動物的死亡作為基礎。而仿真毛繡動物歷來就是我們老祖宗傳承下來的。并且,我們不需要以動物的死亡作代價。甚至,取毛的工作都是在死去家禽、家畜身上進行的。
這樣一來,仿真毛繡必定會有很大的發展窨。他說:“單純靠我一人的力量,把毛繡工藝發揚光大,是遠遠不夠的。”由于制作毛繡所需的工期行,要求掌握的工藝也較多,大多數人只是心血來潮。沒有幾個人愿意耐著性子來學。“我不能讓這門手藝在自己手里失傳。
”蕭掌柜希望能把這門手藝傳授給更多愿意從事毛繡工作的人,“要把這個工作當成一輩子的事來做。”看著滿屋子的毛繡作品,有墻上掛的,地上坐的,還有在桌子上叫的。伴著小貓“喵喵”的可愛叫聲,人告別了慈祥親切的蕭掌柜。毛繡仿真警示人類一只近一米高,兩米多長,黑黃毛色相間的老虎,雙目圓睜,昂首闊步,威風凜凜地出現在人們面前,如果不是在北京百工坊蕭掌柜的工作間里,真會把人嚇一跳的。
這只栩栩如生的老虎,并不是一個標本,而是蕭掌柜運用毛繡制作的仿真動物。這個蕭掌柜是身懷絕技的工藝美術師,他把運用行繡制作人為滅絕的野生動物這件事作為自己比重的事業。蕭掌柜是地道的東北滿族人,祖上一直從事木雕工藝。年輕時,他在烏蘭察布盟插隊當兵,兵團的人多數都是大內蒙古和東北一代生活的少數民族,他們長期和野生動物接觸,對動物懷有一種深厚的感情。
插隊時,聽察右后旗當地的老人說起一訓蒙古族的傳統民間工藝——毛繡,曾在元大都十分盛行,幾乎每個貴族家中都掛著毛繡掛毯,隨著元朝的衰亡,這種工藝也漸漸不為人所知。老人告訴蕭掌柜這種工藝與中國任何一種繡法都不一樣,不用一般的線,而是用動物脊背上的鋒毛(退絨)在粗亞麻布上繡出圖案。遺憾的是蕭掌柜從沒見過一幅古代流傳下來的毛繡制品。回到北京工作后,蕭掌柜有時間就去自然博物館幫忙制作標本,憑著對動物熱愛的這般闖勁兒,跟那里的老師學會了仿真動物標本的制作方法,跟著老師做了獅、虎、豹等大型野生動物的標本。
有了做標本的經驗,蕭掌柜心中產生了一個大膽的想法,把在內蒙古時聽到的神秘的毛繡技藝整理,恢復起來。為了使繡制的動物逼真,他動手前先請教了生物、工筆畫、油畫和解剖學的老師。使自己在繪制繡品底稿時盡量忠于野生動物的原生態。
繪好底稿后,選毛又成了困擾的難題。剛開始制作毛繡的時候,由于選取的家禽、家畜有限,所以毛色很難與要完成的標本達到真正的統一。在不得已的情況下,蕭掌柜采取了用化學藥劑染毛的方法。這樣做,毛色是接近了很多,但完成的標本身上一股化學藥品的味道始終退不下支,失去他要追求的“原生態”。經過反復的推敲之后,他決定把選毛的范圍擴大,“這里動物毛色不合適,我們就到其他地方去找”。
經過試驗蕭掌柜選用了四、五種家禽的皮毛當原料,但每只動物上只能取脊背上4兩左右的鋒毛,還要等到夏季,動物皮毛最光亮的時候取。而一只與真虎大小相同的毛繡虎要用去100多公斤毛。并且不同部位要選用不同的材料;
舌頭和鼻子要求材料有彈性,有一定的手感;而牙齒和腳趾則相對較硬,骨質感較強;繡制成年動物和幼年動物時要選用不同的毛;而表現動物兇猛威嚴和憨態可掬兩種截然不同的神態時,也需要選取不同的毛來表現。我的相貌有千差萬別,動物也是一樣,所以每一只動物標本都有它自己獨有的特征。毛繡是無底稿制作,它的原生態是在腦中的一種印刻,全憑制作者頭腦中對動物的形態,相貌和表情的勾勒。
在描繪動物特征的基礎上,加入動物的喜怒衰樂,構成它的表情。做毛繡仿真動物,就要掌握它們的表情,這需要對動物的生理構造和體貌特征十分了解。比如說要做一只虎,而你卻不知道老虎有多少顆牙齒,犬齒的位置在哪里,這就不行。一般人看,只會注意這只動物“像不像”的問題,而懂行的人更注重的是制作的動物“對不對”的問題。
如果把老虎有多少顆牙齒都弄錯,即使做出來的標本再逼真,它也是“錯的”。為使繡制的動物生動逼真,蕭掌柜繡所有的毛都要用鑷子夾起“栽”到大經緯線料子上,有時動物臉上一些細小的毛用普通的鑷子根本夾不起來,要用特制的竹鑷子。在動物的鼻子、睫毛等點睛之筆處,更是不吝異使用過去做標本時留下的真正野生動物的毛。在繡制時還要特別細心,因為動物皮毛的花紋看似簡單,實際有復雜的規律,中間出一點錯,整體效果就不對了。
當他完成第一幅毛繡作品后,拿給曾向他描述毛繡工藝的蒙古族老人看,老人激動地說,比他以前見過的毛繡要逼真得多。在用毛繡工藝做仿真動物的最初,蕭掌柜也曾做過恐龍等一些史前動物,但后來他把著眼點放在因人為因素滅絕的動物身上。當時有很多人不理解,包括他的家人和朋友。因為做這些動物投入的多。
有人說,你還不如做只東北虎,市場上能賣個好價錢。蕭掌柜說:“在今天,人為的捕殺使得每24個小時就會有一個物種消失,很可能有許多珍稀動物我們的子孫以后就看不到了,做仿真動物是把動物原生態留住的一個好辦法。而且通過展示,可以讓人們更珍惜地球上現有的物種,更自覺地保護大自然賜予我們的一切。”基于這種觀點,蕭掌柜花了大量的時間研究近百年來滅絕的動物。
每次制作前如果沒有原始資料,或原始資料不充分,蕭掌柜都要到自然博物館、圖書館等地方查閱資料,對動物的外形外貌,及動物的生活習性、產地特點等,進行研究、考證,力求掌握最全面的信息。現在蕭掌柜手上掌握了一大批近代滅絕動物的資料,如臺灣的云豹、美洲的旅鴿等。
史料記載,旅鴿的滅亡是慘絕人寰的,百年中就捕殺了幾十億只,干凈徹底地滅絕了一個物種。19世紀初葉,北美洲仍有旅鴿30億到50億只。因為這種野生鳥肉味鮮嫩至極,又愛好群居,便遭到人類大規模圍捕和射殺。1880年,當自然保護主義者大聲東擊西疾呼想要保護旅鴿時,已經太遲了。
1900年,最后一只野生旅鴿被射殺。1914年9月1日世上僅有的一只名叫瑪莎的旅鴿死在人工飼養的籠子里。至些,旅鴿便徹底告別了人間,僅有一只標本留在世上。蕭掌柜最早做的一具滅絕了的仿真動物是新疆虎,這種虎是西亞虎的一個分支,主要生活在新疆中部由庫爾勒沿孔雀河至羅布泊一帶,大約是在1916年滅絕的。除此之外,他一直想要將工業革命后近二三百年內滅絕的幾百種動物,利用工藝把它們都做成仿真的,舉辦一個仿真動物展覽,使更多的人了解自己生存的自然界,熱愛現存的野生動植物。
這對青少年也是一種深刻、生動的教育,讓他們能近距離地感受已經滅絕的物種,從自身小的行為做起,來保護我們身邊的環境。蕭掌柜說:“毛繡不是一種追風、追潮。”由于掌握技術的人較少,工作難度較大、工作量較高等因素,決定了毛繡制品的價值偏高,所以要一下子普及是不可能的。但現在,市場對毛繡藝術品的需求量非常大,很多人都喜歡他做的仿真動物。有給老人祝壽送的,有給企業開業送的,逢年過節還有人把仿真毛繡作為節日禮物。
為了擴大產量、后繼有人,幾年來蕭掌柜收過不少徒弟,但都沒有堅持下來。因為工藝技巧太高,做粘接動物毛量大,時間長,需要很大耐心和細心,所以他的徒弟們開始都信心十足,但最后都半途而廢了。蕭掌柜說:“我喜歡動物,所以我愿意花時間在毛繡制作上。對動物有愛心是很重要的,一個不熱愛動物的人,是不可能熱愛毛繡藝術的。但是單純靠我一人的力量,把毛繡工藝發揚光大,是遠遠不夠的,我不能讓這門手世在自己里失傳。”他希望能把這門手藝傳授給更多愿意把這個工作當成一輩子的事來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