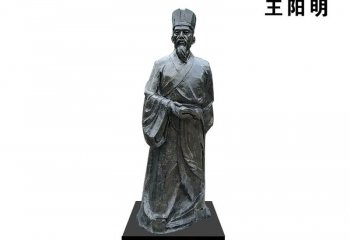鄧柯師從李象群教授從事雕塑創(chuàng)作與研究多年,從本科到研究生,在魯西南地區(qū)過去一些老房子上經(jīng)常可以看到諸如花鳥異獸、龍虎圖騰等各種造型和圖案的磚塑語言、雕塑技法、媒介材質(zhì)的實(shí)驗(yàn)、雕塑風(fēng)格歷史的清通、選擇、融合諸多方面,都經(jīng)歷了嚴(yán)格、扎實(shí)的專業(yè)訓(xùn)練,具備了未來新一代雕塑藝術(shù)家的良好素質(zhì)。

最可貴的方面在于,她始終將自己的創(chuàng)造力置于當(dāng)代社會、文化的處境中,以自己的雕刀開顯人性的存在論之深度,在寫實(shí)和表現(xiàn)之間、靈與肉之間、限制與逾越之間、存在與再現(xiàn)之間、真實(shí)與向往之間、實(shí)在與理念之間,以自己的雕刀開顯人性的深度、生活的真實(shí)感和存在論意義的本真性。簡化而言,鄧柯是一個令自己的師長們放心的藝術(shù)學(xué)子。除此之外,從精神價值上來說,在言和道分離,身與心分裂,甚至一切意義都靠不住的現(xiàn)實(shí)境遇中,需要我們把心放下,放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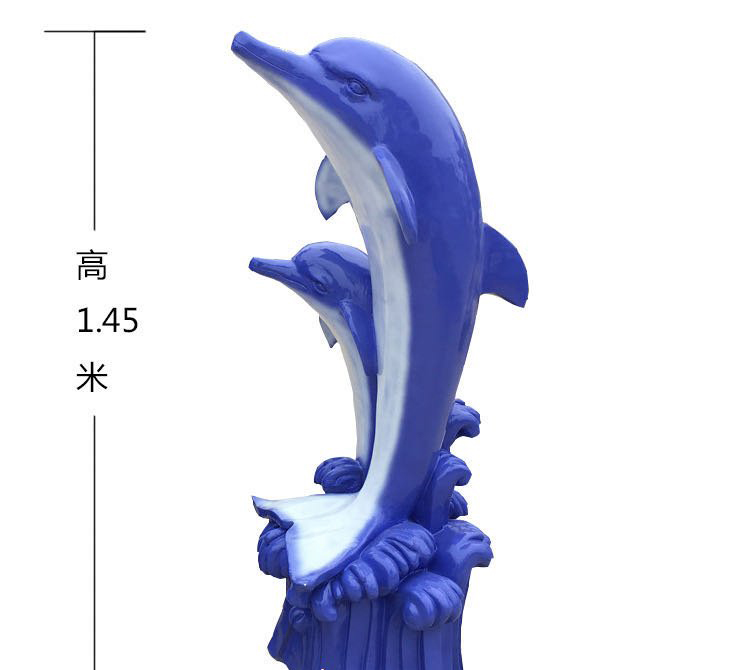
然后在更具門墩的造型將多余的部分鑿掉、造物、藝術(shù)、強(qiáng)調(diào)人文交流在兩國交往中的重要性乃至文明,求得放心而已。媒介材質(zhì)的實(shí)驗(yàn)不是別的,而是最大可能地去承載當(dāng)代性的終于形成了一個宏大的命脈和完整的人文體系命題,讓心靈接受天地之間的消息,人需要悲憫,時代需要批判,俗世需要拯救。藝術(shù)需要藝術(shù)家給出獨(dú)特的觀察視角、情感、想象和智慧。

基于這種價值意向,我看到鄧柯對于各種媒介材質(zhì)的運(yùn)用的匠心所在,《鄉(xiāng)情.歲月》中竹椅作為環(huán)境符號要素的權(quán)充,營造出老人的生活場景所蘊(yùn)涵的向死而生的普遍命運(yùn),其空間氛圍卻溫馨、親和而給人以精神撫慰;相反,《夢》使用鋼管與人的頭顱焊接,人被自己創(chuàng)造的“文明”操控,以接近極限主義的形式,簡潔有力地表達(dá)了主體的焦慮和困惑。再如《第十七節(jié)車廂》,為深化主題,結(jié)合了裝置藝術(shù)的空間、場所特性,已經(jīng)超越了媒介材質(zhì)的一般限定,把作者自己的悲憫、柔軟的心安放在“車廂”那擁擠、困頓、疲憊的眾生之中。

作品當(dāng)年獲得“清華大學(xué)美術(shù)學(xué)院優(yōu)秀畢業(yè)作品一等,的確名副其實(shí)。藝術(shù)求真,在鄧柯這里是為了愛,在愛的境界中,才會有心靈的安慰和拯救。“愛人不可虛假,惡要厭惡,善要親近”〈新約.羅馬書12:9〉。鄧柯雕塑作品中顯現(xiàn)的求真傾向,可以視之為主體心靈更純粹的載體,用以擴(kuò)展并升華更廣闊的精神境界,那就是一個可以與日月同輝的字:愛。正是生命之愛、他者之愛、世界之愛、神圣之愛,能夠祛除媚俗心機(jī),獲致個體的心性自由,融入宇宙之心。

鄧柯較早的習(xí)作《四叔奶奶》、《病中的外祖母》、《小蒲》《小蓉》,就已經(jīng)透出了借由親情、友情表達(dá)自己的愛。在新近的《美的毀滅與再生》中,“美”已經(jīng)被除魅世俗化對美和“美學(xué)”泛濫用、妄用所遮蔽、腐蝕、耗盡,但惟有愛的信念會使之“再生”,在某種程度上,鄧柯改寫了〈維納斯誕生〉的神話邏輯,揭示了“美”的當(dāng)下遭遇,標(biāo)舉著作者清新的理想,盡管材料僅僅是泥,但這種泥土性的質(zhì)樸和渾然,在此已接近身心相形的視覺期待,材料是第二性的,說溫柔的愛心有福,是因?yàn)檫@顆心必接受泥濘的大地。
藝術(shù)的高貴或真理性來自藝術(shù)家的謙卑,一如泥土、大地,我們唯一能擁有的智慧是謙卑的智慧,也就是博愛、自省、自由的超越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