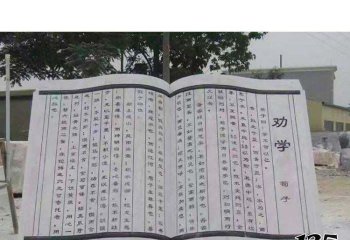最近,繆哲先生向我建議,能否用書面的形式,回答一個讀者常提的問題,以盡譯者的責(zé)任:貢布里希《藝術(shù)的故事》正文第一句話到底何意?為了不負朋友所望,我想試一試。讓我先引用原文:TherereallyisnosuchthingasArt.Thereareonlyartists。我所見到的幾種中文本分別譯為:我們的中譯本,1987年天津人民美術(shù)出版社的版本為:“現(xiàn)實中根本沒有藝術(shù)這種東西,只有藝術(shù)家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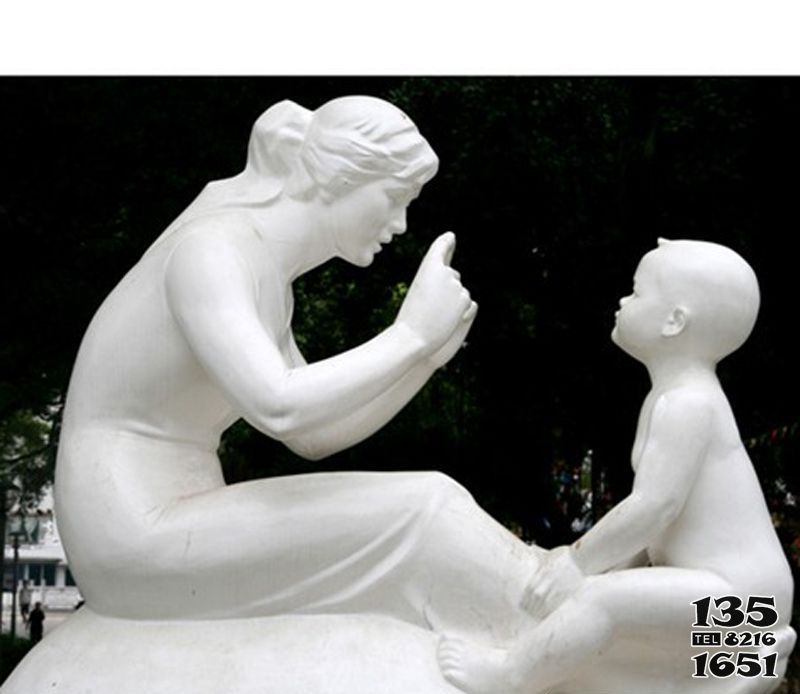
”1999年三聯(lián)出版時改為:“實際上沒有藝術(shù)這種東西,只有藝術(shù)家而已。”在1995年譯對話錄ALife鄄longInterest,又干脆采用了更口語化的形式:“沒有藝術(shù)這回事,只有藝術(shù)家而已。”這樣簡單明了的句子,幾種譯本在理解上并無分歧,但要表達得好卻不容易。

我們之所以一改再改,顯然是因為還找不到一種理想的表達方式,唯恐蠅惑曙雞,以昏啟昭,敗壞了原作本應(yīng)帶給讀者的雅意。此處就容易犯上這種毛病。一位著名的譯者談翻譯的甘苦,這樣說道,一旦發(fā)現(xiàn)了自己的誤解錯譯,便有一種穿地而去,不想人見的念頭。這真是心聲之言。我也譯過幾本書,譯時抱著一種激情,想把自己的讀書之樂傳達給別人,可靜心之際,內(nèi)心的深處卻是悲涼的。不過,我也認為,害怕犯錯誤,只是一種可憐的愿望。沒有錯誤,我們的知識恐怕就無法增長。

例如,我自己對于這第一句話的理解就是通過一些誤解才覺得漸有所知的。原來,它看著容易,其實,不要說對中國讀者,就是對西方讀者,似乎也不那么簡單。有位學(xué)者在評論《藝術(shù)的故事》時說:貢布里希學(xué)識淵博,但他表達得不露聲色。這第一句便足供佳例,因為它不是貢氏的獨創(chuàng),而是有典故可尋的名言,其出處可以追溯到150多年以前。1935年施洛塞爾在他的著名論文“造型藝術(shù)的風(fēng)格史與語言史”中講到心理學(xué)家利普斯和一位批評家辯論的故事,那位心理學(xué)家說:Genaugenommengibtes“dieKunst”garnicht.EsgibtnurKünstler施氏接著寫道:“不過,那位批評家不知道這句話早在1842年就由馮·麥爾恩說過了。

”這就是《藝術(shù)的故事》第一句話的來源。我猜想,當費弗爾說“沒有歷史,只有歷史學(xué)家”時,他可能就是受了這句話的啟發(fā)。曹意強先生告訴我,尼采也說過,“沒有哲學(xué),只有哲學(xué)家”,顯然也是舊瓶新酒,暗中換進了自己的私貨。貢氏從老師那里順手拈來,在寫法上有點像宋元話本的入話,或雜劇中的楔子,意在引起下文。

但也有更深一層用意,即用一種唯名論的看法去反對他一貫批評的亞里士多德的本質(zhì)主義。按照亞氏的學(xué)說,一個定義就是關(guān)于一種事物的固有本質(zhì)或本性的一個陳述,它表明,一個語詞即指稱該本質(zhì)的名詞的意義。貢氏強調(diào)說,在古代,在文藝復(fù)興時期,arte指的是工藝技巧,技術(shù)能力,而不是我們所謂的藝術(shù)。
他說道:現(xiàn)在大部分人用“藝術(shù)”這個詞,來指一種與社會上的任何功能都不相關(guān)的為藝術(shù)本身而進行的活動,藝術(shù)成了一種神秘的事業(yè)。實際上這是18世紀發(fā)生的一種變化造成的結(jié)果,當時人們開始賦予藝術(shù)一種新的意義。在那以前人們談?wù)摾L畫或雕塑,不是談?wù)撘话阋饬x上的藝術(shù)。只有當美學(xué)得到發(fā)展、人們的行為擺脫了教會的桎梏以后,當沉思已經(jīng)代替禱告的時候,人們才開始談?wù)撘话阋饬x上的藝術(shù)。艾布拉姆斯最近寫了一部極好的著作,證實藝術(shù)作為一種高尚和神圣之物的觀念是在18世紀才出現(xiàn)的。這就是藝術(shù)一詞的古典含義。
至于它的今典,讓我們繼續(xù)引用貢氏本人的說法:今天的“藝術(shù)”有兩種意思。如果你說“兒童藝術(shù)”或“狂人藝術(shù)”,你不是指偉大的藝術(shù)品,而是指繪畫或圖像;如果你說“這是件藝術(shù)品”,或“卡蒂埃—布勒松是位偉大的藝術(shù)家”,則表現(xiàn)了一種價值判斷。這是兩種不同的東西,但有時被混在一起,因為我們的范疇總是有點漂移不定。
所以我認為一開始先警告讀者我不從定義入手,這樣做會穩(wěn)妥些。因為定義是人造的,藝術(shù)沒有本質(zhì)。我們可以規(guī)定我們所謂的藝術(shù)和非藝術(shù)。所以我用那句話開始我的書,并不覺得遺憾。當然,這話可能導(dǎo)致誤解。我的觀點是:有制像這么回事,但是要問建筑是否藝術(shù),或者攝影和地毯編織是否藝術(shù),那只是浪費時間。在德語中Kunst包括建筑,但在英語中不包括,如果你看一看《塘鵝藝術(shù)史》,你會發(fā)現(xiàn)其中一卷稱為《十七世紀的法國建筑和藝術(shù)》。
每個概念在不同的國家都有不同的意義范圍。簡單地說,貢氏絕不想在詞語定義上糾纏,他的意思是:實際上沒有亞里士多德本質(zhì)主義定義上的藝術(shù),只有藝術(shù)家而已。但這樣表達顯然不適合他所設(shè)定的讀者對象,何況他使用的又是引語,所以他又接著寫道:Oncetheseweremenwhotookcolouredearthandroughedouttheformsofabisononthewallofacave;todaysomebuytheirpaints,anddesignpostersforthehoardings;
theydidanddomanyotherthings.Thereisnoharmincallingalltheseactivitiesartaslongaswekeepinmindthatsuchawordmaymeanverydifferentthingsindifferenttimesandplaces,andaslongaswerealizethatArtwithacapitalAhasnoexistence.ForArtwithacapitalAhascometobesomethingofabogeyandafetish.Youmaycrushanartistbytellinghimthatwhathehasjustdonemaybequitegoodinitsownway,onlyitisnot‘Art’.AndyoumayconfoundanyoneenjoyingapicturebydeclaringthatwhathelikedinitwasnottheArtbutsomethingdifferent.再回到《藝術(shù)的故事》的第一句,既然只有藝術(shù)家,沒有藝術(shù)其物,我們或許會問,貢氏是不是打算寫一部藝術(shù)家的歷史呢?
貢氏答道:正如我剛剛說過的,“藝術(shù)”這個詞至少有兩種意義,所以《藝術(shù)的故事》實際上講述了兩件事:它是人們制作圖像的故事,從史前洞穴到埃及人直到現(xiàn)代人制作圖像的故事;但是顯然我選了那些可以在價值上作判斷的藝術(shù)品作例子,所以,《藝術(shù)的故事》又是另外一種意義上的“藝術(shù)”的故事,即制作好圖畫的故事。
《藝術(shù)的故事》在西方向稱藝術(shù)史中的圣經(jīng),在中國也擁有廣泛的讀者。它的第一句在文章中屢被援引,也經(jīng)常聽到友人問起它的含義,此處就個人所知,撮取貢氏的觀點如上,引文主要取自對話錄《藝術(shù)與科學(xué)》。行文至此,擱筆臨窗,想想貢氏已經(jīng)謝世五年,不由得興慨無端,又想起沈彬的詩句:千古是非無處問,夕陽西去水東流。另外,此處要特別強調(diào)一點,因限于報刊的體例,不能全然征引原文,這就又成了個人的翻譯和讀解,誤讀之處或許多有,亦未可知。
好在我們可以傾聽批評的聲音,能夠在錯誤中學(xué)習(xí),并且試圖通過一種態(tài)度,即Imaybewrongandyoumayberight,andbyaneffort,wemaybegetnearertothetruth,來獲得一種生活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