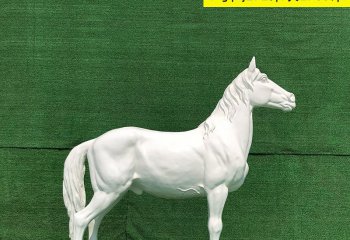初春三月,陽光清冷,北京798藝術區內依然靜謐。游人似乎比往常多了不少,很多是背著行囊的外國人,他們打聽著同一個地方——時態空間藝術機構。挪威女藝術家瑪瑞安·海耶道爾的“我是兵馬俑”系列作品正在那里展出。兵馬俑是中國文化的象征,被稱為“世界第八大奇跡”,也被譽為中國歷史上的男性力量、威嚴和無上權威的象征。而瑪瑞安,一個來自挪威的女人,不僅以寫實的方式復制了兵馬俑,還將其性別改變了——置換為女性。在這樣一個藝術空間,一眼望去全是清一色的女兵馬俑,那種奇特和震撼難以言表:從背面看,她們的體量、服飾與男兵馬俑相同,但走到前面,卻發現她們的神態、服飾和發型各異——戴著戒指的女人,懷著敵人孩子的女人,做鬼臉表示不屑的女人,想要充當人體炸彈的女人,因化學戰失去了秀發的女人…

或隱忍、或悲苦、或安詳、或憂傷,都身軀壯碩,背對觀眾。正看得出神,有位一襲黑衣、金發碧眼的優雅女人向記者走了過來,她就是瑪瑞安。瑪瑞安不懂中文,一直在跟隨拍攝其紀錄片的陜西電視臺導演李亞民,當起了我們的臨時翻譯。

“為什么要將兵馬俑變成女性?”記者脫口而出。“我想告訴人們一個關于戰爭和女人的故事。戰爭一直伴隨著我們,過去是,現在是,將來也是。在人們眼里,戰爭只是男人的事情,其實,女性在戰爭中也遭受了很多痛苦。她們失去了自己的家園,失去了丈夫和孩子,不得不四處流浪。

女性的社會角色,無論在古代還是現代,家庭還是職場,都存在著被誤用、濫用,甚至虐待的問題。”在瑪瑞安的眼里,女性是痛苦的承受者、化解者,同時也是歷史的創造者。這些女兵馬俑以高大的身軀背對觀眾,意味著女性的歷史從未被正面書寫,她們在歷史中只留下了影影綽綽的背影。瑪瑞安1957年生于挪威奧斯陸,她的家族——海耶道爾在挪威聲名顯赫。

父親老海耶道爾是挪威著名的人類學家和冒險家。對于人類橫跨大西洋遷徙的問題,老海耶道爾提出,古人就用一種葦草編織的小船,改寫了人類歷史。很多人取笑這種想法,老海耶道爾和志同道合的朋友用9根輕型原木制成越洋筏,最終穿越大西洋,創下了航海史紀錄…在挪威文化史上,海耶道爾的名字閃閃發光。瑪瑞安小的時候,父親常帶她到世界各地旅行。父親告訴她:無論民族、宗教、國家怎樣不同,我們都是大自然的孩子。父親那種充滿幻想、熱愛冒險的精神也影響了瑪瑞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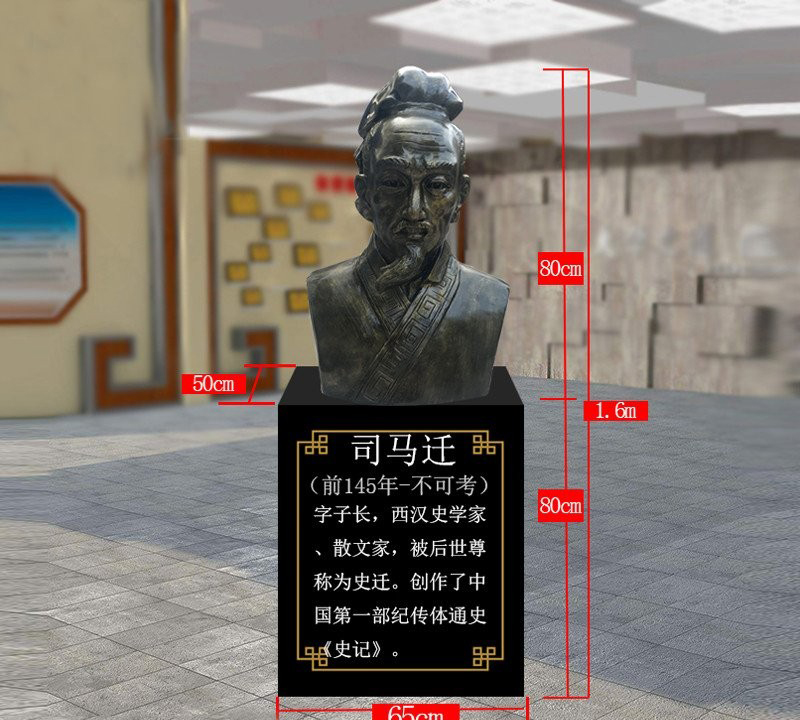
1997年,40歲的瑪瑞安獨自開車穿越撒哈拉大沙漠,在非洲進行藝術創作。老海耶道爾在2001年去世,生前幾乎走遍了世界,唯一的遺憾就是沒去過中國。他去世前曾和挪威駐中國大使館聯系,希望能去陜西的兵馬俑和四川的三星堆看一看,結果沒等愿望實現就走了。受父親的影響,當瑪瑞安第一次在《國家地理》雜志上看到兵馬俑的圖片時,就被深深地吸引了。2004年,瑪瑞安終于在中國親眼看到了兵馬俑。
第一次看到氣勢恢宏的秦始皇陵“地下冥軍”,她佇立在那兒,淚水彌漫雙眼。這就是父親向往的古老文化,沉郁的中國歷史。離開時,她買了一尊大型將軍俑和幾尊小俑復制品,帶回了挪威。這幾尊兵馬俑成了瑪瑞安放不下的牽掛。一年后,她再次來到陜西,在一家距離秦俑館最近的復制工廠學習制俑工藝。冬天很冷,工廠條件又簡陋,瑪瑞安第一批制作的20尊大型女俑,還未等燒制就被凍壞了一大部分,最后僅留下4尊成品。
瑪瑞安并沒有因此放棄,2006年9月,她決定再試一把。這次她沒有住賓館,而是租住在最早發現兵馬俑的農民家。她常常睡在土炕上,想象著自己腳下埋藏的強大古代軍隊。瑪瑞安說在兵馬俑的故鄉工作,她的心好像與古老文化貼得更近,更能夠靜下心來創作。
瑪瑞安喜歡和農民拉家常,一起做飯看電視,觀察人家怎么縫被子,怎么婚喪嫁娶。雖然語言不通,但她開朗隨和,和大家相處融洽。她每天早出晚歸,騎車往返于住處和工廠。工人們看到這個外國女人這么執著,都非常敬佩。把最好的黃土和膠泥給她做藝術創作,由最好的技術工人向她提供咨詢幫助。而具體的造型細節都由瑪瑞安親自制作。瑪瑞安準備了一個速寫本,在大街上對當地的女孩、婦女、老太太進行速寫。每天晚上看DVD,觀察中國古裝劇中的人物發型和服飾,然后用膠泥和刻刀一點點用心刻畫。
2006年圣誕節前,作品出爐了,瑪瑞安決定把它們搬到北京來展覽。在工人們的悉心幫助下,70多尊1噸多重的兵馬俑運抵北京。在西安制作好的兵馬俑,需要在北京完成后期的附件安裝。瑪瑞安在北京北五環外的索家村找到一處房子。這是一個類似車間的工作坊,上面是6平方米的小閣樓,僅能放下一床一桌,下面是80平米的大廳,作品一個挨一個地擺放著,狹小的空間僅能供她鉆進去進行制作。
瑪瑞安一個人住在這里。每天8點半起床,工作到晚上12點,從來沒有休息日。她的丈夫歐拉是挪威奧斯陸大學藝術系的教授,經常從千里之外打來電話叮囑:“親愛的,現在是北京時間零點,你該休息了。”“今天是周五,你休息一下吧。”在給瑪瑞安拍攝專題片的過程中,導演李亞民對這個外國女藝術家刮目相看:“一個女人,一句漢語不會,到了陜西學會了一句‘美得很’,到了索家村學了一句‘索家村’,現在798搞展覽,又很費勁地學會了‘798’。
除了對中國歷史的一些研究,她是一個‘中國盲’,但我覺得這并不妨礙她成為具有國際眼光的雕塑藝術家。”用極具中國文化符號意義的兵馬俑進行藝術創作,瑪瑞安的做法引發了不少爭議。有些人認為這歪曲了中國的歷史和文化,也有藝術家評價:“以前的作品都是表現男性,現在你的作品表現女性,這就圓滿了。你發現了一個新的視角。
”瑪瑞安喜歡后者的評價。她說自己選擇兵馬俑作為藝術載體,是因為它很容易被人接受,并非是以西方審美文化來滿足一種消費文化的獵奇,也不是對中國文化的簡單置換,而是以一種平等的方式,和中國文化進行對話。瑪瑞安曾告訴導演李亞民,她覺得自己是一個國際藝術家,不愿帶著政治色彩去創作。女兵馬俑反映的是人類戰爭的歷史,在挪威的歷史上也有類似的不幸。二戰期間,希特勒的部隊到了挪威,強暴了挪威的婦女,當時人們仇視這些被敵人侮辱的女人。
現在挪威也在反思這段歷史。上千年前,在凱撒時期,羅馬大帝的軍隊橫掃歐洲。一些國家為了使婦女免遭侮辱,就把她們藏到一個石頭窖里,每天晚上偷偷給她們送飯。瑪瑞安把她理解的所有關于戰爭的符號,都賦予女兵馬俑身上。在瑪瑞安的眼里,地球越來越像一個村莊,中國文化在世界上的影響越來越大,而文化是屬于全人類的。
她想用這個和平國家的文化符號,表達對全世界戰爭的憤怒。采訪中,李亞民說瑪瑞安是一個勇敢的女人,“她是在吃第一個螃蟹。人們看著一個橫著走過來的東西,不敢吃的時候,瑪瑞安把它吃掉了。”看了瑪瑞安的作品,挪威大使館的文化參贊說,這是迄今為止挪威與中國文化交流中影響最大的事件,讓他們很感動。在挪威駐中國大使館的一個小冊子上,瑪瑞安的丈夫歐拉給了她這樣的評價:“在過去的一年,瑪瑞安·海耶道爾比我多走出了半步。
”歐拉已經來到中國,在江西景德鎮進行藝術創作。而瑪瑞安說,她的思維可能每秒都在更新,說不定什么時候就有了新的想法。兩個藝術家都50歲了,還在藝術創作的道路上你追我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