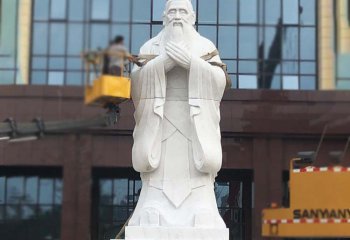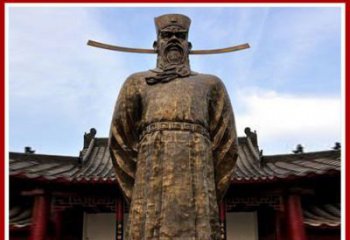徐堅偉習畫很早,小學四年級就上少年宮學畫,而且是從水墨畫學起,在以優異成績考入中央美術學院中國畫系之前就已經有了很好的基礎,再經過學院的名師指導和嚴格訓練,應已具備不凡的實力。不過,看徐堅偉的畫卻是不容易察覺這種實力,也可能是藏而不露。他的畫看起來很平淡,乍一看去,好像不會畫畫的一樣。畫國畫講究功底,講究傳承,功夫是練出來的。國畫其實是不用到學院來學習的,拜個名師指導,天天臨摹古畫,功到自然成。
學院也強調傳統,也讓學生臨摹,但學院教育的基礎是寫生,筆墨要結合到寫生中去,這無疑會改變傳統的筆墨關系。從學院出來的學生,如果不是一味追隨傳統的筆墨,總是會顯露出寫生的痕跡。寫生的意義其實不在寫生本身,而在于面對真實的生活和鮮活的生命,如果沒有對生活的真實感受,即使是寫生也會走向“油滑”,現在很多寫生山水是練的寫生畫法,而不是感受生活,也成了千篇一律的公式。
徐堅偉對此是很有認識的,他在筆記中談到,齊白石“無作家習氣“,黃賓虹不顯“畫家畫”,吳昌碩不是油滑空洞。任何筆畫畫法都是可以學到練到,但要得觀察生活之理法卻是不易做到的。觀察生活固然重要,更重要的可能還是體驗生活。體驗生活就是體驗自我,徐堅偉對藝術的這種認識可能還不是來自藝術自身,我們在他的畫中看不到一點西方現代藝術的痕跡,他談得最多的都還是中國傳統水墨畫,但怎樣把傳統的語言變成表達自我心性的方式,卻是沒有現成的答案。
一個藝術家在進入自己的圖式之前,總是受預成圖式的支配,決定預成圖式的重要因素有二,一是藝術家的早期生活,無意識的記憶作用于圖式的選擇;另一是藝術家的早期教育,尤其是在不自覺中練到手熟,怕是一輩子都甩不掉。這兩者對徐堅偉都非常重要,傳統不能丟,生活要堅守。實際上是生活改造了他的藝術,而在學校期間更多的是現代藝術的影響,他不是學的現代藝術的樣式,而是現代藝術的精神,尊重自我,表現自我。
我們無法知道徐堅偉童年生活的記憶怎樣留存在他現在的藝術中,但他現在對生活的體驗卻滲透到他的形式中。生命的記憶總是被現實喚醒的,對于徐堅偉來說,就是大學畢業后在大山莊的一段生活。在他的畫面上總是會出現蒼涼的村莊與荒原,沒有背景,沒有近景,既是水墨又不著意傳統筆墨,既是寫生,又不完全是真實場景;好像是心靈的感應和內心的獨白。
他的筆記中有對農村的印象。“農村田野的樹杈上掛滿了破碎的塑料袋,摻雜著北風卷起的黃土,望去一片荒蕪。““在似凍固的空氣中,從遠方破柵里傳來捆豬時所發出的尖冽的嘶叫聲,令人感到天空的陰沉與寒冷。“再看他的畫,一種難以言狀的孤獨,空曠的荒原上孤零零的村落,一片荒草,后面一片白水,再往后還是一片荒草,幾棵孤獨的樹。
即使是夏日的風景,也是一堵殘缺的墻,一棵孤獨的楊樹。這些畫好像是內心的獨白,是說給自己聽的。在這些畫上,寫生的成分似乎更多一些,但又不完全是寫生,似乎是從自己的窗口看去畫的一個“局部”。一般的局部是截取畫面的一部分,他的局部是將個別的東西從整體中抽取出來,好像是把花鳥畫的構圖用到風景中,只有大片的空白,單個的景物被巨大的空無所壓迫。徐堅偉的畫是有生命的,不是他畫得多么生動,而是他自身生命的投入,生命的意識融入到他的形式中,使形式也具有生命。
幾根樹枝斜著插向天空,兩只小鳥掠過樹梢。這個畫面似乎是徐堅偉的寫生風景的延伸,仍然是從窗口看到的景色。把這幅畫分解來看,可以看出徐堅偉的花鳥畫的獨特之處。鳥的畫法還是比較傳統,樹枝則是寫生與傳統筆法的結合。空曠的背景不是無意義的空無,而是實體性的負空間,承載著情感和意志。
徐堅偉確實很崇拜傳統的筆墨,對于歷代大師的用墨用線也有很多獨到的理解,但在他的畫中,筆墨被孤立起來,服務于他對生活的觀察和體驗。用現代藝術的批評術語來說,形式是藝術家個人意志的再現,或者說是藝術家個人情感的符號。傳統的筆墨是在一定的程式和秩序中,筆墨的訓練就是熟悉和掌握這種程式,但重復的是古人的符號。徐堅偉沒有走這條重復之路,但也沒有拋棄傳統,他仍然在畫花鳥,寫生是生活的參照,也是對他的花鳥畫的解讀,因為他的花鳥早已不是傳統的花鳥。正如人的生活有其表象和內在之分,徐堅偉的花鳥與他的生活態度也有兩個層次。
作為表層的是他根據生活的經驗更換了花鳥的題材,這點可能并不新鮮,因為很多人都這么做過,從生活的環境中尋找花鳥的旨趣,在他的畫中就是鄉野的蟲草、莊稼等等。但這點對他卻很重要,題材帶來格式的變化。那些不講規則甚至有些笨拙的構圖真正畫出鄉野之野。野性是對優雅的顛覆,是生命向其原始本性的回歸。這就涉及他的繪畫的第二個層次。徐堅偉的花鳥一點不輸筆墨,甚至還有老辣之感,但他的“老辣“是局部的,就像他的寫生風景一樣,局部的筆墨從整體中抽象出來,傳統的秩序被他打亂了,秩序的成分被他重新結構和組合。
他那種隱藏得很深的功底在每一個局部都顯示出來,但每一個整體都不是傳統的秩序,而只是他自己的表現。在一幅畫中,有一個巨大的樹根和一片深黑的泥土,筆墨的層次表現得淋漓盡致,泥塊的勾勒像古人畫水紋一樣,都是象征的符號。但構圖卻不合章法,樹根直插畫面中央,泥土水平地分布兩邊。這不是一種入畫的趣味,而是一種記錄生命的方式,它顯得沉重、滄桑而頑強,只有走過泥土才能看到它的存在,而且只有從中體驗到自我才能表現它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