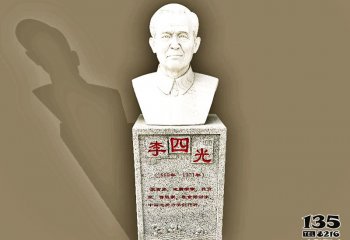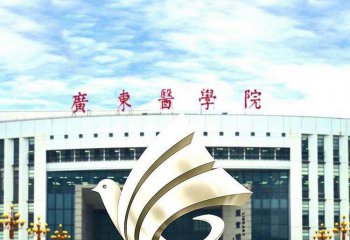英國雕塑家葛姆雷的能力使他超越圈子,走進公共空間,與大眾直接發生關系。而且他是一位具有雄心壯志的藝術家,想做前輩藝術家不能做到的事在倫敦市中心的肯特停車廠,一座巨大的人物雕塑矗立在那里,突兀而震撼。這個被命名為“藝術天使”、高達7米的龐然大物,實在是無法不讓人舉頭觀望。它是一場特別藝術展的作品之一。倫敦的市民有福了,因為他們不用花錢買票就可欣賞到有趣的雕塑作品展覽。這場雕塑展屬于英國著名雕塑家安東尼·葛姆雷。
這位戴著眼睛,看上去文質彬彬的雕塑家早已享有全球性聲譽。2003年,這位雕塑大師曾和中國有過一次親密接觸。他的作品“土地”曾在廣州、北京和上海展開巡展。由300位中國人燒制出的12萬個小泥人所組成的“亞洲土地”,曾讓人欣喜地領略到當代雕塑藝術的魅力。
安東尼·葛姆雷于1950年出生在倫敦。1994年,他獲得了視覺藝術中的奧斯卡獎—特納獎。獲獎作品是鑄鐵作品“檢驗一個世界觀”獲得大獎。葛姆雷的此次個人作品展將在英國持續展出3個月。在葛姆雷的這次作品展中,“藝術天使”用廢棄的桌子、椅子、柜子、電子琴、沙發、衣服等材料做成,并非傳統意義上的雕塑作品。
其“雕塑”過程是一個巨大的工程,也不是雕塑家個人所能完成的,有一幫工人參與了制作過程。作為此次葛姆雷個展的代表作,“藝術天使”將在展覽結束時,被點燃燒掉。葛姆雷似乎有點偏愛大型雕塑,他最著名的作品“北方天使”也是一個龐然大物。這座巨型守護天使屹立在英國蓋茨黑德,這座早已蕭條的煤礦及造船城市。“北方天使”高20米,擁有波音767客機航翼般的巨型翅膀,屹立在城市的最高山坡之上。因為這座著名雕塑,凋零的蓋茨黑德再次吸引了世人的眼光,竟奇跡般地復蘇起來。
當地人萌生了把蓋茨黑德建設為藝術之都的大膽設想。在這個夢想的引導之下,一些現代的畫廊和音樂廳正在建造中,蓋茨黑德逐漸改變了城市品位。在美國《新聞周刊》評選的全球八大創意城市中,蓋茨黑德名列其中。一件藝術作品竟如此奇跡般地改變了一座城市的命運,這實在不能不讓人驚嘆。“垃圾人”是另一件大型雕塑,高達23米。和“藝術天使”一樣,用廢棄的桌子、椅子、柜子、沙發等垃圾材料搭建而成。
曾被安放于英國馬爾蓋特市廢棄的夢境主題公園內,在數公里以外就能看到它。“垃圾人”的命運也和“藝術天使”一樣,在展覽之后被燒毀。葛姆雷所酷愛的鑄造鐵人也是此次個展的重要作品。這些鐵人高1.96米,重650公斤。有意思的是,它們都是以葛姆雷的身軀為模子鑄造出來的。葛姆雷把自己裝在塑料袋里,鑄成鉛模。這是一個緊張而危險的過程,讓他體驗到了他和自己的身體的關系。此刻,有的鐵人被安放在倫敦市中心的建筑物頂上,有的正站在街頭的某個角落里。
倫敦的市民隨時都可能與他們偶然相遇。而其中的100個鐵人正站立在英格蘭默西塞德郡的克羅斯比海灘。英國政府已允許此作品被永久安置于此。這個被命名為“另一處”的作品成為克羅斯比海灘上有趣的一景。隨著潮漲潮落,這些真人大小的鐵人將與天地、大海日夜相伴。葛姆雷是公共藝術的積極實踐者。他的雕塑作品總是不甘于被局限在狹小封閉的展覽空間里,或者走進擁擠嘈雜的城市中心,或者屹立于廣闊的自然天地。無論是“北方天使”、“藝術天使”、“垃圾人”,還是“另一處”,都是公共空間內的藝術品,開放地融入進周遭的環境之中。
“我覺得藝術就應該貼近人們的生活,我不認為藝術是一段時間內的憑票入場的展覽。如果在我們的公共空間里有一些有創造力的東西,可以讓生活更有趣。那是一件多好的事。”在此次個展的開幕式上,葛姆雷這樣說道。在中國之行中,他也曾說過:“我想達到徹底的開放。
”任教于中央美術學院的藝術家隋建國,對葛姆雷評價頗高。“他是一位超級藝術家,立足點很高,他的‘亞洲土地’的作品,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參與作品的人很多,效果非常震撼。其實,也很難界定他的作品,可以說是雕塑,也可以說是裝置。”“一般藝術家在藝術圈內瘋狂,但是葛姆雷的能力使他超越圈子,走進公共空間,與大眾直接發生關系,所以說他是大師。
而且他是一位具有雄心壯志的藝術家,想做前輩藝術家不能做到的事。”在5月17日的個展開幕式上,安東尼·葛姆雷展出了最新力作“迷光”,在英國藝術界引起轟動。“迷光”是一個裝置作品,主體是一個8.5×10×3米的玻璃房。參觀者走進玻璃房后,將被白色迷霧籠罩,能見度只有幾英寸,只能伸手摸索著前進。玻璃房內只設有一個很小的出口,在迷霧中非常隱蔽,要找到它得頗費力氣。另外,地板上還有水,葛姆雷給參觀者又設置了一重障礙。“這個裝置內部能見度很低,地上還有水,進去就找不到方向,而且僅一個進出口,建議有哮喘、幽閉恐怖癥或神經質的人進入前做好準備。
”為了確保參觀者的安全,藝術館特意寫出了這樣善意的提醒。參觀者在玻璃房中迷失并產生不安、恐慌和焦慮,而這正是葛姆雷希望看到的效果。“一方面,你失去方向感,突然迷失在空間中,很焦慮,但也會有一種欣快感,身體忽然自由了,回歸到新的狀態。這是氣候性的經歷,也是社會性的體驗。就像兒時早上醒來發現外邊大雪紛飛,你只想出去扔雪球。你在玻璃房內的感受也是如此。”葛姆雷這樣解釋“迷光”和參觀者共同產生的體驗效果。
玻璃房一次只允許25位參觀者。在葛姆雷看來,參與者也是這個作品的組成部分。這種想法仍然和他所追求的“徹底的開放”一脈相承。他說:“光和水是展覽的兩種元素,第三種是參與其中的人,我對參觀者置身其中的場面很感興趣。這是一個開放式作品,讓生活與藝術結合在一起,我試圖讓它越簡化越好,玻璃房子雖小卻有一片未知的云。”在葛姆雷的設想中包含著一股浪漫的氣息。隋建國則這樣評價葛姆雷的新作品:“他的作品關注的是兩個元素,身體和空間。
他把身體當作世界的一個細胞,用身體去感知世界宇宙。而‘空間’也始終是他的關注所在,所以他的很多作品都被置放于公共空間中。‘迷光’同樣也是關于身體和空間的探討,他關注身體在玻璃屋這個空間的感受。平時,人們總是習慣用視覺去看空間,而在玻璃屋中,人們將用觸覺,用身體去感知空間的存在。
”英國的評論家們對“迷光”同樣頗有好感,甚至充滿了期待。他們認為葛姆雷的這件新作品是“非常有效果”,將會吸引公眾的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