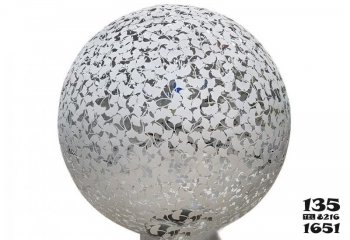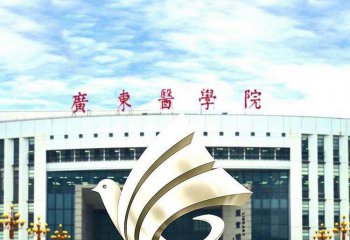曾幾何時,進駐“新家”的藝術家們感慨,在市中心黃金區域以每平方米每天不足1元的價錢租下近百平方米工作室,簡直像是“天上掉下了餡餅”。現如今他們又在擔心,這個餡餅什么時候會不見了。威海路696號,原上海元件五廠廢棄的廠房和倉庫的一部分,隱匿在陜西南路與茂名南路核心商業區的小弄堂里。很多人每天上下班從這里經過,卻不知道這條幽深的弄堂內藏著一幢英式風格的產業建筑,歷史的風霜早已讓它失去了昔日的風貌和輝煌。
眼下,這里成了藝術家理想的天堂。從去年10月開始,來自世界和全國各地以及臺灣地區共30余名藝術家迅速聚集于此設立自己的工作室,從架上繪畫、雕塑、攝影、影像、觀念和裝置藝術到平面、時尚和造型設計等,豐富多樣的藝術形態讓威海路696號迅速成為城市藝術新地標。最早發現威海路696號的是在汽車界鼎鼎有名的攝影師龔振宇,緊隨其后的是廣告界的資深導演,現已成為職業藝術家的馬良、來自法國的設計團隊STUDIOZERO、來自英國的藝術家ChrisGill和來自日本的藝術家萬里。
原桂林愚自樂園和上海月圓園雕塑公園的藝術總監蕭長正、為好萊塢電影提供造型設計的豆豆以及服裝設計師吉承也在此租賃了工作室。一直從事繪畫藝術的吳曉寧說,“現在想來,在威海路這樣一個時髦地段,和朋友擁有一處200平方米的工作室,幾乎是一種奢侈了。
每天來畫上幾個小時,不少時間勻給了喝茶、聊天和逛街。陽光好的午后,朋友們閑聊之后散去,畫室里驟然安靜下來,放一段舒緩的音樂,翻翻畫冊,忽然會覺得,自己是不是幸福過頭了?”吳曉寧的工作室幾乎沒做額外的裝修。只花了600元上上下下粉刷了一遍。“沙發是二手市場淘的,900元,最貴和最實用的是畫室中央的一張乒乓球臺了,利用率極高,1000元的付出使得每個來畫室的人都要沖殺幾個回合,達到了強身健體的初衷,所有費用加在一起控制在5000元以內。
”從杭州鳳山藝術空間來到上海696,周華海說自己就是喜歡這里的風格——時尚、前衛。“如果說,杭州鳳山藝術空間代表著小橋流水、楊柳依依的江南風景,上海696就代表著摩天大樓、川流不息的現代風情。”馬良的工作室在三樓,大約有230平方米左右。他的房間里有一面墻是原來的老建筑的外墻,紅色的磚結構的建筑外立面,有高大的鐵窗和落水管道,如同舞臺布景一般突兀地出現在室內。
而馬良說這是他最喜歡的一個細節。“除了屋子到下雨天有幾處程度不同的漏雨,冬天非常寒冷這兩個微不足道的小毛病,我覺得一切已經很完美,是我從小夢想中的馬良工作室的樣子。”馬良有收藏的癖好,多年來搜集了很多奇形怪狀的東西,如今他終于有了一個空間將它們好好陳列出來。“看著這些‘破’玩意兒滿滿當當地填滿了我的工作,也填滿了我的生活,真是從心底里感到快樂。我的拍攝需要做很多準備工作,設計道具和制作服裝等等,以前我必須干完一件后,全部收拾起來,再鋪開另外的思路重新開始。因為工作室只有20平方米,實在周轉不開。
現在好多了,所有事情同時兼顧,環顧我作品里將出現的一切就在身邊眼前,工作上便利了太多。“以前,在弄堂里籌備和拍攝我的作品,總是被鄰居指指點點,視為異端,居委會大媽都來視察過,在確定了我的畫室不是地下工廠之后,才滿臉狐疑地離開。而現在,在這個696倉庫里,我終于不算是異類了。”馬良說自己每周工作6天,除了外出旅行,他最愛的事情就是把自己關在工作室里,呆著。他打算天氣暖和一點搬到工作室來住,像勞模一樣“愛廠如家”。
盡管這些身處“邊緣”的藝術家們非常喜歡這座銹跡斑斑的百年老建筑,但是由于種種原因,有傳言這幢英式風格建筑將于2007年6月拆除,他們開始變得惶恐不安,本來有打算進一步裝修工作室的一些人也暫時將想法擱置起來。為了記錄這段短暫的歷史,《威海路696——上海當代藝術狀態及開放的工作室》眼下正在開展。
它包括兩個部分,一個是在上海多倫現代美術館舉辦的《上海當代藝術狀態》,30多名藝術家以威海路696號這個集體的身份參加展覽,豐富多樣的藝術表現方式展示上海當代藝術現狀的一個斷面。與此同時,在威海路696號,藝術家的工作室統一開放,成為這個主題展覽的一種延展和繼續。30多名藝術家希望借助這個展覽表達對威海路696號的熱愛之心。本次展覽的策展人張冰認為,在商業繁華的中心城區,一個不以營利為目的的藝術家聚集區,如果可以合理地規劃,對于上海在國際社會中的文化形象提升以及周邊商業的帶動都會產生不可估量的價值。
“我們在談論威海路696號的未來時,追溯上海當代藝術園區的形成發展歷史不無裨益。2000年藝術家丁乙租賃了西蘇州路1131號的一處‘紅樓’作為自己的工作室,不久藝術家和畫廊也逐漸進駐此地,但是隨著西蘇州路一代房地產的開發,1131號和其他一批老廠房和老倉庫很快被拆除了,藝術家們最后遷入今天的莫干山50號。
“在這一過程中,同時著名的事件還有浦東大道2970弄3號樓的藝術村,業主一開始以低廉的價格將毛坯房租賃給藝術家作為他們的工作室,到了2003年,在上海樓市暴漲的強大攻勢下,業主將畫家村所在的樓宇整體出售,結果是畫家們被勸退出所租賃的公寓。”藝術家的夢想遭到市場經濟的強烈沖擊,最后不得不以藝術家的讓步為結束,這一結果取決于早期藝術園區自發聚集的現實狀態以及其產生的時間節點。
2004年轉機出現了。上海率先提出了“創意產業”這一概念,并將創意產業的規劃內容列入《上海2004-2010文化發展規劃綱要》,藝術產業也在其中。隨著相關政策的出臺,包括莫干山路50號、泰康路田子坊和四行倉庫等在內的許多藝術園區得以保存下來。這些已經掛牌創意產業基地的藝術園區大都建在一些老廠房和老倉庫內,為這些本已廢棄的歷史建筑注入了新的活力,并為上海城市產業遺產的保護和再利用探索到一條可持續發展的道路。
威海路696號會不會成為其中的一員?目前我們尚不知道答案。不過在這個每天都有許多改變的城市中心地帶,它的存在已然是一個異數。若它還能以這樣堅守的姿態存在下去,那就斷然不會是過把癮就死的悲愴結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