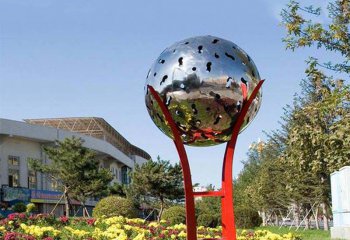“婉孌不終夕,一別周年期。桑蠶不作繭,晝夜長懸絲。”近日,新生代導演李玉正以此詩的韻律,和著舞蹈藝術家黃豆豆手持絲綢剛柔并濟的肢體演繹,在Hermes絲巾藝術展中,上演著一幕影像藝術。同時,Chanel預熱許久的MobileArt也終于憑借Perre這讓記者回憶起千禧年時,日本藝術家村上隆因在原本穩重的LVMonogram系列畫上卡通造型的眼睛和櫻桃,引發了時尚界與藝術家合作的風潮。如今,他所崇尚的“一流的作品就是被很多人理解的作品”已被業界奉若圭臬。

在中國,伴隨國際頂級時尚品牌市場的日益擴大,具此風尚的藝術家也初顯端倪。然而,這種趨勢的風行是藝術發展的新生力量?抑或只是一場國際品牌一廂情愿的“行為藝術”?“對絲巾,我仿佛在印制一幅絲網版畫,秉持慣有的抽象筆法,我融進了傳統與現代、欲望與理想、虛夸與嚴謹、混亂與次序的矛盾美學,讓由此產生的相互對抗和競賽的力量組合成交替起伏的畫面韻律。”配合李玉執導的影像,Hermes同時高調發布了由著名抽象藝術家丁乙設計的“中國韻律”款絲巾,這是其旗下第一個由中國藝術家設計的作品。

在丁乙看來,自己個性化的十字符號在如此的藝術成品中更以一種理性的姿態表達著他內心的世界,“我就像完成一個命題作文,在不同的主題下,用夸張的光與色裝扮和呈現著刺激的表面肌理,濃縮起那些未被展開的故事”。此外,以Hermes70年中遴選出的46款絲巾為“道具”,美國藝術家HiltonMcConnico更是用“大隱隱于市”的中國手法完成了21部裝置藝術杰作,最特別的莫過于搭配中國苗族的繡片圖案用絲巾扎成的大紅燈籠。Hermes藝術總監Pierre-AlexisDumas在評論這樣的創作時說:“嚴謹的絲巾框架允許藝術家最大限度地展現自己的創造力。

中國舞蹈和抽象藝術具有流動而不可捉摸的氣韻,這與絲綢的閃亮與質感恰恰不謀而合。依稀記得藝術家丁乙的設計草圖為我帶來的第一次驚艷,宛如十字繡法的畫面完全打破他先前的風格,他不是專職設計師,每一個筆觸下卻鐫刻著他強烈的個人符號。可以預見,這樣的藝術與絲巾邂逅,固然是一場不可多得的視覺體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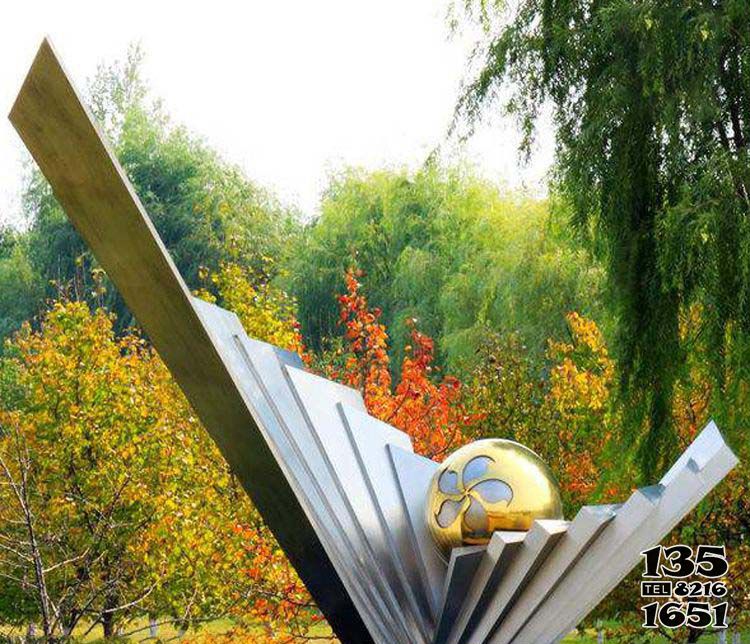
”無獨有偶,在李寧運動系列舉辦的“SayNoToLimits”活動現場,擅長以墨繪畫的日本藝術家茂本用水墨涂鴉的手法一氣呵成了定義下的“連貫投籃動作”。與丁乙的風格堅持相比,茂本與“李寧”的合作似乎更具藝術創新的力量,“我沒有學過傳統日本畫和中國水墨,在我看來‘以墨于紙上創作’和‘水墨畫’是兩個概念,后者有其技巧和值得繼承的價值,但于我,目的就是以墨的形式去改變一切。用傳統墨來表現現代運動的動感,在用筆的所到之處則需要不同以往的剛韌和張力,這意味畫面表達著一種想象之外的自信與活力”。

縱然FabriceBousteau大肆地宣傳著Chanel經典菱格紋包才是MobileArt的最終旗幟,但依然無礙美籍日裔現代藝術家、著名“披頭士”主唱JohnLennon遺孀小野洋子在個人風格上的“固執”:“在MobileArt設置人人都可祈禱的‘許愿樹’,其實在28年前John去世后我就播種下了。把寫滿心愿的紙條放入雕塑塔中,仿似一尊強大的圖騰。
這是Fluxus的行動精神,更是我完成的一次絕美行為藝術”。同樣,在2007年韓國當代藝術家GalleryARTSIDE力邀的包括方力鈞、周春芽、劉野、岳敏君等在內的15位藝術家創作的112種藝術商品中,方力鈞的“光頭漢子”、俸正杰的艷麗色彩、李金德的現代水墨和周春芽的“綠狗”等,都以其鮮明的個人特色,以領帶、手冊、名片夾、鐘表等為人熟知卻又陌生的“藝術形態”,不動聲色地傳遞著各自的藝術感染力。
由此看來,在與各大時尚先鋒的聯姻下,藝術家大多依然理智地保持了自己獨有的藝術個性。北京電影學院新媒體實驗室主任劉旭光教授對此表示:“藝術是人類表達精神世界的方式,它的生命力就在于無限的融合。之于時尚品牌,藝術當然是助推它的美麗袈裟,任何藝術創作在有形的載體下都會受到約束,這不僅是設計師和藝術家最大的區別,也是當下品牌商偏愛藝術家的重要原因。之于公眾,藝術是小眾的艷羨,從另一個角度看,與時尚結合恰是藝術在某一領域的最大化個人傳播。
而在日益走強的國際藝術品市場,這也不妨是成就一名藝術家的另類方式。”《紐約時報》曾指出,在藝術家與時尚的合作中,藝術的注入可為品牌帶來年收入上億美元的進賬。有人說這是“財富可以給任何人指引通向上流社會的道路,但高貴的藝術魅力卻無價”的映照,但央視品牌顧問、中國品牌建設第一人李光斗卻以“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的“情感營銷”對此解讀:“這是一個情感經濟的時代,真正的行業翹楚不是在資產排行榜上,而在人們的心中。
動輒幾千萬的藝術拍品市場,無一不是‘特色情感’的產物。情感創造財富,亦在創造藝術。從某種意義講,藝術價值需要價格的評斷,當它有了可落腳于當代的學理突破,現代商業文明也就與文化藝術構筑起了新的價值觀體系。”也許,引用北京今日美術館館長張子康的話以此詮釋“藝術+時尚”更為恰當,“自我從事藝術工作以來,便常常陷入矛盾或悖論的氛圍中,總滿懷英雄情結以二元對立的眼光審視周遭:傳統與現代的對立、商業與非商業的對立、純粹與混搭的對立、形式與內容的對立。而在當代、抽象等多種藝術從地下走到地上,藝術市場空前繁榮之后,用貫通社會各領域的資源與智慧,創造大社會概念下的大藝術,或許方是藝術生命常青的情境與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