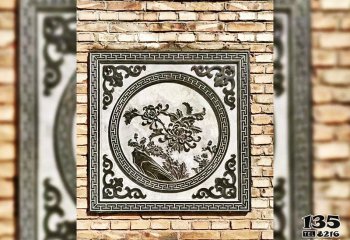日前,在北京華僑城展出的第三屆“全國高校畢業生優秀雕塑作品展”上,來自全國27所高校的120余件雕塑作品接受了專業和大眾的檢閱。清華大學美術學院副院長包林說:“總體情況不錯,很多學生對社會有著強烈的關注意識。”也有些學生的作品引來爭議,“讓人摸不著頭腦,看不懂,有故弄玄虛之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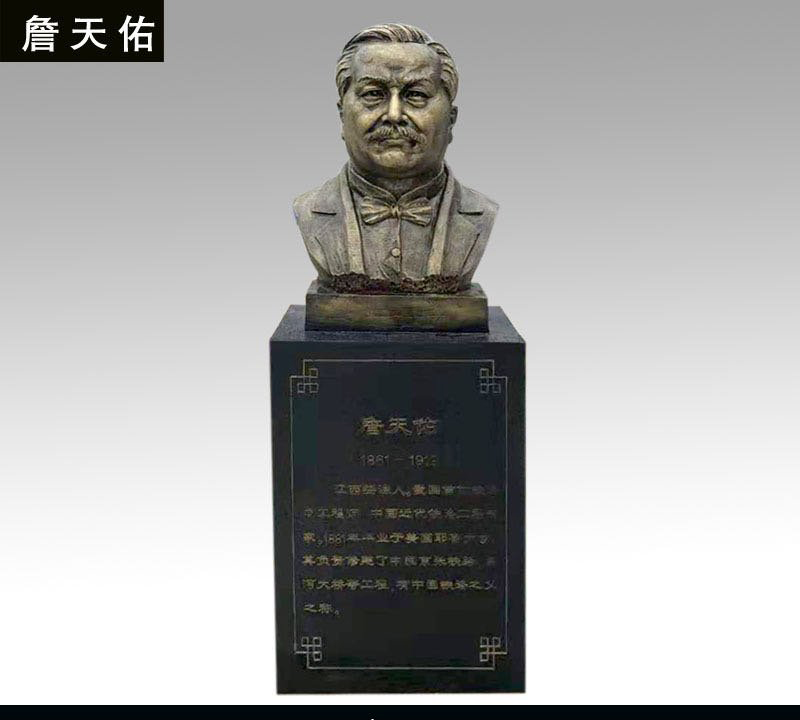
”雕塑家錢紹武如是評價。造成雷同和怪異的原因是什么?這次雕塑展中有些作品讓專家直呼“看不懂”。“我在西安時沒有看懂,這次到北京來還是看不懂。藝術創作,要考慮給誰看、對社會有什么回應。現在,國家富強了、學校條件好了,但若我們專業圈的都看不懂,怎么指望一般老百姓能欣賞?
”西安美術學院原院長陳啟南說。“現在很多作品力求新鮮,怎么怪怎么畫,就像小孩想引人注意就怪叫一聲一樣,感覺太浮躁、太急功近利。這實際是走向了極端。”錢紹武認為,一切文化藝術都應具備基本交流的可能,個性還要與共性相結合。而藝術作品只有與觀眾對話,才能進入流通領域,體現自身價值。有關人士指出,本次展覽在保持總體水平的同時,不乏雷同和怪異之作。貌似現代的骨架卻缺乏文化血氣,造成這種雷同和怪異的原因很多,但學院教育及市場因素首當其沖。
學校教育中對中國傳統造型精神和中國文化精神的吸納沒有足夠的重視,同時,市場誘惑也給學生創作造成了巨大沖擊。“藝術的商業化幾乎深入到每個學生的心里,當然部分有藝術理想的人會以一種拒絕的方式應對,但社會的潮流如此,我們也不由自主地被推著向前。”某校一畢業生說,“學校對基本技法非常強調,但其他方面有所缺失。例如,我們都知道,中國的民間藝術和傳統文化會對作品造型產生良性影響,但找不到具體的學習途徑。
我們學校沒有相關課程,而去博物館、劇院的機會也不多。”深圳雕塑院院長孫振華則從另一個角度解讀看不懂的原因:“知識來源的不同是重要原因。如今學生的學習已不局限于學校教育,很多人的作品從構思、材料及色彩搭配上都非常詼諧,有著濃重的網絡和卡通色彩,所以有時會連老師都看不懂。”但孫振華同樣認為,雕塑家應該在大眾性與藝術性間作出選擇,一方面要考慮到百姓的需求,要有民族特色,另一方面也不能一味迎合市民,降低雕塑的品位。“如果僅僅只是看不懂倒無須驚訝。
”中央美術學院雕塑系副主任王少軍認為看不懂背后有知識背景的原因也有觀點的對立,藝術應允許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但藝術本身不應該有污泥濁水。師承關系模糊是圖像時代的產物?“我看了展覽之后,很大的感受就是:誰是他們的老師?
”孫振華說。他所指出的正是如今美術院校師承關系漸趨模糊的現象。孫振華認為,這是社會發展的必然,也是圖像時代、媒體時代的特點。如果說,以前學生的知識包括基本的技能、技法、觀念等主要來自于老師,老師對學生的思維和創作有著絕對的影響力和控制力,但隨著圖像時代、媒體時代的到來,學生可藉各種媒介獲取他們需要的知識,老師在這方面已談不上多少優勢,更有甚者,在對信息的敏感性、圖像的感悟等方面還可能超過老師。因為藝術的獨特性,這樣的“模糊”在如今的校園里是被提倡和鼓勵的。
“我們有時候會和老師在課上爭執,表達不同的觀點。我學了5年雕塑,我希望老師教出來的是獨特的我,而不是另一個自己。”雕塑系學生顧健說。在王少軍看來,如今的學生是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接受教育,除了專業知識的研習外,要多學習老師的治學方法和治學精神。同時,他們的創作應更加放松、自由,更加具有這一代人的色彩。我國公共藝術建設難在何處?雕塑畢業作品展的舉辦地從第一屆的中央美術學院到第二屆的清華大學科技園,乃至此次的北京華僑城公共藝術街,清晰地反映出雕塑藝術一步步地從校園走向公眾的軌跡,雕塑創作所具備的公共性在逐步增強。
“雕塑與公共藝術”因此也成為本屆畢業展的熱議話題。“今天中國的公共藝術教育還缺乏深層次的討論。”雕塑家王中說:“其實我最初是反對把公共藝術設置成一個專業的,但從去年開始,我改變了自己的看法。在加速的中國城市化進程中,城市規劃、城市雕塑與公眾的公共需求所引發的問題,是我們在特定歷史時期需要解決的。
首先要解決理論梳理問題。現實情況是設有公共藝術專業的學校不少,但是普遍缺乏理論積淀。”雕塑家陳云崗思考的則是,怎么讓公共藝術真正進入教育領域,如何設立相關課程。除了理論思考的缺乏,“官方意識”在某種程度上也影響了公共藝術的良性發展。目前的情形是,很多藝術院校的教師和學生都在參與國家的各種大型項目建設,包括城市雕塑及各種設計等。
“但這種參與更多的是一種甲方和乙方的關系,是一種合同形式。很多項目必須符合官員意志,政府才會埋單。”在包林看來,公共藝術的推動與發展在某種意義上還缺少一種制度化建設,也缺少公民的有效參與。“公民的參與實際上是一種形式,但這種形式非常重要,它體現在公民社會建立過程中每一個公民的自覺性。
雖然目前我國的公共藝術發展很快,但體現的官方意識仍然很重,專家與百姓的意見有時仍然難以表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