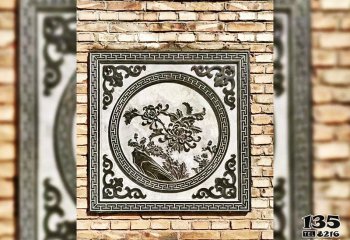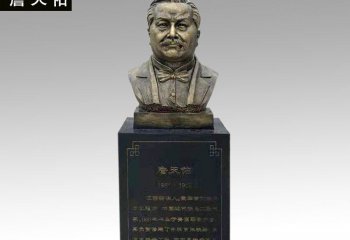機構對藝術品的收藏,其實早在1995年便已開始——中國建設銀行總行以605萬元人民幣收藏了“文革”時期的經典之作《毛主席去安源》,一舉創下當時中國油畫拍賣紀錄。這一數字相當于中國嘉德1994年至2001年間油畫雕塑專場一場大拍的成交總額。而此間,大陸僅有嘉德一家在持續推出油畫雕塑專場,因此這605萬元也就相當于當時整個油畫雕塑拍賣市場的份額。

換句話說,建行超乎常理出牌,用可以買一個整場的錢,買了一張畫。據統計,嘉德、保利、佳士得、蘇富比的油畫雕塑及當代藝術拍賣,現在每家每季的拍賣成交額均在1.5億元至4.5億元間,整個行業的季度拍賣額保守估計也在10億元左右。以此推斷,如今中國美術史上最出色作品的價格拍出近10億元,才可真正稱得上咋舌。我們不是鼓勵,也不希望迅速出現如此高價,但最出色的作品如果過億元大關,應該是可以接受的。目前,逾5000萬元的作品已經有4件。

這些作品中除了徐悲鴻作品外,均是大尺寸且由多幅組成,從這個意義上說,并不比當年的605萬元貴。之所以沒有出現億元作品,筆者認為,是因為沒有緩慢但持續增長的資本與機構進入,機構收藏沒有在真正意義上啟動。一般而言,私人收藏是個人喜好與趣味至上,機構收藏卻要放在藝術史的脈絡上,不能按一時市場價格出牌。對于有價值的作品,可以以市場數倍乃至十數倍的價格購藏,也可把暫時沒有市場的門類納入收藏視野,關鍵看是否有藝術史的意義,而非看短期市場表現。對于機構而言,不是不談價格,而是要談就談10年后,這件作品還會不會有價格?

它在藝術史上還能不能被提及?雖然貴的作品未必是好的,但好的作品一定是貴的。機構收藏不怕作品貴,就怕作品不好。這就涉及到收藏的精要:精品至上。評判者無疑首先要純粹,要客觀公正。而純粹的前提是經濟的獨立,避免陷入藝術品的交易。真正的經濟獨立,對大部分目前的評判者和未來的評判者來說是困難的,因為文字的酬勞還不夠買書、買畫冊。研究者需要機構的支持,其產生的結果反過來會讓整個行業受益。

在我們身邊,有的收藏者可以短短幾年內花費數億資金收藏藝術品,卻舍不得拿出百分之一進行理論研究的贊助。這些錢對很多收藏者來說也許算不上什么,對企業家來說也是小錢,但對藝術史研究者來說,卻可以資助近百項碩博士研究課題,它所創造出的價值、產生的連帶效應,卻遠非百倍。許多收藏者之所以不愿意對理論研究進行贊助,一是因為學術的贊助是長線的,短期似乎看不到什么回報,二是因為中國沒有藝術品抵稅制度。所以,對于機構收藏來說,可以隨時進入收藏環節,沒有合適與不合適的時候,但要有選擇;

進入時,一定要按照史學脈絡進行判斷,寧可高價集中買精品,不圖便宜買很多,寧缺毋濫,不隨一時市場;在起步階段,便可直入深層次,把看似無用的理論建設納入視野。雖然早在十幾年前中國已有機構介入藝術收藏,但畢竟只是個別行為,沒有制度化,金融機構和藝術的緣分無論從時間的長度,還是合作的力度均無法同瑞銀集團、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銀行等機構比擬。從私人零散的收藏轉到機構收藏、公共收藏,不僅需要法律制度層面的配合,更需要觀念的深層轉變。
先行者必有巨大回報,藝術品收藏無論是對企業長遠的資產增值,還是對形象與品牌的塑造均有很大益處——眼光與魄力的能量從來都是超乎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