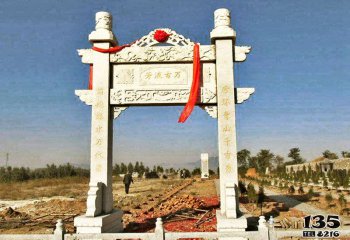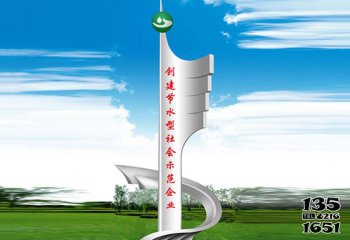今天,亞洲當代藝術倍受國際廣泛關注,亞洲認同也隨之得到提升。這種文化轉變顯然與“冷戰”后尤其是全球化帶動的亞洲國家經濟迅速發展和民族意識的不斷增強有關。那么,為什么亞洲藝術問題要被提出呢?盡管亞洲藝術開始在國際上受到廣泛關注,但還是缺乏對亞洲藝術所包含的差異、傳統、民族、宗教、習俗的細察和深究,基本上停留想象的亞洲。
因此,問題的提出也就是思考和行動的開始。倘若要認清亞洲當代藝術在國際上的獨特性,就需要將亞洲當代藝術置于歷史語境與現實發展的聯系中加以考察。實際上,談論亞洲問題,一個主要針對的是歐洲中心主義的取向,因為亞洲地區的歷史是被西方中心主義的歷史觀所籠罩的;
另一個針對是在亞洲內部發現超越民族國家的政治結構的想象空間。對于民族國家的預設和想象則是要把國家作為一個重要的核心。如果要想象一個超國家的空間,那就應采取一種批評以民族國家為中心的民族主義取向。這種以一種區域政治結構來迎接和抗拒全球一體化的思路無疑是受到了歐盟模式的啟發和影響。歐洲已形成了超越原來民族國家的新的經濟和政治結構,以迎接全球化帶來的巨大挑戰。當然,歐洲的文化發展也正是建立在這樣一個超民族國家的整體政治架構之上的。
因此,在這種對照之下,亞洲問題就顯得非常的急迫和重要,既然藝術是一種文化理想的形式,那么以藝術想象來解釋和建構超越亞洲性的可能性就顯得格外具有現實意義。今天,對亞洲當代藝術的研究,它仍要被置于一個歷史范疇的概念來思考——它蘊涵了差異和身份、傳統與現代、里與外、包容與排斥相關聯的多樣性和復雜性。事實上,如果要認識亞洲的當代藝術,應以理解“亞洲”一詞的歷史內涵為前提條件。
雖然“亞洲”在地理上很容易描述它的位置,但它在文化上是個難以澄清其內涵的概念。這主要由亞洲文化包含的豐富而復雜的多樣性所決定,因為無論是在宗教、文化、傳統習俗,還是在現代化進程和社會體制上皆存在差異性。倘若以歷史角度看,亞洲一詞最早不是由亞洲人提出的,而是由歐洲人提出的概念。Asia一詞最早是指希臘以東的地區,包括了今天的土耳其一帶。
在早期歐洲的概念中,亞洲就等于是東方之意,后來就衍生出了遠東和近東的概念。17世紀以后,亞洲與歐洲的殖民主義擴張的地理概念相聯系。可以說,19世紀以前亞洲人對自身歸屬亞洲的概念是含糊不清的,準確地講,亞洲一詞來自它之外的世界,即來自西方殖民主義對一個不同時間和空間位置的定義,也就是說,西方借此用以區別于自身的一種設定。
今天的亞洲地理版圖是以蘇伊士運河劃分亞洲和非洲的邊界,以烏拉爾山脈劃分亞洲和歐洲的邊界,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交界為其東南邊界。這種亞洲地理概念也是伴隨近代歐洲殖民主義的地理不斷擴張才逐漸形成的。從文化史的角度看,“亞洲”概念與民族關系模糊及專制主義的基本特征相關,并通過與歐洲國家之間的對比才建立起來的。
因此,亞洲既是一個在政治體制、經濟體制和文化傳統上截然不同于歐洲大陸,又是一個內部高度分化的區域。關于“亞洲”概念在亞洲國家中的具體提出和運用,我們可以追溯到1885年3月16日日本近代變革先驅福澤諭吉在《世事新報》上發表的“脫亞論”,即“脫亞入歐”的觀點,其主要意旨在于擺脫以中國為代表的儒教主義的封建關系,以圖將日本建設成歐洲式的民族國家。
實際上,福澤諭吉的思想深受1884年朝鮮李氏王朝發生“甲申政變”的影響,由于李朝的“開化派”試圖采納西方近代國家、社會、權力的思想模式進行改革,最終僅持續了三天便告失敗。福澤諭吉洞察了這種政治變化,并非常認同開化派的進步思想,但這個事件給他很大震動——對這種改革失敗進行反思,并認為朝鮮李氏王朝改革失敗的原因就在于深受儒教文化的長期掌控。①于是,他明確提出了脫亞的主張,這就意味著日本要走向改革之路,必須先要擺脫儒教文化的影響,才能建構具有歐洲式的“自由”、“人權”、“國權”、“文明”和“獨立精神”的民族國家類型,其目的就是日本不再依賴在亞洲內部以中國為中心的儒教文化。
1885年前后,整個日本的政治界和思想界已彌漫著求變的思潮。初任總理大臣的伊藤博文就極力推行歐化政策,盡管也有以西村茂樹為代表在《日本道德論》一書中提倡儒學道德復興的主張,但文部大臣森有禮支持伊藤博文的主張,他明確提出:“在現代提倡孔孟是迂腐的。”他的理念代表了一種價值取向,脫亞實質上就是脫儒。因此,“脫亞”表達的改革思想,確立了日本近代國家的自我意識。與此同時,“脫亞入歐”成為了日本民族主義興起的重要口號,并被日本的極右翼勢力和日本的殖民主義政策所利用,也就是將“入歐”的民族國家邏輯與“入亞”的帝國主義邏輯之間相混淆。
在具體行動上,他們則轉變成了“入亞反歐”,最終借“解放亞洲”之名發動了對中國、朝鮮和東南亞地區的侵略和殖民統治。實質上,日本以“亞洲主義”彰顯了“日本主義”。“亞洲”概念與社會主義運動有關,它本身就具有革命性的內涵。20世紀上半葉,社會主義革命運動在世界范圍內蓬勃發展,在反抗殖民主義和反對資本主義擴張的過程中,社會主義明確提出了亞洲概念。如果回顧近現代歷史,可以發現19世紀源于歐洲的社會主義運動實際上是一個國際主義運動,它在思想和主張上批判民族主義。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社會主義者們面臨著一個非常嚴峻的問題——各國無產階級和工人階級能不能支持本國政府去打擊另外一個帝國主義國家,以及工人階級在民族沖突中所處于怎樣的位置。在這個特殊的社會背景下,列寧提出了民族自決權的理論。列寧關于民族自決權的觀點主要針對了像俄羅斯這樣的大國內部的革命者和知識分子如何對待弱小國民族自決的要求——俄羅斯人怎樣對待烏克蘭的獨立和波蘭的獨立的問題。因為列寧將社會主義運動既視為是一個民族主義運動,又看成是一個國際主義的革命運動,他進而又從倫理的高度提出了要求,認為大國的革命者在這個關頭不能站在大國沙文主義的立場和態度上支持本國政府,而應支持小國的民族獨立運動。
他的這種批評觀轉化成了民族自決權的思想。在這樣的背景下,列寧開始關注亞洲,并在俄國革命前夕細察了1911年在中國爆發的“辛亥革命”,他在這個歷史時刻發表了《亞洲的覺醒》和《落后的歐洲和先進的亞洲》,他在盛贊“中國的政治生活沸騰起來了,社會運動和民主主義高潮正在洶涌澎湃地發展”②的同時,又鮮明地批判了“技術十分發達、文化豐富、憲法完備、文明先進的歐洲”正在資產階級的領導下“支持一切落后的、垂死的、中世紀的東西”。
③依照他的觀點,資本主義進入帝國主義階段,世界各地的被壓迫民族的社會斗爭就被組織到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范疇之中。在這個意義上,他對為何亞洲是先進的和歐洲是落后的做了界定,亞洲被納入世界范圍去看待,它代表了在帝國主義階段的世界革命的斗爭。1924年11月28日中國近代革命家孫中山在日本神戶的一個商會上發表了題為《大亞洲主義》④的演講,在這一著名的演講中,他比較含混地區分了兩個不同的亞洲概念:一個是“沒有完全獨立的國家”和作為“最古老文化的發祥地”的亞洲;
一個是即將復興的亞洲。顯然,從這種區分來看,前者是指亞洲尚未建立新的民族國家的政治結構,這是被否定的亞洲;后者則是指復興的亞洲,它是以日本作為起點,因為日本廢除了與西方的不平等條約,成為了第一個亞洲的獨立民族國家。換言之,亞洲復興的起點不僅僅指的是日本,而是指的是民族國家。當孫中山看到了日俄戰爭以日本的勝利而宣告結束時,他歡欣鼓舞地指出:“日本人戰勝俄國人,是亞洲民族幾百年來第一次戰勝歐洲人”。⑤他還以帶有種族主義的語言區分白種人歐洲人和黃種亞洲人的民族主義的概念。
非常有意思的是,孫中山有意地把作為白人的俄國從歐洲分離,因為在他看來俄國人主張的王道符合亞洲文化傳統。與列寧的論述相比,孫中山更把視角深入到亞洲內部國家間的文化關系,他發現亞洲內部的國家交往關系是依賴于封建的朝貢關系來維系近代政治和近代經濟的。
他采用中國的“王道”和“霸道”的概念,強調一方面亞洲復興的前提是建立民族國家,另一方面建立民族國家又正體現了歐洲殖民主義擴張的一種形式——霸道文化。對于王道的敘述,他提到了封建的朝貢,具體以尼泊爾和中國的關系做了充分的例證說明⑥。孫中山提倡的王道試圖將其融入到列寧主張的世界主義文化中去。所以,這種論述在某種程度上超越了亞洲的觀念。這種思想也反映了當時的知識分子對俄國革命抱有非常理想化的理解,他在“大亞洲主義”中說:“現在歐洲有一個新國家,這個國家是歐洲全部白人所排斥的,歐洲人都視它為毒蛇猛獸,不是人類,不敢和它相近,我們亞洲也有許多人都是這一樣的眼光。
這個國家是誰呢?就是俄國。俄國現在要和歐洲的白人分家,他為什么要這樣做呢?就是因為他主張王道,不主張霸道…”⑦他以種族主義的觀念把俄國人定義為歐洲人,又從現實的壓迫關系將俄國革命運動則看成是亞洲的組成部分,構成了“大亞洲主義”的同盟。在這個意義上,無論是“脫亞入歐”,還是“大亞洲主義”,亞洲仍是超越民族國家的范疇,每次提出的新議題都與民族國家和民族自決密切聯系。倘若對這兩種思想加以比較,我們就會發現,福澤諭吉所想象的亞洲和東亞具有高度的文化同質化的范疇,都是儒教背景下建立起來的文明,而孫中山提出的大亞洲主義不是這樣的,他特別強調了亞洲是所有宗教的發源地。
所以,他甚至把俄羅斯和土耳其歸入亞洲范疇,以民族國家解決內部的差異性,但并沒有形成內部文化上完全一致的亞洲觀念。也就是說,孫中山理想中的亞洲景象應建立內在統一性,這種統一性并不是類似于儒教式的單一文化,而是一種平等的政治文化,能夠包容了不同宗教、信仰、民族和社會的形態。
他的“大亞洲主義”以“王道文化”反對“霸道文化”,以恢復亞洲的民族地位和尋求一種平等解放的文化。基于這些論述,“亞洲”既是一個實體的地理概念,又是一個與歷史相連而又存在差異的想象空間。因此,亞洲不是一個絕對的隔絕的總合體,亞洲概念總是處于一種帶有模糊的游離狀態——具有曖昧性和內在矛盾性的特征。
亞洲概念交織了二重性,亞洲既包含了殖民主義和非殖民主義的內涵,又蘊涵了保守和革命的特征,更具有民族主義和國際主義的意義。可以說,它是歐洲人提出的概念,既界定了亞洲,也塑造了歐洲人的自我理解。它與民族自決和帝國的視野相聯系。今天,全球化給亞洲帶來的影響,不僅僅體現在快速發展的亞洲經濟,而且還體現在重塑亞洲的文化認同。尤其是在建構亞洲認同的過程中,亞洲正在由以經濟為中心的時代逐漸向以文化為重心的時代轉變。
⑧與“冷戰”后亞洲地區緊張的國家關系相比,亞洲當代藝術則超越了各種各樣的界限呈現出生機蓬勃的活躍景象,這種新的文化現象都是經過許多策展人、評論家、藝術家長期共同努力和奮斗的結果。如果考察這種現象背后的動因,它在本質上依然來自亞洲外部的作用和影響。在現代藝術史中,20世紀70年代,歐洲和美國出現了對以西方中心主導的20世紀藝術潮流的一元中心的質疑,但這股思潮并沒有在廣泛的領域中得到展開,甚至沒有波及或影響到整個東方,盡管日本是個例外,但絕大多數的亞洲國家與西方之間是隔絕的。
然而,1989年在巴黎舉辦的“大地魔術師”展是一個重要轉折點,它第一次向西方文化中心介紹了非西方國家的藝術,這不僅暗示了西方中心文化之外存在著未被認識和未被發現的共時性的現代藝術觀念,而且也預言了多元主義文化時代的降臨。與此同時,它無疑在藝術實踐上動搖了西方中心主義的價值體系,從而導致了以西方中心的視點向多元文化視點的轉移。這種非中心的藝術實踐無疑預示了“冷戰”之后國際藝術發展的新走向——嚴格劃分的“中心”與“邊緣”的文化版圖逐漸被溶解,并帶動了非西方藝術的多元藝術的崛起。
尤其是90年代以來,隨著全球化的加劇,非西方國家/地區的社會政治體制變化和經濟迅速發展不斷強化了“他者”的文化自覺意識。盡管東方和西方都面臨作為自身文化建設的戰略選擇,彼此都采用了多元文化的國際展覽的形式,以實現相互間的對話與交流。于是,新的展覽模式以驚人的速度在世界范圍內不斷蔓延。亞洲也積極參與和回應了這種文化變化,吸收或引進國際流行的展覽機制來建構自身文化體系,也提高了自我意識和文化身份的伸張,重新審視自身文化的價值。
亞洲各國從內部改善藝術環境,建立起了緊密的交流關系。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多元主義文化的背景下,亞洲策展人、評論家和藝術家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機遇和文化使命,他們借“非中心”、“身份”、“跨邊界”的概念尋找與西方相“對比”、“差異”后的潛在可能性,力圖把被動的選擇扭轉成主動的自決。他們還在藝術實踐上超越了東西方之間的對立概念,盡可能擺脫作為西方想象的“異國情調”,以表明亞洲文化身份的自覺意識。
一些中國、韓國、日本、印度、泰國、新加坡等國的評論家、藝術家、策展人充分發揮了各自的才智和能量,超越了現實的種種局限,提升了亞洲藝術在國際上的位置和影響。值得注意的是,亞洲的策展人、評論家和藝術家在方法論和實踐上給予了這樣的暗示,亞洲當代藝術面對歐美為中心的藝術價值體系,怎樣擺脫西方系統的模式而確立一個新的亞洲藝術形象?事實上,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盡管層出不窮的亞洲當代藝術活動在亞洲或西方引起了廣泛關注,并獲得了比較廣泛的學術影響。
亞洲藝術展在西方展示并得到認識,逐漸發展和建立起了亞洲的“雙年展”、“三年展”機制。雖然采用“移植”西方模式有一定必要的參考性,但這絕不意味著要生搬硬套,而是充分體現一種獨立思想和自覺意識,更重要的是在展覽組織和交流中探討不同藝術間交流和影響的相通性,這才是實現跨文化交流的關鍵性所在。事實上,如果從現代藝術史角度看,可以發現藝術“移植”不僅存在亞洲藝術之中,而且也存在于西方藝術之中。
二戰之后美國重要的藝術家賈斯柏·瓊斯、約翰·凱奇、莫爾斯·庫寧漢、羅伯特·勞生柏等人就曾深受日本禪學大師鈴木大拙的影響,禪宗思想曾在美國著名的黑山藝術學院盛行,當時該學院聚集的凱奇和勞生柏等藝術家都認識到東方與西方的思維差異,由于禪宗包含了宇宙是如何形成及如何解讀時間和空間等東方觀念,他們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既研讀又實踐。
特別是凱奇就直接把禪宗觀念具體應用到他自己的行為表演中,涉及感性音樂的復興和創新的可能性。從現代藝術史的經驗到今天全球化的現實來考察,我們根本不可能尋找一個純粹和本質的亞洲,亞洲并不是一個隔絕的停滯地帶,而是一個交流的動感區域——吸收、融合、影響和發展。那么,策展人是否能從亞洲內部出發掘出一條新路呢?他們是否能從亞洲藝術與亞洲社會、政治和文化的聯系中找到亞洲藝術的本質?從東亞的日本、韓國、中國的發展來看,它們在總體上表現出一種儒教資本主義的文化特征,這與三國的現代化進程有關:日本早在“明治維新”就確立了君主立憲制;
韓國是在80年代中后期走上了民主化;中國在80年代初推行的“改革開放”政策具有“后社會主義”的特征。當然,這種文化表征正反映三國間的共同性和差異性。在亞洲政治經濟條件下,談論亞洲立場是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在國際藝壇中亞洲當代藝術的民族性與“他者”如何建構,以及它們之間的關系。它們又直接引出了最本質的問題:什么是亞洲?
亞洲在哪里?亞洲人怎樣認識自身?因此,這些復雜的問題似乎被亞洲藝術家在實踐中所證明。面對現代化進程中意識形態的差異和重重困難現實,無論是歷史傳統,還是現代國家的關系,亞洲還沒有建立起歐盟模式的超級民族國家的先決條件,因為它的內部包含了各種不同的文化傳統、習俗、宗教和政治因素,像佛教、猶太教、伊斯蘭教、基督教、印度教、道教、錫克教和儒教等都起源于亞洲,用任何單一的文化來概括亞洲都是難以有說服力的。
與歐美相比,亞洲更具多元文化的特征。它的差異性基本源于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歷史發展延續的結果;一方面是殖民主義、地區戰爭和冷戰等遺留的影響。盡管全球化時代早已降臨,但亞洲在殖民主義時代和“冷戰”時期遺留的矛盾和沖突仍在延續,并在新的國際環境條件下衍生出新的問題,諸如“巴勒斯坦與以色列的沖突”、“伊朗核問題”、“朝鮮核問題”、“印度與巴基斯坦之間克什米爾領土糾紛”、“中國、韓國與日本間關于歷史問題爭論”、“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等。雖然這些各種各樣的復雜現實性阻礙或限制亞洲藝術的交流,但藝術作為一種烏托邦理想和一種自由的表現形式,它往往超越國家疆界和意識形態的約束,以寬容的態度去吸收和融合別的文化。
亞洲藝術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建構和發展的。實際上,“亞洲性”指的是在藝術創作中的亞洲主體性,是一種銘刻了文化身份的表現形式,是一種建立在語言、傳統、宗教基礎上的差異性的文化話語。在這個意義上,超越“亞洲性”的藝術理想應該是超越民族國家的邊界,重新建構一個想象的文化空間,它的基本前提就是必須確立兩個明確的目標,即對內消解國家“中心”,對外則抵抗西方文化的“話語霸權”,對亞洲藝術實踐者而言,這既是一種文化策略,又是一種文化使命。21世紀的亞洲在現代民族國家的發展過程中,它建構了由語言、信仰、歷史組成的想象空間,并鮮明地區分了自我與他者的認同基礎。
在亞洲區域,只有尊重不同的語言、不同的價值和不同的思維方法作為共存的前提條件,才能實現多樣文化的生長,才能使文明價值得以延伸和發展,才能看到豐富而生動的亞洲文化圖景。實際上,亞洲國家的現代性不是單一的,而是包含了各種各樣的模式。這恰恰證明了亞洲想象的文化空間所蘊涵的復雜性和多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