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過七旬的克里斯托和讓娜-克勞德,完成的作品只有19件,但每一件都舉世聞名。這些作品不僅實現難度極大,而且造價高昂得離譜。他們將河流覆蓋,將國會大廈和海岸包裹起來。他們從不接受贊助或委托,也拒絕為作品闡釋任何深刻含義,堅持聲稱:那只關乎歡樂與美感。上世紀的60年代初期,大地藝術在西方孕育而生,不到10年就蔚然成風。LandArt、EarthArt或Earthworks有時也被翻譯成“地景”藝術,透露出作品以土地、山谷、公共建筑等自然景觀為材料的創作特性。從1962年第一個戶外大型作品“鐵幕”開始,克里斯托和讓娜-克勞德創作了一系列大地藝術作品,包括1971-1995年的“包裹德國柏林議會大廈”、1984-1991年在日、美兩國的“傘”、1975-1985年在巴黎的“包裹新橋”、1980-1983年在邁阿密的“被環繞的群島”、1972-1976年在加利福尼亞的“飛奔的柵籬”等。

這些極具顛覆性的項目,使這對夫婦藝術家成為20世紀后半葉最大膽、最有創造力的大地藝術家。40多年來,他們一直自費上千萬美元,耗時幾年甚至二十幾年等待許可證,去實現這些曇花一現的超大型項目。在商業社會的價值觀里,這簡直荒謬透頂,但兩位藝術家卻十分自豪地表示:“我們從不接受任何贊助或委任,這是我們藝術創作的基本底線。我們自己付錢,自己銷售,自己辦理一切委托事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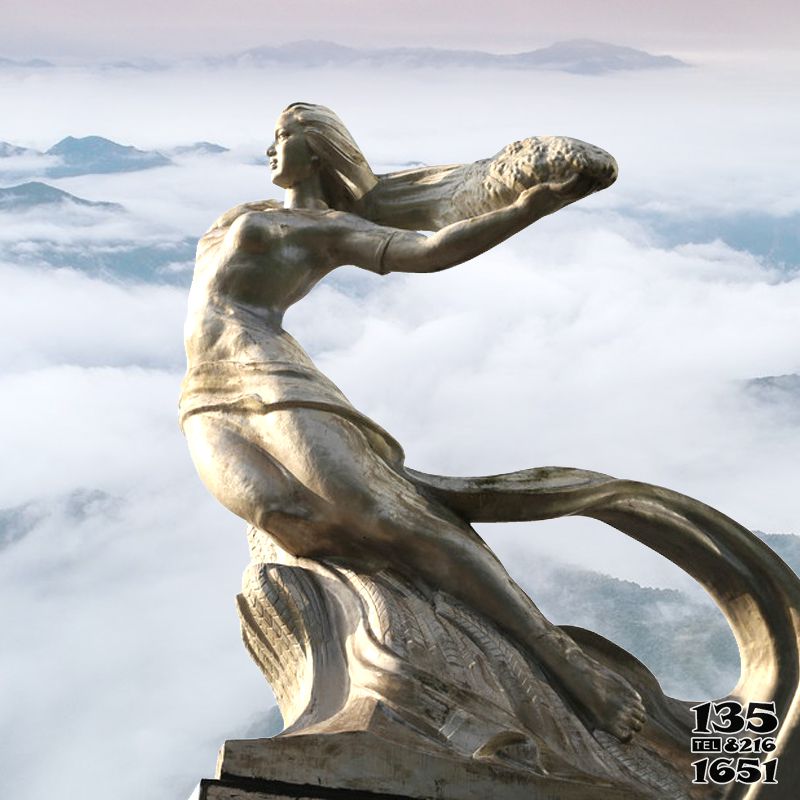
”如果還要加個“最”,那克里斯托和讓娜-克勞德夫婦一定是“最自由”的藝術家。9月8日-10月7日,上海樸麗淑畫廊推出的“馬斯塔巴金字塔之準備—阿拉伯聯合酋長國項目”,是克里斯托和讓娜-克勞德在中國的首個展覽。雖然創意成型于1977年,但“馬斯塔巴金字塔”目前仍僅存在于藝術家的草圖上。不過在克里斯托和讓娜.克勞德的“語言系統”中,“未實現”應被稱為“正在進行中”。“馬斯塔巴”在阿拉伯語中是“長椅”的意思,是金字塔的前身。

“馬斯塔巴金字塔”將被建在阿布扎比,四壁中兩邊是斜的,兩邊是垂直的,頂部則是平的,像一個被削為平頂的金字塔。“馬斯塔巴金字塔”將由大約410萬個橫向擺放的鋼質油桶堆砌而成,高150米,寬225米,長300米,完成以后,將比埃及的吉薩金字塔更大。油桶將被漆成不同的鮮亮顏色,顏色的選擇和位置將由藝術家決定,因為一天中的時段和光照量不盡相同,油桶的顏色將起到馬賽克一般的效果,造成一種不斷變幻的視覺體驗。按照夫婦倆的意圖,這件作品將十分特殊。

以往的作品在展出兩周后,其材料將被回收利用,而“馬斯塔巴金字塔”建成后將不再拆除。此次展覽包括了一系列草圖和拼貼,展出這些作品,是為了讓人們知道,經過了31年的漫長申請,他們依然還在等待這個項目實現的可能。雖然“馬斯塔巴金字塔”的實現尚無著落,但他們另一個項目—創意于1985年的“覆蓋河流”,正在卓有成效地進行中。他們將用9400米透明反光布料,把穿過科羅拉多州的阿肯色河覆蓋起來。項目預計將在2012年夏季完成。克里斯托和讓娜-克勞德出生于1935年6月13日的同一個小時里,說起來,這對“同命相連”的夫婦,身世和相識的過程都頗為傳奇。

克里斯托是保加利亞一個德國工業家的后代,他的祖父開創并經營了東歐第一個滾珠軸承工廠。克里斯托從小便顯露出藝術天分,青年時還曾沉迷于莎劇。由于不滿扼殺藝術生命的政治環境,畢業于索菲亞藝術學院的克里斯托,賄賂了一名鐵路官員,跳上一輛運輸藥物的火車,取道捷克斯洛伐克流亡至維也納,后又輾轉前往日內瓦,最后移居巴黎。一路顛沛流離,克里斯托丟失了他的護照,在1973年成為美國公民前,克里斯托做了17年沒有身份的人。
克里斯托在巴黎的生活極為艱難,除了要克服語言障礙,他還不得不以畫肖像畫謀生。后來,他將當時的畫畫生涯比喻成賣淫。1958年10月,他被邀請去為雅克.德.高依本將軍的夫人畫肖像,隨后與夫人的女兒讓娜墜入愛河。讓娜出生在卡薩布蘭卡,她的親生父親是一名法國陸軍少校。
與克里斯托相遇時,她正值新婚,然而,克里斯托的出現讓新婚夫婦的關系僅維持了21天。采訪中,聊到他們的相遇,讓娜的聲音頓時變得少女般輕柔起來。當被問及克里斯托身上怎樣的特質吸引了她時,讓娜連聲問丈夫:“克里斯托,我能說嗎?”獲得準許后,她才笑著吐露了秘密:“那跟藝術完全沒有關系,完全是出于性吸引力。”一年后,他們的兒子、日后出版了5本詩集的著名詩人西里爾.克里斯托誕生。由于出生門第嚴重不“登對”,兩位年輕人的結合受到家人一致反對,但他們全然不顧,一頭扎進藝術創作中去了。當時,克里斯托的“捆扎藝術”已積累了不少作品。
他通常以帆布、塑料布、繩索為材料,包裹桌子、椅子、自行車以及他自己的繪畫作品,甚至捆扎人體本身。評論認為,他的小型包裹藝術作品的美感,來自纖維織物拉扯牽伸之間所產生的張力,圍堵、隱藏、插入,賦予作品模棱兩可、曖昧含混的意象。沿著“捆扎之路”,克里斯托夫婦在1962年創作了第一個戶外大型作品“鐵幕”—用油桶將塞納河邊一條名為威斯康辛的小街堵塞了數小時。
前一年,柏林墻剛剛建起,而作為“反柏林墻”宣言,該項目一下子使他們名震法國。1964年,克里斯托夫婦移居美國,將目光投向包裹貝納美術館、MOMA、芝加哥當代美術館等大型建筑。迄今為止,這對七旬老人“實現”的作品僅有19件—少得讓人難以置信,但每一件都舉世聞名。這些作品不僅實現難度極大,而且造價高昂得離譜。1995年6月包裹德國柏林國會大廈,是最好的例子。由于柏林國會大廈極為敏感的政治性,藝術家堅持不懈達24年之久才得以完成這一驚世之作。該方案在1977年、1981年和1987年三次被官方否決。
24年中,克里斯托夫婦不厭其煩地修改作品方案,鍥而不舍地游說包括德國三大政黨的190位議員在內的662位代表。最終,德國國會在1995年以292票對223票通過了該項目。藝術家用超過10萬平方米鍍鋁防火聚丙烯面料以及1.5萬米繩索,完成了該作品。克里斯托夫婦為實現這一項目,耗資高達1300萬美元,并且全部自費。這秉承了他們一貫的原則:不接受任何形式的贊助,包括藝術基金會的資助以及義工的加入,全部費用靠他們出售早年的小型包裹作品以及作品準備階段的草圖、習作、拼貼、縮小模型、版畫等來籌集。
被包裹的柏林國會大廈展出時間僅兩周,但吸引了多達500萬名游客,成為戰后柏林最受矚目的藝術品。然而,這些旅游收入卻分文不進創作者的腰包。除了不直接通過作品賺取收入,即便是關于他們的出版物的版稅,夫婦倆也不愿沾手。雖然已是祖父、祖母,但在采訪中,讓娜告訴記者,他們仍住在紐約一幢沒有電梯的公寓樓5樓。他們沒有所謂的工作室,就在家里工作。他們在那里住了45年之久,每天就靠雙腿爬樓梯。他們甚至沒有車,雇用的鐘點工每周來家里收拾兩個小時,平時他們自己打掃衛生。
要是坐享其成,這對夫婦的財產早已超過數億美元,讓娜說:“你知道這些錢能買多少部電梯嗎?但這是我們選擇的生活。我們是自己的老板。”采訪多次因克里斯托跑開去接電話而中斷,讓娜解釋說,由于他們需要親自接洽來自各大洲美術館、畫廊、媒體以及各相關單位的繁雜事務,因而家里的電話系統管理也頗為復雜。除了用多門電話區分不同對象的來電外,他們還會根據時差來安排處理各地事務的時間。
讓娜對各個時區的時差幾乎倒背如流,他們指定給記者的采訪時間,就是因為此時的歐洲已到深夜,他們可以集中面對來自亞洲的事務。兩個70多歲的老人,依然思路清晰、頭腦敏捷。采訪過程中,他們明確表示不愿浪費時間回答別人問過的問題,讓記者去查閱相關的出版物。
對于提問中出現的疏漏或誤解,他們會非常嚴厲地加以指出,有時候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對細節精確程度的要求,讓他們更像科學家,而不是一般人印象中大大咧咧的藝術家。采訪之后,只過了三四天,記者就意外地收到了一個UPS的大箱子,采訪中提及的“相關出版物”和DVD已從美國寄到,足見他們的縝密和高效。
把大樓、橋梁用布包裹起來,在峽谷中橫跨兩座山掛起大簾子,把上萬個彩色油桶整齊地摞成一堵墻…這些很像是小孩子的“空想”,也有不少人覺得是胡鬧,但夫婦倆偏偏愿意付出巨大的心血及代價,來實現這些僅僅存在兩周的作品。
“對我來說,一切都是冒險!”克里斯托說,“我的創作幾乎總是瀕于不可能的邊緣,但這正是令人興奮之處。我面前的道路總是顯得十分狹窄,每一件作品都是一個充滿風險的艱難過程。”但他們絲毫也不認為自己“烏托邦”。他們的藝術創作十分簡單平實,技術上都很容易實現,從不異想天開,風險和難度更多在于是否能得到所在國家或地區的許可證。
“目前為止,共有19個實現的項目,還有兩個正在進行中;而我們放棄的計劃卻多達37個,全部是因為得不到許可。”讓娜有些遺憾地說。克里斯托夫婦的“大地藝術”中最為人熟知的,是把橋梁、公共建筑物、海岸線等包裹起來,形成讓人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景景觀。在完成了貝納美術館等數個大型建筑物包裹項目之后,1969年,他們極為大膽地用尼龍布,把悉尼附近的整個海岸都包裹了起來。這個名為“包裹海岸,1962-1969”的作品,面積達9萬多平方米,動用了超過130名工作人員,耗時達1.7萬個小時。
原先陡峭嶙峋的懸崖絕壁從人們的視線中消失了,變成了一片陌生的人造世界,銀白色的織物綿延著,長達16公里;整個海岸從堅硬變為柔軟,呈現出一片不可知的朦朧。這個作品首次使他們獲得了國際性的關注。此后,“包裹人行道,1977-1978”將堪薩斯城魯斯公園中的人行道包裹成了黃色;“新橋,1975-1984”又用4萬平方米布料將這座塞納河上最古老的橋梁包裹起來;包裹德國柏林國會大廈以及在瑞士巴塞爾的公園里包裹178顆樹木,則讓這對夫婦標志性的藝術風格名揚天下。
藝術評論家大衛.布爾登精辟地把他們的“包裹”藝術概括為“包得越嚴,展露得越多”。對此,克里斯托引用羅丹的雕塑來解釋:“羅丹曾做過許多巴爾扎克的雕像,第一個版本中的巴爾扎克渾身赤裸、大肚子、細腿?有一天,羅丹把自己的披肩往雕塑上一放,遮蓋住巴爾扎克巨大的身軀,從而誕生了今天矗立在MOMA花園內的杰作:雕像被塑成身披睡袍的姿態,身體的細節被布料遮蓋了,只露出昂揚向前、傲視一切的臉部。”這與布料之于新橋或柏林國會大廈的意義如出一轍。
流動的、帶著反光的布料在空氣中隨風飄蕩,建筑上的窗戶、小雕飾及其他裝飾全被忽略了,只有最基本、最抽象的形狀被強調出來。“那些瑣碎和平庸的東西都不見了,只剩下建筑最本質的比例被呈現出來。”“峽谷垂簾,1970-1972”是克里斯托夫婦另一件代表作,將重達3.6噸的橘黃色尼龍布,垂掛在美國科羅拉多來福峽谷相距1200英尺的兩個斜坡之間。這個耗資40萬美元的作品,卻因為即將到來的暴風雨,而在尼龍布掛上去28小時后,不得不緊急取下。
“飛奔的柵籬,1973-1976”則是在美國加利福尼亞的馬林和索諾馬縣,用白色尼龍布制成高5.5米、長40公里的柵籬。“被環繞的群島,1980-1983”用超過60萬平方米的粉紅色布料,覆蓋佛羅里達的11座島嶼,從高空俯瞰,如同漂浮在碧海上的朵朵睡蓮;
耗資2600萬美元的“傘,1985-1991”,分別在日本東京北面80英里的山坡和美國南加州的田野上,插上1340把藍色和1760把黃色的傘,這些高6米、直徑8.66米的巨傘在山坡田野上綿延達12英里,蔚為壯觀,在日本和美國兩地引起了極大的轟動。克里斯托夫婦的作品在視覺上極為震撼,也有人從中看出種種人與自然的深層關系。對此,夫婦倆一再拒絕為作品闡釋任何深刻含義,堅持出于純粹的審美考慮,只是想把世界變得更美麗。
即便你問得再多,他們給出的解釋還是會讓你云里霧里。在采訪中,克里斯托夫婦極為嚴厲地批判“他們的創作就等于包裹”的觀點。讓娜指出,他們最后一次提出“外部包裹”的創意,其實已是30年前。雖然他們花了24年,才在90年代中期獲得包裹柏林國會大廈的許可,但他們的創作在70年代已經開始轉型。他們依然保留布料為創作材料,但呈現手法已經多樣化。“用布料來創作的歷史源遠流長,埃及、希臘、中國的古代藝術品中都很多見,并無特殊意義。”克里斯托說。
盡管常被認為是“觀念藝術家”,克里斯托夫婦并不認為自己的作品是“觀念作品”,因為其作品之目的,就是實現并建造實物,而非僅僅停留于紙上;他們更樂意宣稱自己的作品“關乎歡樂與美感”,而不喜歡被貼上某種流派的標簽。夫婦倆表示:我們不是酒瓶,理論上不希望別人為藝術家貼任何標簽,但如果一定要貼,可以稱他們為環境藝術家,因為城市和鄉村環境都是他們的創作資源。出自克里斯托夫婦之手的“浩大工程”,需要投入的人力物力極為龐大,更要牽涉到政治、經濟、法律、外交、消防、保險、交通、安全等等方面,出于得到各層面機構許可的需要,他們的顧問團常常包括工程師、律師團、環境工作者等,復雜程度足以讓其他藝術家瞠目結舌。
你會發現,他們所有的作品名字后面,都標明兩個跨越多年的年份,但那并非作品實體的存在期限。實際上,這些投入巨大的作品,平均壽命才半個月,然后一切都會撤去,建筑或自然界都不留任何痕跡地恢復原貌,僅剩圖片供人緬懷。
克里斯托說:“除非親身經歷作品的空間,走在這些隨風搖曳的布料旁感受它們的運動,否則你根本無從欣賞或想象作品的美。”相比長達十數載的醞釀準備期,這些作品供人們欣賞的時間只有短短幾周甚至幾小時,實在過于“短命”。
但克里斯托夫婦并不因此感到惋惜,他們認為,與政府等相關機構交涉的過程也是作品生命的一部分,因而他們將作品開始構思的年份標在前面,而將作品最終完成的年份標在后面,以表明創作一件作品的整個時間跨度。讓娜把他們經年累月苦苦經營的作品比作他們的孩子,而長年的準備期就是女人的妊娠期,“如果沒有媽媽在妊娠期的苦苦煎熬,就不可能有孩子的誕生”。
克里斯托常說:“我們的作品都有關自由,自由的敵人是擁有,因此消失要比存在更永久。”為了這份自由,他們拒絕利益集團對作品的干涉,作品展出期間帶來的旅游收入,他們也分文不取,讓娜說:“哪個父母能利用自己的孩子來賺錢?顯然不行。
”夫婦倆最近完成的作品,是“門”。在苦等了數屆紐約市長的選舉后,終于如愿以償,2005年,新上任的市長布隆伯格不顧生態主義者對其影響鳥類生活等的質疑,批準實施這一項目。“門”蜿蜒伸展于中央公園的走道上,設有鋼座,以每隔12英尺的距離,豎立起7503道由聚乙烯制成的門,每道門都懸掛著一塊橙紅色織布作為門簾;門高16英尺,寬6-18英尺不等,綿延37公里,穿越整個中央公園;從第59街到第110街,那些簾子隨風飄蕩,如同一條“橙色的河流”。雖然這座花費2100萬美元建造的紐約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藝術品僅存在了16天,但在布隆伯格看來,它能與羅馬梵蒂岡的西斯廷教堂、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曲》以及《飄》相媲美,是一件“永恒的杰作”。
流亡生涯使他們決心成為純粹“自由”的藝術家,冷戰、東西方關系是他們藝術追求的源泉,他們的作品是如此短暫,并將永遠消失,沒人可以占有它,沒人可以購買它,沒人可以控制它,就像我們自己的生命那樣,無法重復。B:克里斯托,你早期的流亡生涯,以及到巴黎后以畫肖像畫為生的經歷,對日后的藝術觀有何影響?J:稍等,這里有個誤解。當克里斯托在巴黎依靠畫畫求生存、付房租時,他已經同時在創作自己的作品了,只是那時這些作品無人問津。
當時,他在畫作上署的是原先的姓氏Javacheff,而在自己的作品上署名Christo,以求區別。除了畫畫,他還洗車、在餐館洗盤子,所以,當時他同時要干四件事。B:問題是,是否因為流亡生涯,讓你決心成為一名純粹“自由”的藝術家,無需依靠任何藝術組織或贊助機構。
C:我生于保加利亞,一個東歐的共產主義國家。1957年,我21歲,便逃去了西方,因為我很渴望能做一些真正“自由”的藝術。當時正值冷戰,所有的藝術家都應該做“共產主義”的事,如果不做,就會被認為是“叛國”。J:補充說一句,保加利亞當時是被蘇聯的鐵幕政策籠罩的國家之一。
C:1956年10月,匈牙利事件在布達佩斯爆發,那時局勢混亂,官方無力控制,不僅僅是我,很多人都偷偷跑去了西方。我是途經捷克斯洛伐克,跑去了維也納。要不是冷戰,我應該一直待在保加利亞,所以冷戰、東西方關系一直是我很重要的興趣所在,這成了我藝術追求的源泉。J:對,1962年,用一些油桶堵住巴黎的威斯康辛街,持續了幾個小時,象征“柏林墻”的抽象版本。B:油桶是你們作品中反復出現的材料,馬斯塔巴金字塔以及室內作品《墻》都用到了彩色的油桶,有什么特殊意義嗎?
C:我在早期的小型包裹作品中就開始使用油桶,那是當時最容易找到、最便宜而且不易碎的大容器。當時我十分貧窮,住在巴黎一個非常狹小的工作室,每天撿破舊的臟油桶回家創作,把它們洗干凈并包裹起來。那是我在包裹桌椅之前最早期的作品,那個時期的作品后來大都被搬到讓娜家的地下室保存起來,但油桶很多被丟棄了。J:實際上,油桶啟發了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租借”隨處可見的物品來創作。B:你們包裹了許多大型建筑物,比如德國柏林國會大廈,這種風格是你們首創的嗎?
這樣的創意在上世紀70年代應該非常前衛。J:我不認為是我們首創,我們只是擅用布料。自古以來,布料在藝術創作中就占有一席之地,是十分傳統的元素,你們古代中國的雕塑,也有許多只露出一張臉、兩只手,其余的部分被衣物遮蓋起來。C:我們做的與此完全一致。
就以柏林國會大廈為例,這是座非常典型的維多利亞建筑,有許多細節和裝飾,我們用可以隨著日光變化色彩、隨風飄蕩的布料去包裹它,強調了建筑本身;對新橋來說,我們的作品突出了橋本身是城市中的功能雕塑;“傘”刻畫的則是鄉村的環境。我們的作品不可以籠統地解釋,每一件的意義都不盡相同。C:1961年,我開始策劃“租借”并包裹一個公共建筑,這座房子不能是市政廳,不能是公司總部或私人官邸,而應該是屬于國家的。
唯一屬于國家的樓房就是國會大廈。1971年,碰巧我一個美國朋友到柏林旅游,給我寄了張柏林國會大廈的明信片。柏林是東西方的相遇處,這個地方具有足夠的戲劇性和空間感,而柏林國會大廈則是美、蘇、英、法、兩德的管轄的交集,是最適合的選擇。J:可惜的是,我們并沒有在1989年前完成它,否則它將會為冷戰史記上一筆。C:不過,這座建筑仍然記載著歷史的變遷,這也是包裹它仍然令人興奮的原因。過去蘇聯政府一直擔心,這座建筑將成為兩德統一的源頭,所以嚴加看管,使它成為蒂爾加藤區最孤獨的建筑。如今,德國的首都又從波恩遷回柏林,德國人又在這里制定法律。
J:事實上,過去的那些事,讓1989年后與政府部門交涉的我們仍然不安。冷戰時期,黑和白、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一目了然,冷戰之后,好人壞人無從分辨。J:有時候是先定地點,比如紐約中央公園的“門”。我們在紐約住了30年,想在曼哈頓創作作品。最早,我們計劃利用摩天大樓,后來我們突然發現,其實曼哈頓是世界上行人最多的地方,于是我們聯想到了在公園散步的人們,“門”應運而生。
也有時,我們先有了一個主意,然后去找地方。為了找到“覆蓋河流”中的那條河,我們開車行駛了2.5萬公里,在落基山脈勘察了89條河流,鎖定了其中6條,認為有可能實現,最后再通過科學測量以及精確計算,認定阿肯色州境內的那條河流最為合適。C:我們僅僅是藝術家,但我們的團隊里會有工程師等各種各樣的技術工作人員。
最重要的是,我們把這些人聚集在一起,還要雇用律師、社會學家來為我們獲取“許可證”。所有項目的獲取途徑都不一樣,很復雜,而我們還要同時為幾個項目絞盡腦汁。比如1977年,我們手頭的項目有“柏林國會大廈”、“新橋”、“馬斯塔巴金字塔”等,一旦某個項目有了點眉目,我們就把所有的錢、時間和精力投入其中。獲得許可證的過程中,幫助我們的人以及阻止我們的人,形成了作品本身蘊含的巨大能量。J:哦,你完全不能,要是沒有親眼所見,用腳踩過那片土地,用身體體會空間,你是無法想象的。
我們的作品都是一次性的,拆掉就不會再現了。不過,那些親歷過我們作品的人,即使與兒孫分享的時候,也一定記得那種震撼性的感受。C:你知道,我們的作品都是靠“租借”那些非常特殊的空間來完成的。我們的作品繼承了這些空間的所有特質。我們租借了兩周德國國會大廈,這座大廈對于德國人而言,絕非普通的建筑;我們租借了兩周“新橋”,這座橋對法國人而言意味著400年的歷史、歷代王室變遷以及經歷過的戰爭與革命;而對于“被環繞的群島”而言,陽光、泥土、巖石、風都是作品的一部分。
C:并且,我們也從不重復創作相似的作品,人們無法在兩個地方體驗相似的感受。B:你們似乎從未幫助也未從加入過與別的藝術家的合作,更別提創辦組織了。C:我來自冷戰時期的東歐,見慣了對個人主義的扼殺,我逃離那里就是為了做“自己”;為了不跟人“合作”,我可以放棄任何東西。
幫助別人的話,我都70多歲了,既沒精力也沒時間。C:來過,來過好多次,最早是1991年,上海、北京、香港都來過。我還記得,有趣的是,1998年我們受邀來上海做講座,就在政府接待我們的豪華酒店里,安排我們為150位共產黨員做了講座。我不認為,在中國獲得許可會很容易。為了爭取阿聯酋的“馬斯塔巴金字塔”,我們努力了31年,其間發生了兩伊戰爭和海灣戰爭,該項目如今仍未有起色。J:對,以前有位美國科學家看了“飛奔的柵籬”的照片,就給我們寄了張明信片,上面寫道:“當中國的長城做了一夢,就夢到自己成了“飛奔的柵籬”,因為“飛奔的柵籬”在陽光下變幻色彩,隨風而動。
”B:你們總說你們的作品是“對自由的吶喊”,這究竟是怎樣的一種“自由”?J:一種可以在任何地方、以任何方式、用任何樣子來實現,但卻不是在任何時候的自由。C:就像轉瞬即逝的彩虹、孩子的青春,我們的作品是如此短暫,并將永遠消失;沒人可以占有它,沒人可以購買它,它就在那里,沒人可以征收門票,沒人可以控制它;在存在的兩周內,它對每個參觀者都是免費的,但他們都知道,作品即將永遠消失,而不是像奧林匹克、迪斯尼樂園那樣,可以再來一次;
就像我們自己的生命那樣,無法重復。J:所以,我們是不會接受贊助的,誰出錢就要聽誰的。我們要用自己想要的顏色尺寸,在我們選擇的地點,做我們愛做的“關乎歡樂與美感”的作品。無論你去不去看,它都靜靜地在那里,這就是“自由的吶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