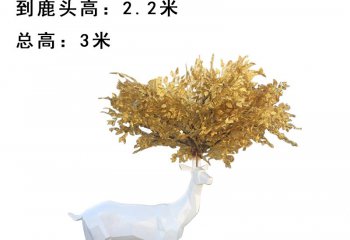30年只是彈指一揮,但剛剛過去的30年卻使我們有太多的感慨和激動。30年的中國文化發展,反映了我們對事物的看法、對世界的認識、對未來的期許發生了深刻變化。“卻顧所來徑,蒼蒼橫翠微”。不知是世界改變了我們,還是我們改變了世界?這些改變明天是否還將繼續…

我們從本期開始,將陸續刊發公共文化、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領域專家、學者及相關從業者的回顧性文章,以回首過去的30年,更是為了翹首未來的日子。——編者伴隨著30年來我國改革發展的浪潮,中國民間美術的發展,在一定意義上反映出中華民族最本源的民間文化的命運,反映出近百年來中國的農民作為民族文化傳承者的命運。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慘遭破壞的民間文化開始復蘇,那些曾經被視為“封建迷信”的民俗信仰文化又開始在民眾日常生活中復活,民間美術也隨之興盛起來。

20世紀80年代,應當是中國近百年來民間美術最活躍、最興盛的時期,主要反映在主流文化對民間美術藝術價值的推崇和文化認同,另一方面也反映在民間美術傳承者開始漸漸脫離民俗功能轉而去進行藝術創作。這一現象在民間剪紙領域尤為突出。隨著80年代民俗生活的復蘇、復興,再到新時期的發展和創造,民間美術已經頻頻登上時代的“大雅之堂”。這是民間美術的黃金時代,但同時也是其最后的“回光返照”。

那10年當中活躍、高產的老一輩民間美術傳承人,也成為農耕時代最后一批傳統民間美術的文化記憶群體,而今天他們絕大部分已經離開了人世。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弘揚民族文化和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質的文化發展戰略,在此影響下,文化部、國家民委、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共同啟動了“十部中國民族民間文藝集成志書”的編纂工作,這個歷時20多年的浩大工程,對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的民間文化藝術的價值認同和文化記憶的收集整理都起到了重要的歷史作用,也產生了非常積極的社會影響。

但遺憾的是其中居然沒有民間美術。許多浮出水面的民間美術傳統,沒能進入國家民族民間文化搶救保護事業的議事日程中,我們也因此錯過了民間美術普查、收集、發掘、整理的最佳時機。上世紀80年代,國家主導的民間美術調查、收集、整理、展覽工作以及其他相關的社會活動非常活躍。當時的文化部社文司以開展全國群眾文化工作的方式方法,開始了“民間藝術之鄉”的命名工作,同時也支持舉辦了許多相關展覽和學術會議,此項工作一直貫徹到縣級基層文化館。

80年代初,陜北延安地區在13個縣市開展了以民間剪紙為主要對象的民間美術普查,并在此基礎上選出剪紙能手辦班,這是當時民間美術復興和進入時代主流文化視野的代表性個案。普查和發掘確立了民間美術作為民族藝術文化組成部分的身份,發掘出了代表性的天才傳承人,而且通過集中辦班搞剪紙創作的方式,還發現了傳統民間剪紙中大量具有民俗價值的文化記憶,同時也激活了剪紙傳人的創作熱情。
1980年4月,在北京中國美術館舉辦了改革開放以來第一個大型民間剪紙展——“延安地區民間剪紙展覽”,展覽首次以藝術家署名介紹的方式推出了具有民俗內涵的傳統剪紙以及現實生活題材的新剪紙,展覽于次年赴法國巡回展出。應當說,80年代陜北剪紙在主流文化藝術舞臺上的亮相,以及當時刊物、報紙對民間美術的推介,都對當時的美術界產生了深遠的歷史影響。
那些熱衷西方現代藝術的青年藝術家們,在本土民間美術資源中發現了頗具現代感的藝術參照。當時在官方主辦的美術展覽中,借鑒民間美術形式因素和民俗主題的藝術創作屢屢獲獎。在80年代初期主流藝術形態的“民間美術熱”中,藝術家們并不關心民間的生存現實,更多關注的是民間美術的形式元素和民俗主題。作為國家級的美術品展示空間,中國美術館在80年代籌備的“民間美術博物館”開展了比較大規模的民間美術收藏工作,對此國家每年都有固定的資金投入。中國美術館在80年代舉辦了多次不同省份、不同地域的民間美術主題展,這些都對“民間美術熱”起到了廣泛的推動作用。
這一時期社會上比較活躍的民間美術研究者們,都不辭辛勞地去做田野采風,積極參與相關社會活動,專注于某一類的民間美術研究,這是一個民間美術資源學術發現和積累的時代。這一時期,民間社團開展的民間美術調查、發掘、研究、推介等社會活動也非常活躍,如當時中國民間剪紙研究會、中國民間美術學會、中國民間工藝學會、農民畫學會等活動頻繁。
民間社團的組織者多為高校和文化機構的專家學者,他們以多年從事專業研究和田野調查的積累,有效地開展了許多有社會影響的活動。民間社團的作用是以專家學者的學術理念聯合統籌全國各地的政府部門、民間學術力量,也包括民間美術代表性傳承人的參與,形成了專家、政府、傳承人、民間美術收藏者、專業藝術家、傳媒人等廣泛的社會協作模式,可以說民間美術許多的發掘推介工作,都是民間社團以文化志愿者參與的方式完成的,這是今天仍然值得借鑒、推廣的民間美術傳承保護模式。在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美術教育領域,中央美術學院對待民間美術表現出比較自覺的文化認同,該校民間美術系的建立也是這個時代最具代表性的事件之一,它標志著民間美術進入國家高等教育的知識體系當中,也應當是新中國美術教育史上的標志性事件。
1986年,陜北和隴東6位鄉村“剪花娘子”被邀請到中央美術學院向師生表演剪紙,此舉產生了極大的社會影響,不僅促成了民間美術系的建立,也引起了師生們對民間造型體系的關注,掀起了師生下鄉采風的熱潮。原中央工藝美術學院和南京藝術學院80年代在中國民間工藝美術方面的發掘、整理研究,同樣有許多開創性的貢獻。
但遺憾的是,這些大多是個人常規的學術行為,許多高校并沒有建立起使民間美術在學院體制內立足和可持續發展的學科模式,當這一代熱心民間美術的人退休后,許多有益的研究與教學無法持續。到了90年代,中國進入了一個經濟高速發展的時代,鄉村的大批青年農民涌入城市,鄉村傳統的生產方式呈現衰勢,傳統的民俗生活也趨向淡化。民間美術漸漸失去所依附的載體,許多傳統民間美術類型甚至逐漸瀕危,同時,一些民間美術類型脫離開民俗,開始市場化、商品化。
同時,受到經濟大潮和價值導向的影響,政府主導的基層民間文化藝術的調查收集、發掘整理、組織活動等工作幾乎處于停滯狀態,市場經濟價值觀也沖淡了以往群眾文化建設的價值理念。許多縣級文化館開始把80年代民間美術普查所得的代表性民間美術資源復制生產,通過市場化的方式獲取經濟利益。民間美術產品的商業開發本無可厚非,但不應當忽略當地真正的民間美術傳承工作,尤其是以村社文化為中心的民間美術傳承工作。
中國民族眾多,地域遼闊,文化多樣,其中文化的多樣性與400萬個自然村有著直接的密切聯系。幾千年持續穩定的村社文化傳統,是中華民族文化多樣性活態的基因庫,活態文化資源正是通過村社的生活形態持續傳承的,村社中的一代代人是文化傳承的主體。改革開放30年來經濟、文化上的變化,預示著文化自發、依賴于民間村社約定俗成方式傳承的時代正在結束。
90年代是中國鄉村傳統村社文化形態向現代鄉村文化形態轉型的過渡時期,經濟大潮動搖了鄉村民間文化傳承的根基,文化傳承出現了斷層。鄉村基層文化工作受到了忽視,傳統的村社文化傳統趨于松散衰落,文化多樣性受到了很大的損傷。
更大的問題是村莊的“生命力”衰弱了下來,只留下老人、婦女和兒童的村莊更是如此。90年代還呈現出民間美術市場化資本化的趨勢,受經濟利益的驅使,一些地區的民間美術在非民俗的生產中,出現了粗糙化、隨意化的傾向,民間美術傳統的基本程式因為人為因素發生了很大流變。這一時期地方政府在民間美術保護傳承上的冷漠和忽視,或短視功利化的對待民間藝術的現象十分普遍。新世紀的前夜,教科文組織在巴黎總部開始醞釀和啟動“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項目的評選。我國在90年代末也在著手制定與民族民間藝術相關的法規政策,如1997年5月20日國務院發布的《傳統工藝美術保護條例》,1998年以來文化部與全國人大教科文衛委員會開始組織起草《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民間傳統文化保護法》,這個保護法在中國加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后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法》。
進入新世紀,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事業在中國的開展,應當是劃時代的社會政治文化事件,其最重要的標志是幾千年來一直處于中國農耕社會邊緣底層的農民群體,作為民族文化傳承主體正式登上主流文化的歷史舞臺,幾千年來一直處于自生自滅的鄉村民間文化形態,首次作為當代社會可持續的文化資源和本土文化象征進入國家發展的視野,非物質文化遺產提升了民間文化作為文化多樣性主體身份的價值。作為瀕危性遺產的民間美術已經進入國家保護名錄中,而作為活態文化的民間美術傳統,更需要尊重、理解和敬畏。
21世紀是一個民眾傳承的活態文化復興的時代,民間美術傳統會伴隨著民眾生存狀態的升華與發展,去完成自身的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