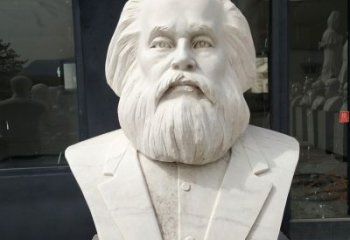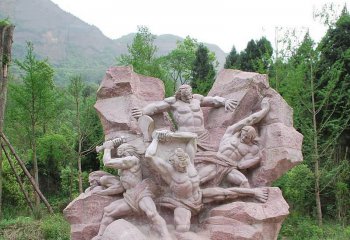目前鑒定宋至清傳世古玉的分歧較大亟須綜合探討,達成共識國人收藏傳世古玉歷史悠久,積累了豐富的鑒定經驗,關于鑒定古玉的古今專著已有不少種,但過去由于受客觀條件制約,眾說紛紜,分歧錯雜,未能整合梳理而趨于一致。由來已久的習慣勢力和傳統觀念仍在古玉鑒定領域發揮作用,扭轉這一混亂局面是當今文物工作者和玉器研究家的當務之急,也是必須完成的歷史使命。宋玉鑒定長期以來一直處在一個誤區,在過去相當長的時間里人們對宋玉面貌的認識模糊不清,以前,在故宮博物院流傳著“宋玉細”的說法,這種說法后來擴大到對宋代所有工藝制品的鑒定之中,也都是以“細”為其標準。

當時對這個“細”字未曾深思,經過長期的實踐與研究之后,越來越感到其不妥之處較多,妥帖之處較少。近年筆者研讀了乾隆帝御制詩文等文獻資料,譬如說乾隆帝認為某件宋作玉爐是一幅玉圖畫,他還鑒定另一件青玉獸耳云龍紋爐為廟器,雖對其年代未作判定,但從其飛龍形貌與動態可知,其必為宋器而無疑。乾隆帝的上述考證使今人鑒定宋玉頗受啟迪。吉林、北京、上海、四川、陜西等地宋金墓出土的玉器均為宋玉鑒定提供了可靠的證據,使宋玉鑒定有了突破性進展,但尚不能解決鑒定中存在的全部問題,尤其在獸禽、嬰戲、螭虎等肖生玉雕的鑒定上仍存在著較大分歧,并未消除。
出現分歧的原因非常復雜,并且是多方面的,假如集中于一點,則是各家都堅持自己的看法,各家之間也從不進行交流,都不知除了自己的主張外其他鑒定家的具體主張,互相間好似毫無了解。此外還有一個缺欠,就是沒有在查找證據上下功夫。盡管出土玉器并不多,但多少可以提供一些這樣或那樣的鑒定上的真實憑據,這也就是我們過去常說的鑒定標準或鑒定標準器。我認為以迄今已出土的宋至清的玉器為基礎,將其按器形、紋飾以及作工分別進行排比歸納,抽衍出鑒定用的證據,將這些證據再用于鑒定上,肯定會有很好的成效。如果能夠這樣做,我相信宋代至清代的玉器鑒定工作就有可能達到有證據、有科學性、有準確度的境界,即達到“實證鑒定法”的科學高度。
試探“實證鑒定法”的兩種鑒定標準并認同輕微模糊度的存在上面講過宋玉鑒定的概況,已由過去的誤判魔圈走上今天的科學鑒定的道路,這是經過幾十年來的汲取前人摸索鑒考經驗所取得的初步成果。過去所謂的宋玉是包括兩宋在內的籠統的時代界限,大概不會包括同時并存的遼、金等邊疆地區民族政權的玉器,這是歷史的局限性使然。現在我們所說的宋玉將北宋和南宋同姓皇室的兩個時代區分開來,兩宋的玉器各自有不同的風格與特點,這是宋玉鑒定的宏觀標準。與此相聯系的是遼朝玉器的存在,這已被正史所證明,在《遼史·服輿志》中就有不少有關玉器的文字記載,這是有目共睹的。
近五十年來已出土了二百余件遼代玉器,經初步研究,其中確定包含著富有契丹民族特色的玉器,這不僅肯定了遼玉的存在,也指明契丹族玉器的出現。與遼玉相聯系的還有五代十國玉器的問題。五代十國是指梁、唐、晉、漢、周等五個奉唐正朔的短祚王朝以及在全國各地冒出來的吳越、吳、前蜀、楚、南漢、閩、南平、后蜀、南唐、北漢等十個小國,其中吳越錢氏及其家族墓、前蜀王建墓、南唐李弁與李縖墓均出土了玉器。
這批五代十國玉器中不僅有不少的有利于玉器鑒定的微觀標準器,并且最為重要的是它滌蕩了唐代帝王玉的精美華麗的富貴氣息,滋生了平淡近人的鄉土韻味,而宋玉恰好繼承了五代十國,嚴格地說就是吳越玉器平淡近人的風格,發展成為樸素淡雅的具有平民色彩的玉器。從這一角度思考,五代十國玉器是摒棄了唐代帝王玉的氣派而創造了貼近生活并富有地方風格的玉器。遼玉直接繼承梁、唐、晉等正統王朝玉器的傳統,它在東北邊疆和中原地區發育成長,是與五代至北宋玉器并存的具有統一時代風格和民族色彩的玉器。
北宋玉器則直接柴周衣缽,在中原及江南文化的基礎上成長起來,它帶有濃重的庶民色彩。由于北宋繪畫藝術高度發達,輻射力極強,玉壇亦概莫能外,故而出現了乾隆帝稱之為“玉圖畫”的帶有極濃的繪雕性的玉器。民玉出現于北宋,從中原逐漸蔓延至全國,大大沖淡了玉苑原有的帝王玉色彩,庶民玉器像潮水一般上漲,拍擊著帝王玉的護堤。偏安的南宋王朝與強勁的北方女真族金政權長期并存,雙方的撻伐與和好互為交替,最后均亡于蒙古汗鐵蹄之下。
南宋與金南北分治,金雖與南宋交往密切,文化上受其影響,但仍以本地北宋固有文化藝術為主流,女真本民族的文化漸漸被淹沒,曾為遼金故土的白山黑水地區出土的玉器已傳遞了這一歷史信息,所見女真族玉器只有承繼契丹族的春水秋山玉得到巨大發展并趨向完善,而其它各種玉器與南宋玉器不論題材還是形飾都很相像,疑其在本地碾琢之外,不排除通過民間交易和戰爭掠奪等手段直接地或間接地取自南宋。
上述五代十國、遼、北宋、金、南宋等五個時代及其各個王朝玉器發展的時空關系,是通過正史、文人筆記等文獻和對出土、傳世玉器的分析研究、比較整合之后所獲得的嶄新認識,如本文所附的這幾件遼、宋、金玉器,都帶有樸素平淡、貼近生活的特點,它的藝術手法是形神兼備的現實主義,充滿著詩情畫意,散發著濃郁的藝術芳香。
如果我們鑒定人員能夠真正掌握宋玉的這一宏觀鑒定標準,便可以避免出現朝代鑒定上的重大誤差。宋代現實主義手法的后續情況如何,這是我們研究玉器的人都十分關心的問題。歷史的發展軌跡說明,蒙古汗、元帝國確是全盤繼承宋玉現實主義藝術手法的正統的接班人。
談到這里,我們還要向讀者講明,在上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我們在劃分玉器發展的時空框架時,曾將元朝與明清兩朝聯系在一起,提出了“元明清玉器”的說法,這是由于過分看重元明清均建都于北京的政治文化背景,還沒有真正地掌握玉器文化本身及元明兩朝玉器的區別。之后,英國“玉之友”主席弗雷先生約我寫元明清玉器,我便應允寫了一篇專文,經弗雷找人譯成英文之后公開發表在英國倫敦出版的《玉》上。此后,我在投入玉器藝術方法研究時發現,元明兩朝玉器是由兩種截然不同的藝術方法所支配,元是宋代現實主義藝術方法的繼續,到了明初,這種現實主義藝術方法已成尾聲。
明清玉器的藝術方法應是擬古主義的而不是現實主義的。所以,從藝術方法來看,宋元玉器藝術是一脈相承,持續發展,但在工藝上已出現簡單粗糙、留下部分工藝痕跡的缺點。如附圖中的這幾件元代玉器在形象的生動性與活力上確與宋玉形象十分接近,也表明了宋玉與元玉在藝術方法上的一致性與近似性。我在研究明代玉器時發現,其早期與晚期的玉器在形制、裝飾及形象上出現了摹擬古代玉器做工和造型,由此發展起來形成一種社會風潮和藝術傾向。
其時的碾玉名家就是蘇州的陸子剛,流傳下來的子剛款玉器真贗難分,是一個很難解開的歷史謎團,尚有待辯證。到了清代,經歷了康熙、雍正兩朝的整頓和開創,終于醞釀成康熙、雍正及乾隆等三種藝術模式,在形式上、工藝上與明晚期好似不同,但其指導思想與藝術方法卻很相近,明清兩朝玉器均表現出明顯的崇古、仿古傾向。
不難看到明清兩朝玉器藝術的共性與個性并存的狀況,還可看到其發展變化的軌跡。史實證明,元與明、明與清之間,或者元、明、清三代之間的玉器分期都不可避免地出現一定的模糊度、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這既是客觀存在,是玉器發展本身出現的現象,又是玉器鑒定者主觀認識上的局限性所致,玉器斷代的難度亦由此而加大。古玉鑒定標準的重要價值上面我們談了宋至清玉器藝術方法及時代風格的變化和發展,那么藝術方法和時代風格對玉器鑒定有何意義和價值呢?
我認為,研究玉器的專家學者只要掌握了歷代玉器的藝術方法和時代風格,便等于掌握了古玉宏觀鑒定標準,當應用到古玉鑒定時雖不能達到百分之百的準確率,也可達到基本準確。如果是一位富有經驗的文物工作者也依據上述中外藝術格調和藝術方法鑒定文物,再兼用宏觀的鑒定標準和經驗,相信其鑒定準確率一定會有所提高的。可知宏觀鑒定標準是關系全局的概括性的抽象性的標準,所以非常重要,但是目前古玉鑒定人員大多還未注意到這一層面,往往以微觀鑒定標準為唯一的鑰匙去開啟古玉鑒定迷宮大門上的鎖,其效果便往往會不理想。
這并不意味著微觀鑒定標準不重要,如果這樣理解則是十足的誤會。那么古玉微觀鑒定的標準是什么?有何價值?我認為,古玉微觀鑒定的標準是涉及一件玉器的局部性的、具體的、具象的標準,是可以看得見、摸得著的,也是比較容易掌握的、頗有靈驗的鑒定標準,所以很受歡迎。
譬如說現在把時間拉近到唐宋或其以后,過去收藏家有個俗稱“唐大頭”,意指唐代玉雕人物的頭面較大,這就是關乎唐代人物玉雕鑒定的微觀標準,其準確的概率較高,但也不是絕對可靠的,譬如唐玄宗前后陶俑的頭就顯得不大而是合乎人體比例關系的。由于唐玄宗前后的玉俑還未發現,是比例均衡還是“大頭”尚不可知,所以“唐大頭”仍是一付靈丹妙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