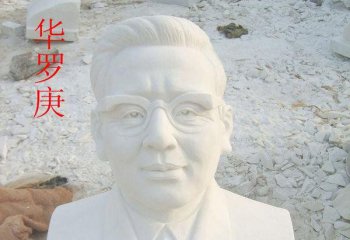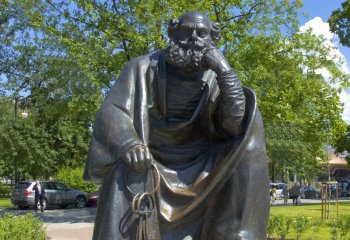漢代是中國歷史上雕塑藝術大發展的時期,俑的種類、數量、材質、顏色、造型、水平等都達到了新的高度。陜西西漢帝陵陶俑數量很大,一般高50-60厘米。或上承秦俑,模制敷彩;或沿襲楚風,裸塑著衣。王侯墓中,除武裝士兵俑外,家中奴婢和伎樂俑也占很大比例。型體略小于帝陵之制。低級官吏和地主墓中也有放置俑的,俑的構成主要是家內奴婢。西漢南方常見木俑,楚制依舊。而山東地區陶俑也繼承了戰國齊地古拙的傳統。
東漢伴隨著莊園豪強的發展,與場景模型配置的小型陶俑多了起來,而且造型更為生動傳神。其中河南的樂舞百戲、武裝部曲俑;四川的勞作、說唱俑;廣東的陶船及船夫俑;甘肅武威的銅車馬儀仗俑代表著這一時期的最高水平。是一種代替活人陪葬的雕塑,研究對象多為墓室中出土的考古發掘,俑的使用是為了死者能在冥世繼續如生前一樣生活,所以俑真實負載了古代社會的各種信息,對研究古代的輿服制度、軍陣排布、生活方式乃至中西文化交流皆有重要的意義。
而且中國古俑在其盛行的從東周至宋代的約1500年中,彌補了同時期地面雕塑在種類及完整性上的重大缺憾,為我們勾勒出古代雕塑藝術發展的脈絡以及歷代審美習尚變遷的軌跡,成為了解中國古代雕塑藝術史不可或缺的珍貴實物資料。西漢初期,漢高祖采用了“黃老”思想做為自己的統治思想。這種統治思想,在當時起到了相當積極的作用。
秦代修長城、連綿三百里的阿房宮、一直到始皇帝死還沒有修好的秦始皇陵以及春秋戰國的連年混戰,搞的國家一窮二白,人民苦不堪言,百業待興,急需休養生息。在這樣的背景下,主張“無為”而治,反對戰爭、反對苛捐雜稅、反對勞苦兵役,是順應歷史和人民的呼聲的。“黃老之學主張實行“無為”政治,主張統治者“省苛事,節賦斂,毋奪民時”和“節用民力”等等,要求統治者適當減輕人民負擔,不要過度地剝削和壓榨人民。
這就有利于緩和社會矛盾,使人民發揮生產的積極性,恢復和發展受到嚴重破壞的社會經濟。這些基本主張既符合人民休養生息的愿望,也適合統治階級鞏固統治的需要。”1漢初的幾任丞相,大都“治黃老之術,實行無為而治。”西漢中期,漢武帝摒棄這種“黃老”思想,反對“無為”而治,而是采取相當強硬的政策,采用“外儒內法”的統治思想,這又與當時西漢國力的強盛、匈奴的不可一世有密切關系的。
黃老之學在漢初十分流行,有很大的影響。漢初黃老之學,促進了封建統治秩序的鞏固,為社會生產的恢復創造了條件。但是,“隨著統治階級本身力量日益強大以及社會矛盾日益尖銳,統治者必然要求強化和集中權力,不可能長期安于“清靜無為”的自由放任狀態。”1于是,西漢初期一度盛行的黃老之學,到了西漢中期的漢武帝時代,也就隨著國家由弱到強的轉變,走上了由盛而衰的道路,最后讓位于為漢武帝“有為”政治服務的董仲舒的新儒學理論體系。
西漢初年,由于國家急需休養生息,漢高祖劉邦采用了“黃老”思想做為自己的統治思想,實行“無為”政治,主張“省苛事,節賦斂,毋奪民時”和“節用民力”等等,需要適當減輕人民負擔,所以漢代雕塑與秦相比就又有其不同之處。
首先,它沒有像秦代兵馬俑那么龐大的工程,尺寸約五十公分左右,只有秦俑大小的1/3-1/5,由于西漢的政治穩定,人殉意味已不多存,轉為人間場景的呈現。其次,在造型上秦俑和漢俑的不同處,在人物塑造上,身體及四肢造型比較簡單;手腳以木頭制作再接上;減少了臉部細節的雕刻,以彩繪替代刻畫細節;人物傳神表情豐富,動態鮮活;
尺寸約五十公分,為真人大小的1/5;姿勢已不多,多為自然的動態;跪祭姿勢的出現;表現平民日常生活及道具;將對象縮小,表現了雕塑能力的提高;場景與人俑相結合等等。,西漢前期,某些軍功顯赫的將領及受封的諸侯王,也使用陶塑兵馬俑隨葬,以炫耀其生前地位與權利。“一九六五年秋出土于咸陽楊家灣漢墓的十一個從葬坑的彩繪兵馬俑中,計有騎兵俑五百多件,步兵俑一千八百多件。
墓主人可能是西漢重臣周勃、周亞夫父子。騎兵俑高六十八厘米左右,步兵俑高約四十四至四十八厘米,制作精細,神態威武。騎兵俑與步兵俑分置與不同坑內,和秦俑坑車、步、騎諸兵種混合編隊的情況不同;騎兵在總兵力中的比重也明顯增加,顯示了文、景時期騎兵有了巨大發展的狀況。”2《史記.匈奴列傳》曾有:漢文帝時,為了防御匈奴的入侵,于公元前166年“發車千乘,騎十萬,軍長安旁,以備胡寇”3的記載,證明當時漢王朝騎兵軍事力量的強大。出土的兵俑有執俑、執旗俑、敲擊俑、舞蹈俑、指揮俑等不同職能的將士。
他們神態各異,服飾、姿勢也各不相同。“從服飾上看,楊家灣漢俑服飾既繼承和發展了秦服飾,又吸取了“胡服”、“楚服”的一些長處,是保存有三者服飾特色的新階段,而以楚服飾的特點比較突出一些。戰國時期,諸侯割據,“田疇異畝,車涂異軌,律令異法,衣冠異制。”秦統一后,這許多“異”大體上都化為同了。
秦始皇“兼收六國車騎服御”,創立了各種制度,其中包括衣冠服制。這些制度的確定,對漢代影響很大。”4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后乎。」此言充分反映孔子非常反對以人形為殉葬品,因而此舉也反映出人心的貪婪與不甘寂寞。漢代雕塑所呈現的高度寫實技巧與表達內在神情的傳統,在以西安和洛陽的具有宮、官色彩的“京洛風”俑系和以四川地區為主的“巴蜀風”上充分的表達出來。
“巴蜀風”其風格特色更為活潑自由,無宮、官氣息,甚受民間贊賞。拂袖舞俑,是京洛風中較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此俑著長袖舞衣,瀟灑輕盈,體態婀娜,上身淺俯,緩扭腰肢,舞步輕蹈,雙肩一上一下舒展長袖,似乎正踏著樂曲的節拍偏偏起舞,優美動人。恰于漢代詞賦中所描寫的‘振飛以舞長袖,裊細腰以務抑揚’、‘振朱履于盤撐,奮長袖之颯麗’等麗句相印。可見,這精美的拂袖舞俑,正是當時最為流行的‘長袖善舞’之生動寫照。
”5四川地區由于自然資源豐富,社會經濟得到長足發展,文化藝術獨具特色,民間藝術更發展蓬勃。四川不少地區因而出土了說唱俑,反映了漢代四川民間藝術的發展情況。其中特別為人所稱道的是出自成都天回山的東漢擊鼓說唱俑。表現一名老年侏儒俳優赤膊光腳,右臂挾鼓,左手持鼓槌,表演到高潮時,情不自禁地揚臂抬腿的情態。“這件俑,藝術處理上采用了大膽夸張,寓神于情的手法,將說書人伸頭拱背,揮手抬足,激情演唱的動作姿態,進行了大幅度的夸張強化,從大勢情緒上加強了感染力。
”6與之異曲同工的另一件陶說唱俑出自郫縣宋家林漢墓,表現的是一名說唱俑在表演中的一個瞬間──他大半身袒露,肥大的褲子系在臍下,兩足蹀躞,歪頭聳肩,舌頭舐著上唇,神態非常滑稽。重慶鵝石堡山漢墓所出的一件以紅砂石雕鑿的俳優俑,坦腹仰首箕踞而坐,一手握拳,一手伸開,說唱到忘情處,也吐出舌頭。類似的說唱奏樂俑在四川還有很多,都很富于風趣。也許,這正反映了四川人所特有的幽默性格。
至今,四川地方戲曲中仍然保留著那種帶著地方特色的詼諧與技巧。由于政治上得到暫時安定,農業大為發展,使得一般地主官宦們過著“谷物滿倉,牛羊成群”的安樂生活,反映在他們的墓葬明器中,陶塑的豬、狗、牛、羊、雞、鴨等家畜家禽以及糧食、井欄、爐灶、樓臺等小型模型非常常見,可說是西漢墓葬的突出特點,對后世影響很大。“河南輝縣百泉出土的陶羊、陶狗、陶狐等作品,造型渾厚有力,神態刻畫細膩感人,以其生動的藝術形象吸引著觀眾,從這組動物形象的塑造可以看到當時雕塑藝術所取得的輝煌成就。”7雕塑藝術與其它造型藝術一樣,是一定的社會生活和思想意識的反映,它體現了整個時代的物質基礎和精神面貌。
由于兩漢時代處于中國封建社會的上升階段,因此,它所形成的國家強盛和雄健的民族氣魄,也很自然的反映在這一時期的雕塑藝術中,使的兩漢時代的雕塑作品不論在題材內容、整體造型等方面都具有磅礴的氣勢。漢代墓俑即便在輪廓和造型上,難免尚有古拙簡括之處,但由此更增強了任務神態的含蓄沉穩,更為耐人尋味。漢代陶俑正是適應當時的歷史條件而出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