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時(shí)間上來(lái)說(shuō),“理性之潮”最早發(fā)生于“北方藝術(shù)群體”,其建立時(shí)間是1984年9月15日,其次發(fā)生在85年7月浙江美術(shù)學(xué)院畢業(yè)生展中,再次是于1985年10月開(kāi)幕,作為《江蘇青年藝術(shù)周》一部分的《大型現(xiàn)代藝術(shù)展》。除去這三部分之外,其余還有數(shù)十個(gè)展覽和幾個(gè)群體都被《中國(guó)當(dāng)代藝術(shù)史1985——1986》的作者們劃分在“理性之潮”范疇之內(nè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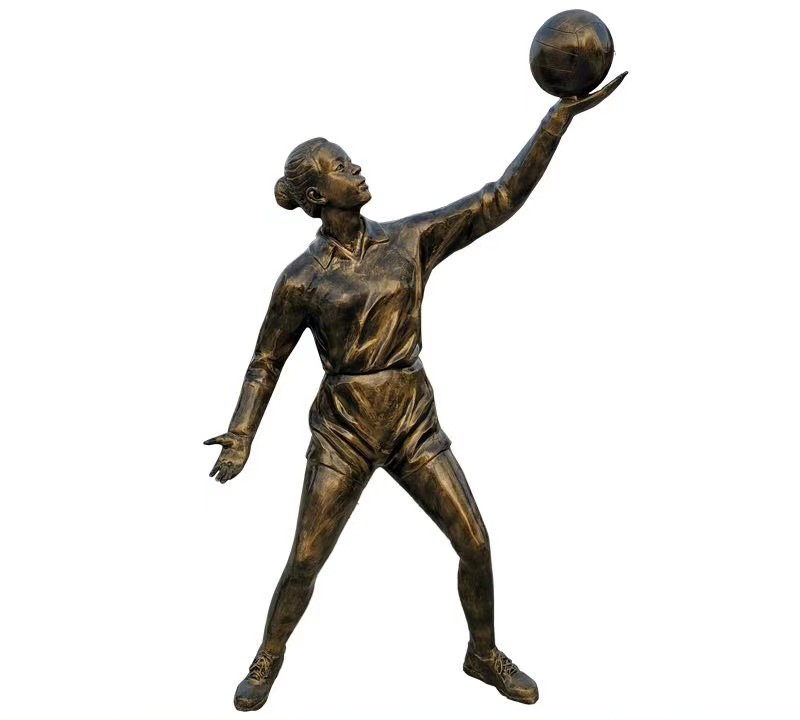
但是本文的目的并非要重新站到《當(dāng)代藝術(shù)史》作者的角度上,再度總結(jié)“理性之潮”的風(fēng)格特點(diǎn),而是把“理性之潮”作為一個(gè)事件,研究它所發(fā)生的過(guò)程和原因。八五美術(shù)運(yùn)動(dòng)從本質(zhì)上來(lái)說(shuō)并非某些大師的運(yùn)動(dòng),而是由全國(guó)各地自發(fā)的美術(shù)組織和藝術(shù)家組成的帶有啟蒙性的美術(shù)運(yùn)動(dòng)。

“理性之潮”同樣也是這樣,它不是一個(gè)有預(yù)謀的“起義”,而是自發(fā)話語(yǔ)的無(wú)意識(shí)匯集。但是,如果我們現(xiàn)在還將“理性之潮”作為一個(gè)自發(fā)“起義”來(lái)思考問(wèn)題,就不可避免地做一些重復(fù)工作,所以,我們不妨換一個(gè)角度思考問(wèn)題,即探討“理性之潮”中的“理性繪畫”概念是怎樣被接受的?我們要回答這個(gè)問(wèn)題,僅知道群體出現(xiàn)時(shí)間遠(yuǎn)遠(yuǎn)不夠,因?yàn)檫@涉及到一個(gè)更重要概念,即話語(yǔ)。任何一個(gè)群體都不能孤立存在,如果“理性之潮”一直是一個(gè)自發(fā)的運(yùn)動(dòng),那么現(xiàn)在也不會(huì)出現(xiàn)諸如“理性之潮”與“理性繪畫”之類的概念,而只有“北方藝術(shù)群體”、“池社”、“紅色旅”等各個(gè)團(tuán)體和展覽的名稱而已。

因此,“理性繪畫”的概念必定是在一定的話語(yǔ)驅(qū)動(dòng)之下產(chǎn)生了運(yùn)動(dòng),并通過(guò)特定渠道進(jìn)行了傳播。因此,我們不得不指出“理性之潮”的話語(yǔ)中心——《美術(shù)》雜志及其與之相關(guān)的話語(yǔ)持有者,也就是說(shuō),潛在的“理性繪畫”概念在沒(méi)有接觸到北京《美術(shù)》雜志和《中國(guó)美術(shù)報(bào)》時(shí),幾乎處于靜止?fàn)顟B(tài)。

“北方藝術(shù)群體”雖然成立于1984年,但是,因?yàn)椤按藭r(shí),任戩考回魯美讀研究生,而舒群留在長(zhǎng)春工作。哈爾濱只有王廣義一人在組織活動(dòng)。由于‘群體’其它成員的消極情緒及勾心斗角的瑣事的干擾,此間的‘群體’實(shí)際上是名存實(shí)亡”。舒群所謂的“此時(shí)”應(yīng)該是指1984年9月份,這也是任戩研究生入學(xué)的時(shí)間。直到1985年11月,“北方藝術(shù)群體”的影響力也沒(méi)有超出邊緣性區(qū)域。《美術(shù)思潮》雜志在第二期刊發(fā)了“北方群體”成立的消息,這也已經(jīng)是1985年2月-3月的事情了。

在1985年4月,“北方群體”主辦的刊物《GOD》由于行政干涉沒(méi)能出版,進(jìn)一步限定了它的傳播范圍。直到1985年11月份之后,我們才能看到眾多媒體對(duì)“北方藝術(shù)群體”的報(bào)道,特別是北京的《美術(shù)》雜志和《中國(guó)美術(shù)報(bào)》兩份刊物。
與“北方藝術(shù)群體”相比,浙江的“理性繪畫”幾乎于1986年才加入到北京這個(gè)核心話語(yǔ)圈。雖然,1985年9月20日出版的《美術(shù)》雜志第九期中,以展覽為開(kāi)端介紹了浙江美術(shù)學(xué)院畢業(yè)展,但也僅僅局限在教學(xué)領(lǐng)域,對(duì)其中以張培力和耿建翌為代表的“理性繪畫”關(guān)注較少。南京的“理性繪畫”在1985年10月份剛剛與觀眾見(jiàn)面,直到11月份,丁方的作品才得以在《江蘇畫刊》1985年11期中得到發(fā)表。可見(jiàn),直到1985年10月以前,“理性繪畫”三股潮流并沒(méi)有碰到一起,“符號(hào)”的運(yùn)動(dòng)正是發(fā)生在1985年11月。
話語(yǔ)權(quán)與運(yùn)動(dòng)的關(guān)系越來(lái)越明顯,缺少話語(yǔ)權(quán)的一方必須與掌握話語(yǔ)權(quán)的一方相互溝通,才能使自己的話語(yǔ)具有流通性。在80年代,中國(guó)還存在一個(gè)關(guān)鍵詞即行政權(quán)力,此時(shí)的話語(yǔ)權(quán)往往依附于行政權(quán)力。同樣,藝術(shù)的話語(yǔ)權(quán)也要依附于行政權(quán)力,在行政權(quán)力發(fā)生變更時(shí),藝術(shù)話語(yǔ)的流通也會(huì)發(fā)生相應(yīng)的變化。通過(guò)這種藝術(shù)話語(yǔ)權(quán)與行政權(quán)力錯(cuò)綜復(fù)雜的關(guān)系,我們可以看出“理性之潮”的發(fā)展蹤跡。
我們從現(xiàn)有的原始資料可以看出“北方藝術(shù)群體”與《美術(shù)》雜志之間的親密關(guān)系,如在1985年底,雖然《美術(shù)》雜志沒(méi)有介紹“北方藝術(shù)群體”,但是與《美術(shù)》雜志同屬中國(guó)藝術(shù)研究院的另一份刊物《中國(guó)美術(shù)報(bào)》則在1985年第18期介紹了“北方藝術(shù)群體”,并發(fā)表了舒群的文章《北方藝術(shù)群體的精神》和王廣義的油畫《凝固的北方極地》25號(hào)以及其它“群體”成員的作品。《中國(guó)美術(shù)報(bào)》第18期印發(fā)于1985年11月23日,稿件必定是在11月23日之前就已經(jīng)寄到編輯部。
想必在這之前,“北方藝術(shù)群體”已經(jīng)建立了與北京核心藝術(shù)傳媒的親密關(guān)系。對(duì)于“北方藝術(shù)群體”與北京《美術(shù)》雜志的關(guān)系,下面這封信件說(shuō)的更明白:昨日我到《美術(shù)》去了,見(jiàn)到了高名潞將你的幾篇稿子都留在他那了。名潞這個(gè)人非常好,年齡與我相近,可能略大三歲吧!
他對(duì)我們的作品和你的文章很感興趣準(zhǔn)備在近期刊用。名潞可能過(guò)段日子會(huì)給你寫信的。我把你的詳細(xì)地址留個(gè)他了。名潞告訴我前幾日中國(guó)美協(xié)油畫藝術(shù)藝委會(huì)召開(kāi)學(xué)部委員會(huì)時(shí),他把我上次寄給他的你的幾張畫和我的“極地”等作品在油畫藝術(shù)委員會(huì)關(guān)于現(xiàn)代油畫發(fā)展討論會(huì)上,用幻燈在討論會(huì)上放了,我們的作品放幻燈效果非常好,引起了與會(huì)代表的關(guān)注和好評(píng)。
名潞并介紹了我門的創(chuàng)作思想等。今晚六點(diǎn)我到了陶詠白家,遇到了她,與她談的很高興。你那篇《風(fēng)起云涌的群體思潮》一文,詠白說(shuō)她準(zhǔn)備給你用,并讓我轉(zhuǎn)告你不要急。這是“北方藝術(shù)群體”成員王廣義給舒群的信,落款是1986年3月6日。通過(guò)信件里的措辭:“…他把我上次寄給他的你的幾張畫和我的“極地”等作品在油畫藝術(shù)委員會(huì)關(guān)于現(xiàn)代油畫發(fā)展討論會(huì)上…”,我們便可以看出,這已經(jīng)不是王廣義與高名潞的初次會(huì)晤,在此之前,王廣義與舒群已經(jīng)去過(guò)北京,并和高名潞交流了看法。
另外,我們還可以看出王廣義對(duì)高名潞的態(tài)度:“名潞這個(gè)人非常好,年齡與我相近,可能略大三歲吧!他對(duì)我們的作品和你的文章很感興趣準(zhǔn)備在近期刊用。”這也從一方面說(shuō)明了在86年以“北方藝術(shù)群體”代表的“理性繪畫”之所以能以壓倒性的優(yōu)勢(shì)占據(jù)85新潮的部份原因。此信也說(shuō)明了雜志刊登稿件時(shí),很大程度上不是依靠接受陌生投稿的手段,而是根據(jù)內(nèi)部的傳遞關(guān)系。之所以將“理性之潮”的時(shí)間定在1985年11月,是因?yàn)樵谶@個(gè)月中《江蘇畫刊》發(fā)表了丁方的《漫足黃土高原所感》一文,并用一個(gè)彩版和兩個(gè)整版刊登了其作品。
1985年11月23日引發(fā)的第18期《中國(guó)美術(shù)報(bào)》首版中,刊登了舒群的《“北方藝術(shù)群體”的精神》一文,并刊登了王廣義作品《凝固的北方極地第25號(hào)》,王海燕作品《沉默》,劉劍宏作品《水桐樹(shù)》。在上文的信中,我們可以看到,王廣義在見(jiàn)到高名潞的同時(shí)又見(jiàn)到了陶詠白,并主要談了發(fā)稿件的事。最重要的是85年18期《中國(guó)美術(shù)報(bào)》頭版的編輯就是陶詠白,因此,我們可以推斷出陶詠白在85年11月《中國(guó)美術(shù)報(bào)》發(fā)表“北方藝術(shù)群體”的文章后,兩者彼此建立了聯(lián)系。
在此之前,《美術(shù)》雜志已經(jīng)在9月刊中刊登了浙江張培力等人的作品,所以,我們可以說(shuō),直到1985年11月,“理性之潮”的主要三個(gè)群體才開(kāi)始共同進(jìn)入傳播渠道。一般的史學(xué)研究方式只是將某一個(gè)畫派的成立時(shí)間作為此畫派的開(kāi)始,但“理性之潮”作為一個(gè)群體性事件,它的開(kāi)始應(yīng)該考慮到多個(gè)時(shí)間。再次,我們要嚴(yán)格區(qū)分事件發(fā)生時(shí)間和事件傳播時(shí)間區(qū)別。事件發(fā)生時(shí)間非常容易確定,但是它絲毫沒(méi)有意義,就像語(yǔ)言的私人性一樣,它不進(jìn)入公共領(lǐng)域,就不能產(chǎn)生意義,所以我們要強(qiáng)調(diào)歷史發(fā)展過(guò)程的事件傳播時(shí)間。
傳播時(shí)間非常復(fù)雜,它會(huì)隨上下文的變化而變化——“上下文不是給定的,而是被發(fā)現(xiàn)的”,并涉及到符號(hào)與話語(yǔ)之間的復(fù)雜關(guān)系,這是我們以后要分析的問(wèn)題。那么在此,我們通過(guò)傳播媒介,通過(guò)不同話語(yǔ)的碰撞,可以看出,確實(shí)是從1985年11月份開(kāi)始,“理性之潮”的話語(yǔ)才共同進(jìn)入傳播領(lǐng)域,其雛形才開(kāi)始形成。是什么時(shí)間出現(xiàn)的“理性繪畫”這一概念呢?
我們可以肯定,必定是在1985年11月之后。我們現(xiàn)在需要考察的是“理性繪畫”這一概念出現(xiàn)之前,其雛形是什么?我們首先不得不提及為“理性繪畫”奔走呼吁的藝術(shù)家舒群。他有兩篇重要的文章,一篇是《一個(gè)新文明的誕生》,另一篇是《關(guān)于北方文明的思考》,其后來(lái)的文章都是圍繞這兩篇文章提出的觀點(diǎn)而進(jìn)行的寫作。我們可以把這兩篇文章看作是“北方藝術(shù)群體”的宣言之作,它們同時(shí)被置于其群體刊物《God》的最前端,可見(jiàn)文章本身的重要性。
1985年4月是重要的一個(gè)時(shí)間點(diǎn)。北方藝術(shù)群體自成立之后,卻面臨解體的危險(xiǎn),為了解決這個(gè)問(wèn)題,舒群百般周折調(diào)入哈爾濱,開(kāi)始了振興群體的工作,其中一項(xiàng)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創(chuàng)辦刊物。1985年8月30日,刊物《God》大樣出廠,其中的稿件可能在9月9日的研討會(huì)之后做過(guò)一定的修改,但是基本雛形已經(jīng)建立。其中《一個(gè)新文明的誕生》并沒(méi)有涉及到太多藝術(shù)上的內(nèi)容,而是后一篇文章落款為1985年6月18日的《關(guān)于北方文明的思考》一文,詳細(xì)論述了關(guān)于藝術(shù)創(chuàng)作中的“理念”和“北方文明”崛起的問(wèn)題:我們常聽(tīng)到這樣的一些見(jiàn)解,藝術(shù)創(chuàng)作僅僅是個(gè)人情感的沖動(dòng)的結(jié)果。
也即是對(duì)某種萬(wàn)物在感情上產(chǎn)生了強(qiáng)烈的反響,持著這種感情通過(guò)藝術(shù)的手段流露出來(lái),這便是藝術(shù),這便是藝術(shù)的本質(zhì)。然而對(duì)于理念則認(rèn)為只屬于藝術(shù)的范疇,因此在藝術(shù)創(chuàng)作中排斥理念的作用。進(jìn)而認(rèn)為理論是多余的,有害的,其實(shí)從本質(zhì)上要這種排斥理念的思想同樣也是受著某種理念的支配。
魯?shù)婪颉ぐ⑺己D吩谒摹端囆g(shù)與視知覺(jué)》一書中這樣說(shuō)道:“不僅理智干擾了直覺(jué)時(shí)會(huì)破壞各種心理的平衡,當(dāng)情感壓倒了理智時(shí)也會(huì)破壞這種平衡。過(guò)分地沉溺于自我表現(xiàn)并不比盲目地順從規(guī)矩好多少。對(duì)自我進(jìn)行毫不節(jié)制的分析固然是有害的,但拒絕認(rèn)識(shí)自己為什么要?jiǎng)?chuàng)作以及怎么樣創(chuàng)作的原始主義行為同樣也是有害的。”我想,阿恩海姆的這段論述是以說(shuō)服那些排斥理念的人。
誠(chéng)然,抱著墨守成規(guī)的陳腐傳統(tǒng)理念是創(chuàng)作枯竭的根本原因,然而因此排除一切理念,甚至對(duì)本時(shí)代的時(shí)代精神以及對(duì)自身的歷史使命也不加以研討,那么無(wú)疑這種盲從的“創(chuàng)造”必將最后走向毫無(wú)疑義的廢品排瀉。打個(gè)比方說(shuō):從古代希臘到文藝復(fù)興好比建起一座“大廈”,而出現(xiàn)在十九世紀(jì)到二十世紀(jì)的“現(xiàn)代派”思潮,恰是“拆除”這個(gè)已在腐朽的大廈的過(guò)程。
因此,迪尚在《蒙娜麗莎》的美麗面孔上加上胡須的意義正在于此。無(wú)庸贅言,當(dāng)我們沉思著從當(dāng)代這種紛繁的“新世界”中走出之后,我們都會(huì)承認(rèn)這樣一個(gè)真理:“現(xiàn)代派”不是完美的!畢卡索不是完美的,達(dá)里不是完美的,拋去對(duì)“現(xiàn)時(shí)代”的狂熱,當(dāng)我們從一個(gè)更高點(diǎn)立足之后,我們便會(huì)看到“現(xiàn)代派”的高峰與之古希臘和文藝復(fù)興時(shí)期的藝術(shù)相比較,無(wú)異于富士山與珠穆朗瑪峰的比較。更形象些說(shuō),比起古希臘、文藝復(fù)興的大廈,“現(xiàn)代派”不過(guò)是一堆瓦礫。顯而易見(jiàn),破壞行為比起建樹(shù)行為總要短暫很多,從古希臘到文藝復(fù)興歷時(shí)幾千年建起的藝術(shù)圣殿竟在一夜之間成了破磚爛瓦,同時(shí)又如摧毀這座大廈那樣迅速,人們很快就清理掉這一廢墟,開(kāi)始了新的建設(shè)。
在整篇文章中,藝術(shù)家集中反對(duì)了創(chuàng)作中的情感至上主義,并批判了由這種感情沖動(dòng)所引發(fā)的現(xiàn)代主義運(yùn)動(dòng)。這當(dāng)然出自舒群思考的兩個(gè)緯度:第一,在藝術(shù)實(shí)踐中如何體現(xiàn)冷靜的創(chuàng)作觀念;第二,怎樣建立一個(gè)能夠概括其群體藝術(shù)實(shí)踐的概念“北方文明”。“理念”是舒群文章的關(guān)鍵詞,它不僅關(guān)系到藝術(shù)的創(chuàng)作,而且是其“北方文明”之所以能夠成立的基礎(chǔ)。在此,“理念”的對(duì)立面是“個(gè)人情感的沖動(dòng)”。
舒群認(rèn)為理念不僅存在于“藝術(shù)”中,同樣也存在于“藝術(shù)創(chuàng)作中”,因此,“理念”又同時(shí)具有了“理論”的含義。通過(guò)引用阿恩海姆的語(yǔ)言,他更加明確了“理念”的含義,即藝術(shù)創(chuàng)作中的冷靜態(tài)度,也可以說(shuō)是一個(gè)藝術(shù)家在創(chuàng)作過(guò)程中所擁有的理性。“理念”和“個(gè)人情感的沖動(dòng)”的對(duì)立并沒(méi)有結(jié)束,舒群隨即將理論的重點(diǎn)轉(zhuǎn)移到了文化上。他將“個(gè)人情感的沖動(dòng)”與西方現(xiàn)代藝術(shù)的“任意揮灑的潛能”聯(lián)系在一起,并將“理念”與古代希臘與文藝復(fù)興時(shí)期的藝術(shù)歸為一類。
在這兩者的比較中,西方現(xiàn)代藝術(shù)無(wú)疑成為“一堆瓦礫”。那么,他們所謂的“北方文明”就是建立在被現(xiàn)代藝術(shù)毀掉的西方古典文明的廢墟之上。因此,在形而下層面上,他認(rèn)為“理念”是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形而上層面上,“理念”又是“北方文明”的關(guān)鍵因素。至于后者,它明顯來(lái)源于黑格爾的美學(xué)理論——“美是理念的感性顯現(xiàn)”。“理念”在此包含三個(gè)要素,首先是“概念”,其次是“概念”的表現(xiàn)形式,最后,是兩者的統(tǒng)一。
如果再往后追溯,我們更能看到柏拉圖的影子。“理念”作為世界最高的核心,是萬(wàn)物之始,藝術(shù)則是處于對(duì)“理念”模仿的模仿。無(wú)論是黑格爾還是柏拉圖的理論,都顯示出了“北方文明”的傾向性。在舒群后來(lái)寫的文章中,要表述的更加清楚:一九八五年七月我又在哈爾濱的朋友的介紹下看到了《凝固的北方極地》這套組畫,又一次的震動(dòng),觸及心靈的震動(dòng),荒漠的原野,暗藍(lán)色的天空,凝固了的人形再一次展現(xiàn)了北方那種神奇?zhèn)グ兜氖澜纾@種互不知曉的同構(gòu)意味著什么呢?
此次遭遇不能不引起我的深思,在我重新翻開(kāi)世界美術(shù)史的時(shí)候,我發(fā)現(xiàn)了文化中心北移這一重要特點(diǎn),西方文化從埃及、古希臘、古羅馬、佛羅倫薩到巴黎,西方的文化中心在逐漸北移,同時(shí)在這種北移停止了的時(shí)候西方文化也就隨之消亡了。這篇寫于1985年7月之后的文章表明,在看了王廣義的《凝固的北方極地》系列作品之后,更加堅(jiān)定了舒群對(duì)“北方文明”與西方古典文明的傳遞性關(guān)系。但是,在此之前的那篇《對(duì)北方文明的思考》并沒(méi)有清楚地點(diǎn)明“北方文明”所蘊(yùn)含的“理念”的具體含義,或確切的說(shuō)是沒(méi)有說(shuō)明“理念”落實(shí)到畫面上應(yīng)該呈現(xiàn)什么樣的結(jié)構(gòu)。
1985年《God》雜志由于各種原因沒(méi)有能夠出版,導(dǎo)致應(yīng)當(dāng)進(jìn)入傳播渠道的文章失去了應(yīng)該有的傳播效應(yīng)。但是,早在《God》大樣出廠之前,在1985年7月出版的《美術(shù)》雜志上,刊登了高名潞的一篇名為《近年油畫發(fā)展的流派》一文。在這篇文章中,作者用了三對(duì)相互對(duì)立的概念對(duì)70年代末到85年之間發(fā)生的藝術(shù)現(xiàn)象進(jìn)行了初步總結(jié),其中第二部分名為“理性主義·自然主義”。我們有必要看一下他對(duì)“理性主義”的論述:“在任何一個(gè)偉大的情感的復(fù)興之前,必須有一場(chǎng)理性的破壞運(yùn)動(dòng)”,這個(gè)破壞運(yùn)動(dòng)出現(xiàn)了。
由青年業(yè)余畫家和專業(yè)畫家組成的一些畫會(huì),特別是“星星畫會(huì)”,為這一運(yùn)動(dòng)的先鋒派,過(guò)去的條條框框在他們那里要少得多,因此其要求解放的口號(hào)就徹底得多。他們的創(chuàng)作觀念走在了實(shí)踐的前面,“藝術(shù)是理念的感性顯現(xiàn)”,對(duì)于他們來(lái)說(shuō)再合適不過(guò)了…他們代表著新時(shí)期中新一代的審美思潮的趨向,他們要將久被壓抑的胸中的巖漿噴發(fā)到畫面中去,他們要表現(xiàn)運(yùn)動(dòng),表現(xiàn)加快了的時(shí)代步伐。
你看艾未未的《水鄉(xiāng)碼頭》、肖大元的《魚與網(wǎng)》、何寶森的《路漫漫》,那些點(diǎn)與線、面與體在多方向多中心地躁動(dòng)著。運(yùn)動(dòng)就是美,世界的本質(zhì)就是運(yùn)動(dòng)。他們的可貴之處也正在于作品中顯示的理念的沖動(dòng)。他們之中的一些“靜態(tài)”的作品又似是凝固的巖漿,是熱情凝縮成的哲理和觀念。如甘少誠(chéng)的《主角》、陳延生《隕》、嚴(yán)力的《對(duì)話》,我不能確切地解釋它們,也不了解作者的動(dòng)機(jī),我與他們毫無(wú)過(guò)從,但我知道這里含蘊(yùn)著他們要說(shuō)明的某種社會(huì)哲理。理念是情感的伴和物。按照格式塔心理學(xué)家阿恩海姆解釋,情感活動(dòng)是對(duì)總的精神活動(dòng)發(fā)動(dòng)起來(lái)之后使神經(jīng)活動(dòng)達(dá)到某種“沖動(dòng)程度”的體驗(yàn)。
這是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動(dòng)力和支配物,這動(dòng)力的來(lái)源則是“一個(gè)人有意識(shí)或無(wú)意識(shí)地意識(shí)到的全部事物和事件”,這里有理念的成分,有意識(shí)的支配,但它必須是與無(wú)意識(shí)和不能被準(zhǔn)確地知覺(jué)和推理的東西相協(xié)同的。二者的渾然天成是藝術(shù)品偉大之所在。
由于功能主義的畫家們的意識(shí)和觀念太強(qiáng)了些,他們似乎還缺乏某種特定的形式,遂使其作品有些圖解之嫌。蘇珊·朗格曾說(shuō):“純粹的自我表現(xiàn)是不需要形式的。”表現(xiàn)可以隨意,而藝術(shù)形式卻不能隨機(jī),它永遠(yuǎn)是個(gè)別的,是不能放之四海而皆準(zhǔn)的。如果說(shuō)“理念”在舒群的文章中既有理性的含義,又有概念的含義的話,那么在高名潞的文章中,術(shù)語(yǔ)的運(yùn)用則更為準(zhǔn)確到位,“理性”和“理念”已經(jīng)有了初步區(qū)分。“理性主義”一詞,在文章中被作者用來(lái)形容以“星星畫會(huì)”為代表的強(qiáng)調(diào)功能主義的畫家們,用以說(shuō)明他們具有的強(qiáng)烈自我意識(shí)和觀念性。
而“理念”則是用來(lái)說(shuō)明“星星畫會(huì)”藝術(shù)家的創(chuàng)作方式,即創(chuàng)作觀念要先于實(shí)踐。高名潞明確說(shuō)明了舒群文章的內(nèi)在邏輯——“藝術(shù)是理念的感性顯現(xiàn)”。所以,“理念”在此文的含義更加明確,就是指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概念及其實(shí)踐,那么“理性主義”則是對(duì)這種“理念”現(xiàn)行的創(chuàng)作模式的理論總結(jié)。因此我們可以說(shuō)舒群更多是從一個(gè)藝術(shù)家的角度來(lái)思考自己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及其要表達(dá)的文化內(nèi)涵,而高名潞則是站在《美術(shù)》雜志編輯的角度,站在批評(píng)家的宏觀角度來(lái)對(duì)全國(guó)的藝術(shù)現(xiàn)象進(jìn)行總結(jié)。
這篇文章的寫作上下文是“第六屆全國(guó)美展”的舉辦以及展開(kāi)的相關(guān)討論。在《美術(shù)》雜志1984年12月刊上刊登了署名為“時(shí)真”的標(biāo)題為《第六屆全國(guó)美展油畫研討會(huì)在沈陽(yáng)舉行》的報(bào)道文章。文章首先以官方的辯證口吻提示要“充分肯定油畫的成績(jī)”,其次才提出了油畫創(chuàng)作中存在四大問(wèn)題:1、“題材決定論”的影響依然很大,有些作品仍然是所謂的“大題材”,架子大,板著面孔,使觀眾感到疏遠(yuǎn)。
2、有些作品重視美術(shù)的教育功能而忽視美術(shù)的審美功能。說(shuō)教、說(shuō)明,而不能給人以美的享受,使觀者感到乏味。3、形式風(fēng)格過(guò)于單調(diào)和簡(jiǎn)單,油畫形式的豐富性和技巧的特殊性,未能得到充分研究和發(fā)揮。4、油畫應(yīng)該走出展覽館、博物館、畫院和學(xué)校,到社會(huì)上去,滿足廣大人民對(duì)油畫日益增長(zhǎng)的需求。以上四大問(wèn)題成為全國(guó)美術(shù)工作者特別是美術(shù)青年所關(guān)注的主要問(wèn)題,“在畫家中似乎有‘凡是六屆美展擁護(hù)的我們就反對(duì)’這樣一種逆反心理存在”。反對(duì)第六屆美展的思想成為85年青年藝術(shù)家創(chuàng)作的主要?jiǎng)恿Γ呙禾幱凇睹佬g(shù)》雜志這樣一個(gè)核心話語(yǔ)地,一定意識(shí)到了這個(gè)情況,所以在《近年油畫發(fā)展的流派》、《三個(gè)層次的比較》和《一個(gè)創(chuàng)作時(shí)代的終結(jié)——兼論第六屆全國(guó)美展》三篇文章中,依次總結(jié)了一個(gè)時(shí)代結(jié)束,提示了85美美術(shù)運(yùn)動(dòng)的合理性。
從這個(gè)上下文來(lái)看,作者大多用否定的語(yǔ)氣來(lái)敘述昔日的美術(shù)創(chuàng)作。讓我們?cè)倩氐健督陙?lái)油畫發(fā)展的流派》一文中去,看一下高名潞提出“理性主義”的真正用意。高名潞通過(guò)對(duì)星星畫會(huì)的論述所引出的“理性主義”并非贊揚(yáng)這種理念先行的創(chuàng)作模式,相反是對(duì)這種方式提出批評(píng)性意見(jiàn)。
他首先認(rèn)為星星畫會(huì)的藝術(shù)家有兩種創(chuàng)作風(fēng)格,一種為“動(dòng)態(tài)”,另一種為“靜態(tài)”。并且這兩種形態(tài)都屬于“理念先行”的創(chuàng)作方式。繼而又認(rèn)為這種理性主義由于過(guò)于注重藝術(shù)的功能性,從而放棄了藝術(shù)本真的一方面。也就是說(shuō),他在這篇文章中批評(píng)理性主義,主要是因?yàn)槔硇灾髁x藝術(shù)家在創(chuàng)作過(guò)程中只有好的理念是不行的,還必須注重藝術(shù)的形式,只有形式與內(nèi)容的完美融合才是理性主義的最佳狀態(tài)。如果我們回頭思考一下高名潞提出這個(gè)批評(píng)性觀點(diǎn)的依據(jù),或許能夠發(fā)現(xiàn)一個(gè)有意思的現(xiàn)象。
在批評(píng)理性主義之前,他在文章中先引用了阿恩海姆的一段話,用以來(lái)證明藝術(shù)創(chuàng)作中理念與無(wú)意識(shí)的相互融合才是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最佳狀態(tài)。但是,在舒群1985年6月18日寫的《關(guān)于北方文明的思考》一文中,同樣引用了阿恩海姆的話作為自己論證的基礎(chǔ),但是得出來(lái)的卻是更為極端的結(jié)論——理念是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根本,其與激情相互對(duì)立。
同樣是應(yīng)用了阿恩海姆的理論,兩人卻得出了不同的結(jié)論,從表面上看,是因?yàn)樗麄兏髯砸昧税⒍骱D凡煌恼Z(yǔ)言,但是,其實(shí)質(zhì)是兩人對(duì)以“理念先行”之藝術(shù)理解上的差異。在舒群的文章中,理念在藝術(shù)創(chuàng)作中只有一個(gè)發(fā)展方向,就是冷靜的分析;而在高名潞的文章中,理念之于藝術(shù)創(chuàng)作則有兩個(gè)發(fā)展方向,即激情和冷靜的分析。因此,理性主義在產(chǎn)生之初就具有了兩層含義:有理念的激情和有理念的冷靜,這同時(shí)也是高名潞在1986年《85美術(shù)運(yùn)動(dòng)》一文中分析“理性繪畫”三種主要樣式的最初模式。
通過(guò)對(duì)兩篇文章的對(duì)比,我們就能夠知道,不管是藝術(shù)家還是理論家,在1985年11月之前都沒(méi)有提出“理性繪畫”的概念,而是提出了與這個(gè)概念最接近的“理性主義”和“理念”的概念。但是,很明顯,“理性主義”和“理念”并非處于一個(gè)敘述層面,一個(gè)出于總結(jié)性的理論敘述層面,一個(gè)出于實(shí)踐性的操作層面。所以,后來(lái)“理性繪畫”的概念應(yīng)該出于“理性主義”的邏輯,而非出于“理念”的邏輯,畢竟,“理性繪畫”和“理性主義”是出于同一個(gè)敘述層面,前者相對(duì)于后者只是內(nèi)涵的不斷擴(kuò)充而已。
而我們應(yīng)該明白的是,在高名潞寫出《近年油畫發(fā)展的流派》一文時(shí),他并沒(méi)有關(guān)注到“北方藝術(shù)群體”成員的活動(dòng),同時(shí),此群體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也還在創(chuàng)作之中,所以在論述“理性主義”時(shí)用了星星畫會(huì)的例子,而非后來(lái)典型“理性繪畫”的代表——“北方藝術(shù)群體”。舒群對(duì)“理念”概念的闡釋雖然沒(méi)有上升到理論高度,但是卻恰當(dāng)?shù)乜偨Y(jié)群體的藝術(shù)指向,明確了“北方藝術(shù)群體”對(duì)繪畫中“冷靜”風(fēng)格的追求,這種風(fēng)格也成為后來(lái)“理性繪畫”的主導(dǎo)風(fēng)格。
《北方藝術(shù)群體歷史資料歷史資料》,舒群,《八五美術(shù)運(yùn)動(dòng)》,高名潞等著,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07《北方藝術(shù)群體歷史資料》舒群“討論會(huì)之后,理論刊物《GOD》即將成書。正值此時(shí),來(lái)至省里各方面的壓力和國(guó)家關(guān)于出版物的通知迫使我們停刊。但是國(guó)內(nèi)有關(guān)刊物相繼報(bào)導(dǎo)了《GOD》創(chuàng)刊的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