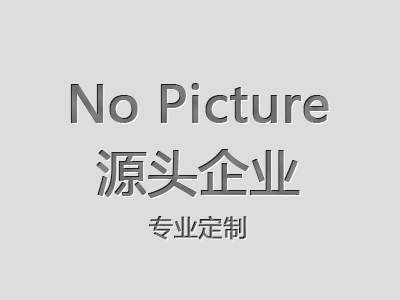一瓢飲:我一直覺得美術作品的形式和內容都非常重要,但我以前一直最鐘愛的是那種首先給人強烈審美愉悅的作品,比如文藝復興后的歐洲古典主義作品,我想知道你的想法,美術作品的形式是否重要?“美”的內涵與外延應該怎樣解讀?首先我想說一個問題,就是藝術品不完全是帶來愉悅感的東西,藝術品只是在呈現藝術家的心靈的力量,而這力量的起點是多元的,建設的或毀滅的欲望都能產生力量。形式感對于藝術品來說是重要的,但形式的東西是不斷變化的,總體來說帶有普遍性的形式外衣在不斷地解體,從西方來看,到了印象派之后,形式感的變化在不斷的加快,藝術的形式不斷隨著藝術家的創作沖動而改變,每個人都能創造出一個形式主體,藝術家來自社會的感受通過不同的途徑進入藝術家的心靈,在那里與藝術家的“原型”聚會,這聚會的結果將形成人對外部世界的理性的或非理性的反映,而藝術家的將通過特定形式,從外部走到他那聚會的地點,去呈現那場聚會,或傾聽那里的言說或與那里對話,這必然導致的結果就是,藝術家走向自己,首先得探索不同的走向自己的方法,首先的找到與自己心靈發出的相一致的語言,這語言就是藝術的形式,只有不斷地深入走向自己心靈的最深處,才能走向所有人。

“美”的概念在我看來,就是力量。美最深的表達是指,外部的形式能印證或呈現一些關于人類整體性,帶有永恒性的東西。而美在最表面層面,是指能帶來一些情緒與思考的力量。飛翔的大鳥:什么是真正的藝術家呢,什么是偉大的作品呢?藝術家一定需要被大眾認可嗎?

在我看來,一個真正的藝術家,就是能否用他自己的藝術形式,走到他的心靈的最深處,原型與外部感受交集的起點處,在那里找到一些人類整體的秘密。一件偉大的藝術品,能夠穿越時空,恒古長存,即使這件作品所采用的形式已經不再使用,作品呈現的內容,已經被現在的世界所遺忘,他還能存在,還能穿過一切形式邏輯的屏障,自達觀者的內心。

另外,不是所有的偉大的藝術品都能被理解,不是所有偉大的藝術品都能在觀者中都能帶來普遍的震撼,偉大的藝術家有如先知,往往是現時代的局外人,他獨特的藝術形式,或在普遍的大眾藝術形式下隱藏著藝術家的精神秘密,在開始的時候,一般只有少數人能感知,能體會,隨著時間的流逝,少數人到多數人,在到更多人,在時間流逝中,隨時都有著藝術家們真實行走,周而復始,見證人類精神傳承,這是偉大作品延續的范式。

其實更多的藝術家與藝術作品,在時間過程中,靜默著,很少被關注,永遠都沒有被主流世界關注的機會,他們的作品如空間飄散的種子,被命運所決定,但這一切都不影響一代一代的藝術家們對于自己的真誠,他們在創作過程中體會喜悅,是他們孤獨的走向自己,探索生命的動力,他們可能只影響一個人,他們的作品可能只會在500年后復活,對于創作者本來已經毫不重要了,這些人的存在給于了人在世界的存在予以意義的回答。

這讓我想阿倫特在“黑暗時代的人們”一書序言里所說,“即使在最黑暗的時代中,我們也有權期待一種啟明,這種啟明或許并不來自理論和概念,而更多地來自一種不確定的、閃爍而有經常很微弱的光亮。這光亮源于某些男人和女人,源于他們的生命和作品,他們在幾乎所有情況下都點燃著,并把光亮射到他們愛塵世所擁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圍”。飛翔的大鳥:你怎么評價最近幾十年的中國藝術家呢?從我的藝術觀來看,中國近30年的藝術家,關注他們作品的藝術精神的呈現,如果放棄特定的社會環境的思考,可以概括為三類藝術家:第一類的藝術家,如陳逸飛、丁少光、何多苓等,我將他們稱呼為情緒藝術家,他們的作品一般停留在情緒的表達的層面,這些作品所帶來的感受,是可以用語詞描述得非常清楚,他們對于精神世界的探索還停留在表面化的階段。
第二類藝術家,張曉剛、方力鈞、曾浩等,他們首先是一個社會見證者或記錄者,或對社會理解的思想陳述者,他們也可以歸納為社會藝術家的范疇,他們不僅僅是記錄一個時代外部特質,更努力想去接近那個時代呈現的時代情緒,如二戰前很多超現實主義的藝術家所做的工作一樣,然爾,記錄性的形式語言,強化了社會性的敘事,而失去了進入自己心靈的利器,這樣作品更接近在表述一個歷史的片段,或個人情緒在時代的背景下的宣泄。
更為遺憾的是這類藝術家,他們為維護大眾認可的形式的標簽而戰戰兢兢,甚至真誠的創作沖動也在不自覺中演變為商業行為,這必然使他們作品的社會批判精神演變為矯情的媚俗行為。第三類藝術家比較接近我對于藝術精神的理解,我稱這類藝術家為生命藝術家,丁方、唐堯、90年初的羅中立、早期的葉永青等,丁方無疑是比較接近那整體秘密的少數藝術家,他的畫面呈現出驚人的感染力,能直達心靈深處,黃土、樹木、或很多抽象的形體,無不是丁方走向自己的印記,但是丁方也只是接近我所認為的好的藝術品,他的作品的宗教氣質阻礙了他對自己的擁抱,也阻礙了他對社會的全面感知,不是說藝術家不能有宗教性,而是宗教性還應該在作品更深的底層,我是講作品在走進自己的時候,應該是無跡可尋的,不必然的表現,將帶來必然的表現,這點上更接近對執著的放棄,這個狀態更接近擁抱、傾聽、或呈現,而不是表現,或許應該忘記表現的前提。
唐堯是我認識的值得敬佩的藝術家,他的作品大地的敘事,將不同材質不同時期的東西組合成若干層,每一層都是創造物,每一層都是上一層的覆蓋于延續,上一層又是后一層的前提與承載者,這件作品有著我所認為的好作品的精神范式。羅中立的大巴山組畫,超越了80年代初很多的藝術家,作品的形式有著特有的生命的感性力量,生命如土地般厚重,帶著生命存在者的樣態而呈現,可惜后面他停止了這些探索。
早期的葉永青也有過這類性的精神探索,不過現在基本上看不到他好的作品了。這類藝術家中的杰出代表,就20世紀下半頁西方現代藝術史來看,包括雕塑家亨利摩爾、抽象表現主義時期的羅斯科、80年代的新表現主義的基弗。一瓢飲:一個真正的藝術家應該怎樣處理現實與理想的關系?這是一個不知道怎么回答的問題,很難期待一種完美的與適合于很多人的方法,高更放棄了證券交易商的職位,到塔西提在“落后的野蠻人”那里找到生命快樂與創作的靈感。凡高在阿爾的烈日下孤獨的創作,欲望亢奮時可以為妓女獻上自己的耳朵。
賽尚有個銀行家的父親,從來不需要思考明天的早餐會在那里,當厭倦了巴黎浮華的生活后,可以在環境優美的埃克斯火山下隱居。畢加索有錢又有身體,80歲的時候追求18的少女。人的命運有如電影“楚門的世界”里面的主人公一樣,被注定與安排,小人物小制作,大人物大制作,我認為的重要的不是這宿命的前提,而是真實的選擇,即使選擇本身也如俄奧浦斯王一樣被詛咒的命運所注定,而藝術的精神能給予人的就是與之選擇的勇氣,如楚門的選擇,即使是死亡,也要看到真實,也要游到島的對岸,即使這一點也是被導演所安排,但楚門完成了他的真實與選擇,所以歸上帝的歸上帝,歸自己的歸自己。
一個藝術家或任何一個人首先需要體會到心靈的真實,有了這樣一個起點,所謂的理想與現實應該好處理了,其實任何的應對現實與理想的沖突,都是在一個“在場”的情況下,而不是理解。這點如自由,比如在酒吧可以高談闊論自由、政治、人權、等等問題,如果你回到家里,想將你的政治意見發表網上去、甚至出版,當你動筆的那一瞬間,你感到害怕了,你害怕了網上有政治警察,害怕寫作出來,有什么人來找你麻煩,這一瞬間不自由臨近了。
不自由在場,選擇這個時候才真正的出現。一瓢飲:你的靈感產生于一種怎樣的存在狀態?你對世界人生的理解來源于怎樣的生活實踐?靈感,甚至不知道他在那里,他卻又無時不在,思考、閱讀、經驗、如不同的水流在心里儲蓄,不斷地、源源不斷的留進你心靈的儲藏地,在那里匯集,思考、閱讀、經驗越多,越深入,這水流愈強大,他會通過一切的方法向外呈現,我努力捕捉這些從心靈讓外涌動的東西,去呈現他們,也與他們交流,用他們的語言與方法,靈感就源源不斷絕,表現的形式也隨著他們呈現的形式而改變,這是我體會的創作的自由。
對世界人生的理解來自于全部的經歷與我在出生那一刻已經被注定的東西,其實每一個在這點上都是一樣,沒有任何差別,但對于世界的理解每個人卻千差萬別。每個人的經歷都是獨特的,都來自外部世界與他之間的緣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