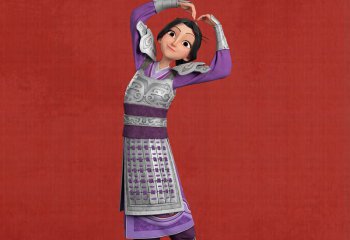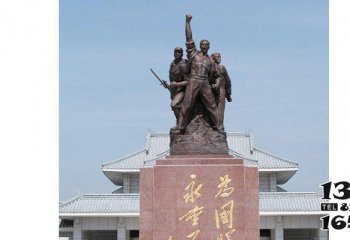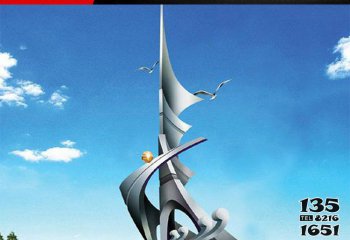談到藝術品,現在都覺得不得了,價格漲得讓樓市都不敢說自己在漲。但后來發現不是這個邏輯,歸根結底漲的不是畫,而是小富翁都已變成大富豪,他們需要一種可以讓他們一擲千金的商品,于是作為頂級奢侈品的藝術自然要漲。如此推算,現在大家一窩蜂地討論藝術品“泡沫”便毫無意義,只要大富豪是個增量,這些人愿意追加金錢玩下去,這個泡沫就會越來越絢麗。本來就是個富人游戲,吾輩在門外踮腳凸眼喊“泡沫”喊得再辛苦嚴肅,都與這個游戲扯不上半點關系。即便如此,當聽到佳士得亞洲區副主席葉正元先生的話時,仍然對這個富有的收藏群體感到些驚異——內地買家已經開始收藏歐洲印象派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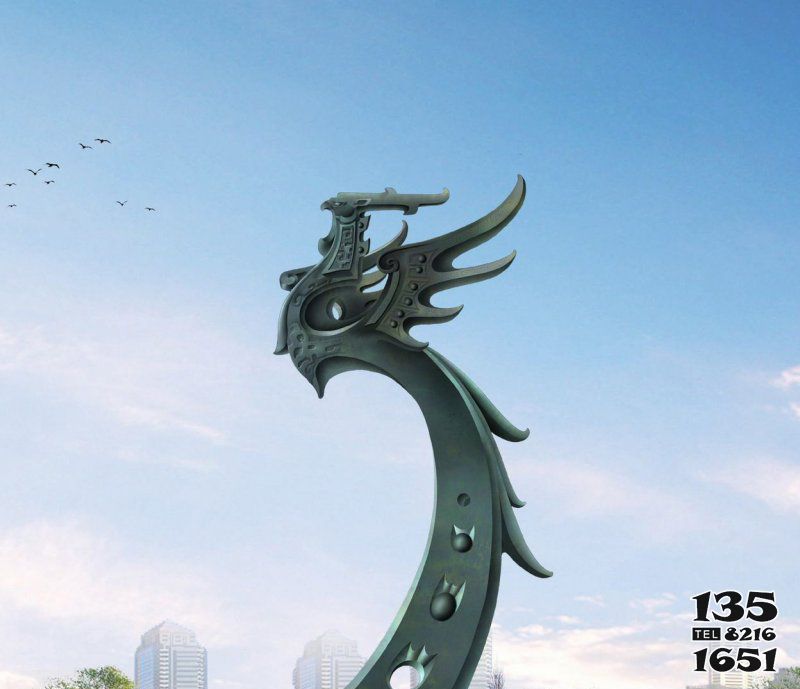
在現有世界藝術品交易市場上,印象派作品是價格最高的一個板塊,這造成更早的藝術經典多被收藏于博物館等藝術機構之中,很少流通。于是,印象派畫作就成了國際收藏家們最頂級的收藏選擇之一。當然,中國收藏家對此的介入有個數量級的差異,比如內地藏家瞄準的是百萬美元級的作品,臺灣、香港的藏家則在千萬級上打主意。

也許從這個消息,我們可以理解為什么佳士得此次不辭辛苦,漂洋過海地把包括克勞德·莫奈、愛德加·德加、阿爾弗萊德·西斯萊等印象派大師的作品運到北京,作兩日的展覽。11月,這些作品將上拍于佳士得的紐約秋拍。主辦方自然不會如此解釋此次預展的目的。佳士得公司對此次北京預展的動因說得很客氣:一是想把藝術的“真金”帶到國內來;二是想起到美育作用,讓早知印象派之名而不識其面目的國內人士熟悉一下。

事實上,佳士得把印象派作品介紹到內地,這已是第四次,最早約在2003年前后的上海。但作為印象派作品專家的葉正元坦言,盡管內地藏家對印象派已經有了收藏興趣,但他們對這些作品并不了解。h其實對藝術品了解與否無礙于藝術投資的運行,事實上相較于賣弄觀念、故弄玄虛的當代藝術作品,印象派作品的單純使它更容易被人欣賞。但如前所言,這不是問題。

藝術品投資是個很小的市場,盡管它資金總量巨大,但有能力參與的就是那些面孔,隨著他們財富的增加和興趣的愈趨濃厚,這些昂貴的畫作會以更高的價格在他們手中轉來轉去,只要有接盤能力的人存在,這個游戲就會越玩越精彩。對于普通人,我們至少有當看客的榮幸,盡管由媒體充當的無數拉拉隊把場內賽事喊得如火如荼,我們卻可以在這熱鬧中找到一些藝術收藏的本真樂趣。便如此次,如果沒有拍賣方的運作,我們也無緣見到這些19、20世紀諸大師的作品,這里有印象派的掌門人物,像莫奈、德加、西斯萊,有被后印象派大師塞尚奉為其師的卡米勒·比沙羅,有野獸派的創始者艾柏·馬爾凱,還有如雷貫耳的畢加索、亞夫倫斯基…

既有印象又有現代諸派,而且其中不乏像莫奈的《松樹,安提貝岬角》、亞夫倫斯基的《閉上雙眼的西班牙女人》這些估價在三四千萬元以上的作品。無疑,這是一個大飽眼福的機會。對于那些蠢蠢欲動又不知如何選擇的內地新興收藏家們,這也有著新品發布會的魅力。跟現在中國流行“四大天王”的畫一樣,國際上也有個“印象派風潮”。
這個風潮在印象派作品誕生之初便開始漸漸形成,與以往那些神圣、嚴肅、莊重的題材相比較,印象派的畫作因多集中于自然風光而被人所喜好,而且大多印象派作品都是畫家于室外即時創作,畫幅較小,所以適合中產家庭裝飾在自己的客廳里。但風潮的洶涌則是因為日本的介入,60年代以后,因為日本經濟上的騰飛,大批坐擁億萬身家的投資客開始在全球藝術市場上呼風喚雨,大肆收羅其他國家的藝術品,截至1990年,日本人購買世界名畫的比例占39.8%,其中多為印象派作品。
他們當時收藏的情景也同今日中國一樣,投資者調動所有力量進行鋪天蓋地的宣傳,從拍賣業、保險業、公關公司、酒店、畫廊、畫家全部進入一種集體亢奮之中,而被他們選中的畫作價格則一路高飚。今年5月,在紐約蘇富比春拍中,后印象派大師塞尚的《甜瓜》以2552萬美元成交。據統計,僅在20世紀最后20年里,印象派的作品至少已經賣了20多億美元。
如今,在這塊投資高地上,中國收藏家們也開始奪寨插旗,只是以目前的實力和對藝術了解的缺乏,他們染指的往往只是一些三流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