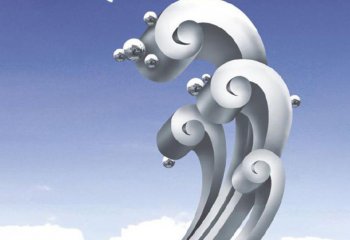《藝術與投資》:現在非常流行的“四川畫派”這個概念和當年的“鄉土”“傷痕”時候所講的四川畫派有很多的區別,更多的是一個市場概念,如果從這個角度進入,可以怎樣劃分“四川畫派”這龐大的群體呢?葉永青:我覺得四川畫派是一個早就應該超越的概念,不能局限在這樣一個概念里面來談它的前景、格局,因為四川畫派是當年77、78級開創的一片天地,如果我們按照這樣的思路延續下來,從四川出來的這批年輕藝術家會越來越弱化,不會超越以前的東西。

每個時代有不同的文化背景、現實,今天的藝術家都走在自己的路上,不能總是用一個標準、框架來定位他們。在不同的創作情形下創作出不同的作品,以前我們那個時代是比較匱乏的年代,藝術家靠逐步積累、靠努力爭取來獲得現實里的各種權利和可能的資源進行創作。今天就完全不一樣了,他們面對的就是過剩的現實,就是靠刪除,要對所有涌來的東西說“不”。今天從四川出來的這么一批蔚為壯觀的創作群體,對于這樣一種現象可以做一種觀察——把他們分為三個部分:第一種是50年代出生的,包括早期的四川畫派的一些主將,還有“85新潮”以來的一些老藝術家,他們中的很多人今天都已經是市場上的紅人;

另外一撥就是60年代到70年代出生的藝術家,他們中的有些人實際上已經是現在四川畫派的中堅力量;第三類就是70年代以后到80年代的一批被市場所推舉的群體,他們一開始就非常商業化。市場上的表現,形成了一種兩頭翹、中間下垂的局面,這里面的原因很耐人尋味。《藝術與投資》:這三個群體的藝術市場狀態大致有什么表現和特征?葉永青:50年代藝術家市場走高,這是自然形成的,也是歷史形成的,剛好是跟市場、學術在生態上有很和諧的關系。以前80年代人人都熱愛藝術,千千萬萬的人都走在藝術的路上,經過很多年的篩選和淘汰,最后就剩下幾個人、十來個人,自然地被社會吸納、消化掉,包括他們的作品,在學術上的地位、在市場上的份額、在國內國外各種收藏的格局里都恰到好處。

我把他們比做一碗“手搟面”,作品非常質樸,但又很好識別,可操作性強。今天如果你要操作這類藝術家的話可能投入比較高,但是回報同樣也是很穩定的;60年代的這部分藝術家是創作能量最大,而且也是現在最努力的一批人,但是被夾在中間,是很尷尬的一個群體,但今天他們在所有藝術方面的活躍程度是有目共睹的;我把后面70年代藝術家看作“速食面”,他們“一桶一桶”地被制造出來,知道怎么樣做正確的事情,不會犯錯誤。

在人人都不會犯錯誤的時候,能否推舉他們的就是看其背后的資金和利益集團的強大與否,能不能把他們放在生產鏈上,把他們推銷、包裝成一個名牌,70年代后的藝術家都很自然地進入了這樣一個系統里面。市場不是人為能控制的,市場有市場本身的規律。比如一個50年代出生的藝術家,無論怎么去做他的東西,都不會貶值,很多人很早就在說這些人有泡沫了,但是你發現到100萬的時候沒有問題,200萬沒有問題,300萬還是沒有問題…

為什么?因為很少。還有當年這些人在創作的時候沒有市場一說,他們不是為市場畫畫。而現在我們這些“勤奮”的藝術家可能達到一年100張畫,在當年是絕對不可能的,沒有那么大的動力來畫畫,沒有市場的刺激。他們畫畫就是為自己畫,為一些展覽分配會很自然,所以不會有我們今天所聽說的那種危機和聳人聽聞的事,而且那些作品都是大大小小的。
但是今天的很多畫家就變成像工業流水線上批量生產的商品一樣。我們做一個假設,一個60年代出生的藝術家,哪一個能做到100萬以上,100萬一定是一個坎,這些畫家都是畫3米、5米的大畫,一年100張。40萬、50萬沒有問題,100萬所有人都把畫拿出來了,等到市場上開始大量出現藝術家100萬的3米、5米大畫的時候,這個藝術家怎么做,哪一個畫廊能收拾這個殘局,這些問題就是60年代要面臨的問題。
但70年代不一樣,他們一開始就是和畫廊“合謀”。《藝術與投資》:川美藝術家的成長和展覽有著密切的關系,一開始比如是官方體制內的各種展覽,到后來90年代的“青春殘酷”展覽,對那個時候部分的川美藝術家作了合適的度量,同一時期還有許多川美藝術家參加國際大展成名,這些都似乎是在一個良性的、緩慢的過程中出現的。而近幾年多了由畫廊主導的展覽,這些展覽對老藝術家和年輕藝術家來說,各有怎么樣的影響?
葉永青:每一個時代都會有新的藝術家找一個方式來出場,像“青春殘酷”或者別的也好,這只是一個命名。中國的每一代藝術家尤其是年輕一代藝術家他們在出來的時候遇到了最好的時機,得到了市場、世界對藝術的關注,這是好事情,但同時也把別的事情給遮蔽掉了,一個藝術家很快就衣食不愁。當代藝術的本質就全世界來說都是一樣的,強調一種實驗性、可能性,它的基礎是這樣。我們今天看到的繁榮很大意義上是商業的結果。
市場有需求,這種份額是擠壓出來的,中國從80年代后期尤其是90年代發展出來的所謂當代藝術市場首先是由海外形成的,形成了對中國當代藝術的一些概念和看法,這些概念會帶來一些爭論,形成了一種金字塔的模式,永遠都是從塔尖上往下流失。隨著中國一些人購買力變大,藏家來拿這些藝術家的作品的時候,這些藝術家從一開始賣不出去到供不應求,中國的一些畫廊或者藏家拿不到這些炙手可熱的藝術明星的作品時,那么他們就他退而求其次,開始制造自己的“方便面”。
當然,每個畫廊都做這些,但是在這個過程中,要關注在學術上的一個思路是什么,跟時代的關系如何,在藝術語言上的說服力如何。畫廊主導的展覽無所謂好還是壞,還是看每個展覽是怎么做的,什么樣的展覽,推出什么樣的作品。每個展覽都有區別。我覺得好多展覽就是一個Party,連促銷都算不上。
《藝術與投資》:不知道有沒有人會忽略川美畫派的成長和策展人之間的關系。90年代后成名的藝術家也得益于策展人所策劃的重要展覽,這就繞過了以前官方展覽的渠道。策展人策劃的展覽對藝術家有度量作用,但不一定都能起到好的效果,盡管新一代的“卡通”定位遭到質疑,但又不可否認地影響到川美在校學生的“卡通創作”。
葉永青:“卡通”只是一種資源,一個人用不用“卡通”是他自己的事,就像過去的一個藝術家采不采用政治的符號一樣,這是他對時代的一種感覺。中國70年代后出生的這些人真是完全不同的一代人,在整個近代史里,中國從沒有這么長時間的經濟持續增長的太平盛世,他們是真正趕上全球化的一代。我的女兒也學藝術,她去年參加上海雙年展,我做上海的“Moca”展覽,我覺得我們所經歷的這一切,對他們幫助很少,基本上我們各自走在不同的路上,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東西。
葉永青:川美確實是建立了一個很好的傳統,有一種大家都很努力的良好風氣。川美主打的都是架上的繪畫,這主觀上會讓一些畫廊覺得這里面有機會;還有川美許多藝術家畫的品相比較正,容易被市場接受,但價格不一定等于真正的創造力。四川人頭腦比較活,容易調整,四川人之間互相有一種氛圍,我以前一直就想做一個展覽叫做“身邊的氣息”,他們不是靠著對歷史的領悟、文化上的判斷力,他們甚至很本能地靠聞著身邊人的味道就可以生存。
大家的競爭是那種短兵相接的、非常較勁的競爭,你賣一張畫,我要賣兩張畫。畫廊最早來四川美院是90年代中期,那時候我們都還很窮,大家都沒有什么機會。當時我跟張曉剛還在重慶,何森、陳文波、忻海洲他們都散居在重慶的各個地方。畫廊、收藏家、批評家不管是來看我也好,看張曉剛也好,我們都希望能給他們一個意外驚喜,讓他們還能看到其他人的優秀作品。后來何森、趙能智、陳文波等等,大家都自覺地在黃桷坪周圍租房,這就形成了現在所謂的“黃漂”的一個雛形。
在那樣一個環境下形成的樣板,其實就是每一個藝術家生活、創作的模式,是互相之間的影響造成這樣的東西,大家都在這樣的過程里面長本事,學到新的東西。《藝術與投資》:對于年輕的川美藝術家來說,特別是剛來北京不久的年輕藝術家,川美龐大的人際資源無形是給他們許多便利,那他們目前最大的困難又在哪呢?葉永青:困難就是能否找到適合他們干的事情,不是所有人都要靠出賣自己的藝術為生。
我沒法回答一個人怎么樣利用藝術來建立為自己安身立命的職業,這是運氣或機遇的問題,但每個人應該問問自己的內心是不是要做藝術,如果真的做這個不開心,那就可以換別的行業。《藝術與投資》:我想提一下“川美”這個創作群體里的另一部分人,就是那些不是市場炒點的做裝置和影像等等其他非架上媒介的藝術家。基金會對于他們來說目前顯得要更為重要,他們的收入渠道要比做架上的藝術家窄,特別是留守重慶的藝術家。
您覺得基金會目前能介入到這個市場中來,給那些身處資源匱乏地區的藝術家提供幫助有哪些可行條件和制約因素?葉永青:每個基金會的目的是不一樣的,西方的大多數基金會都是非盈利的,可以幫助藝術家提供一些條件,但不負責把藝術家推到市場,基金會也不操作市場。在西方有一些藝術家是終生都沒有進入市場的,他們可以在世界各地做展覽,做各種各樣的活動,他們的辦法就是去基金會申請到創作經費和到世界各地進行創作的條件。這些是西方的機制能提供的。
我們中國目前來說從“昆明創庫”到現在,北京很多人在做盈利空間和非盈利空間的可能性中不斷嘗試。從川美本身來說,恰恰就是看起來人才濟濟,但其實是在價值觀上比較單調的一個創作群體。衡量這個創作群體的標準比較原始,就是參照身邊的成功范例作為標桿,獨立性相對較少。《藝術與投資》:藝術園區是近幾年來各地都熱衷的話題,川美所在的黃桷坪街也建起了藝術一條街,但仍然無法與自然形成的798、莫干山路相比,總的來說就是生產力不足,關鍵還是吸引力的問題,這也是為什么很多人都說川美是原材料基地,加工都在北京、上海,這種過度集中會造成怎樣的結果?
會拉大四川、重慶和北京、上海藝術資源的貧富差距嗎?葉永青:全世界都是這樣的。一個中心城市的興起必然是以別的城市的衰落為代價的,非洲種出咖啡豆,跟星巴克里賣的咖啡是兩回事。四川出來的這批藝術家不可避免地要融入全球化和今天這樣一個大的格局里面,這些藝術家以后也不會把自己局限為四川畫派的一員。我想沒有藝術家會這樣去包裝自己,但是因為商家或者畫廊有這樣的訴求去誘導消費者,無非是因為這里面產生了一些名牌和一些經濟上的效益。
《藝術與投資》:我記得您策劃過“貴陽雙年展”,重慶、成都、昆明、貴陽四個西南城市參與進來,這些城市的資源相對少一些,您覺得它們扮演什么樣的角色?葉永青:世界上所有被強勢的文化或強勢的城市壓抑的地區到一定程度的時候會出現反彈,這些反彈往往都會發生在經濟上、文化上或者在藝術上弱勢的城市。全世界最需要雙年展的是什么地方,絕對不是紐約,不是東京,也不是巴黎,一定是二級城市或者叫在文化上的二手城市,重慶就是一個二手城市,成都也是,他們永遠都在吃別人吃剩下的東西。
但不代表這些城市沒有創造力,不代表它們沒有自己文化的性格和激情,但它們要知道怎么樣去創造屬于它們自己能夠玩的模式,而不是跟在上海和北京后面亦步亦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