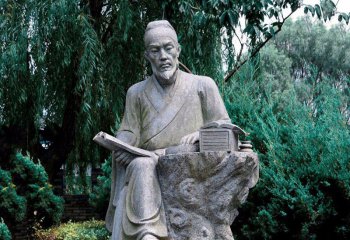在當代藝術(shù)的洶涌大潮中,符號被挪用已經(jīng)是尋常手段。尤其是對文革這樣一段特殊的歷史時期的“符號”挪用,被越來越多的后來者大快朵頤的挪來挪去,已經(jīng)到了信手拈來為我所用的程度。自80年代末開始,人們重新認識中國的時候,發(fā)現(xiàn)直接挪用的方式更為有效。也就是和中國自身的文化、形象發(fā)生關(guān)聯(lián),用平面化、平涂化的手法來表現(xiàn)商業(yè)化和物質(zhì)化對人的精神性的消解。不管是文革符號的重新利用還是把中國人畫的很丑的現(xiàn)象都是文化與社會現(xiàn)實博弈的結(jié)果。

早期從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開始從現(xiàn)代主義、后古典轉(zhuǎn)向?qū)χ袊F(xiàn)狀的具體的認識、表現(xiàn)的藝術(shù)家們,是基于對現(xiàn)實與文化的敏銳思考而產(chǎn)生的,是具有開創(chuàng)性價值和意義的。后來的加入者其中有很多是非創(chuàng)造性、沒有創(chuàng)造力的作品往往是膚淺和蒼白無力的。而這樣一種藝術(shù)現(xiàn)象是怎樣的一個過程和意義呢?

恰好2008年8月2日程昕東國際當代藝術(shù)空間舉辦“當代·紅光亮”藝術(shù)展正是對這一藝術(shù)現(xiàn)象的梳理和呈現(xiàn)。故此我訪問了這次展覽的策展人高嶺博士。裴剛:“當代·紅光亮”的這個題目是怎樣形成的?您一直在關(guān)注中國當代藝術(shù)中的藝術(shù)現(xiàn)象,并做出梳理呈現(xià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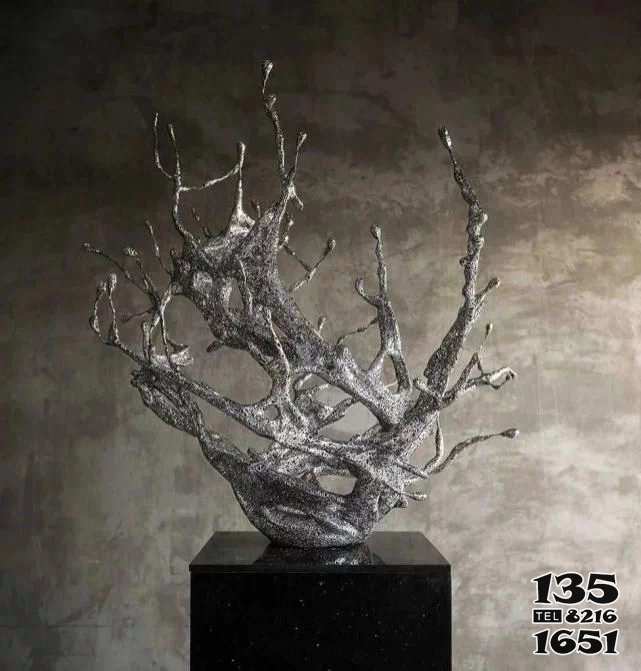
比如上一次的展覽標題是“黑白灰——一種主動的文化選擇”。裴:“黑白灰”或者“紅光亮”他們之間有什么關(guān)聯(lián)?或者這樣的藝術(shù)現(xiàn)象背后的意義是怎樣的?高:我覺得它們是互相對應的一個范疇。“黑白灰”,我們從印象中理解黑白灰就是冷靜、理性、中性,從心理上是往后退了一個色調(diào),給人的感覺是這樣的。“當代·紅光亮”這個概念顯然是一個火熱、熱烈,積極進取的,它是往前進半步,黑白灰是往后退半步。“當代·紅光亮”表述的是當代的現(xiàn)實生活。

我們有時候說是五光十色、光怪陸離,這個其實就有色彩感在里面。如果從色彩和造型上講,這里面有一些很強烈的東西。今天的社會現(xiàn)實,遠遠不是毛澤東時代的社會現(xiàn)實,毛澤東時代的社會現(xiàn)實中的紅光亮是精神層面的。是自上而下營造出來的。而今天當代的紅光亮首先是一個視覺層面。

表述了今天的物質(zhì)化、商業(yè)化、物質(zhì)極大的豐富、各種廣告、商品以及物質(zhì)化的東西。物質(zhì)化景觀的豐富性遠遠要超過毛澤東時代的百倍、千倍。在這樣的時代,它的光怪陸離和五光十色如何來表現(xiàn)?我覺得內(nèi)在的色彩感受藝術(shù)家把握住了,這種色彩感受和毛澤東時代有一種內(nèi)在的聯(lián)系。
這種聯(lián)系有兩方面:一方面是物質(zhì)景觀本身帶有這樣的一種色彩。另一方面,社會的政治體制與物質(zhì)化景觀的關(guān)系。這種光怪陸離和五光十色的景觀是經(jīng)濟機制、市場機制造成的。但是政治體制和社會的政治基礎(chǔ),依然跟毛澤東時代有太多的聯(lián)系。所以這兩方面整合在一起的時候,會產(chǎn)生什么樣的藝術(shù)作品?這是需要提煉的,需要挖掘的。我們可以看到,從藝術(shù)作品來講。
王廣義的大批判系列作品已經(jīng)有整整20年創(chuàng)作歷程,他88年就開始思考毛澤東的大批判。他早期作品在毛澤東標準像上打格子,這個題材顯然不是王廣義發(fā)明的,天安門等一些地方到處都是毛澤東標準像。他為什么把這個圖像直接用到他的作品里來呢?在西方當代藝術(shù)中有一個重要的藝術(shù)批評概念,或者是藝術(shù)批評對藝術(shù)創(chuàng)作做一個總結(jié)的概念是——“搬用”。
“搬用”和“借用”有區(qū)別,這個詞我們推敲了很長時間,“搬用”和“借用”不一樣,因為“借用”這個詞是有借有還的意思,還有所顧忌。“搬用”是毫不顧忌的,搬用是很主動的。而且理由好像很充分。我就拿來,拿來以后就用了,不考慮你的感受。搬用是不考慮要往回還的。
王廣義作為藝術(shù)家肯定不知道搬用這個概念,但是他用藝術(shù)家的直覺,在20年前就感覺到這個東西能夠更有力地表達當時他的一種思考。因為王廣義在“搬用”之前,他畫了很多后古典系列作品。后古典系列都是借西方藝術(shù)史的一些形象,但是他又大量的改造了。不像現(xiàn)在的面貌,僅僅是添加,幾乎不加改造。
他覺得自己以往過多的追慕名畫,追慕西方藝術(shù)的東西,不能夠有力地、準確地表現(xiàn)當時他對文化的一種認識。他認為中國的藝術(shù)應該需要有文化的針對性,所以他在調(diào)整自己。他認為什么是最有文化針對性的呢?當時已經(jīng)開始有市場、商品這些信息。另一方面,社會的整體思維模式,社會的政治制度還是毛澤東時代的體制,這兩樣東西的碰撞,只有搬用這樣的題材更為有力。
當時就有很多人說王廣義是制造噱頭。但今天看來,我覺得是非常理性的。從此,他認為這個東西最符合中國的現(xiàn)實,最有文化的批判性和針對性。裴:他還是很理性的,并不是一種沖動。高:從那兒以后,我們可以看到很多藝術(shù)家都開始注意到毛澤東時代的美術(shù)視覺圖像、視覺資源可以被使用,并成為一種藝術(shù)。當時隨著王廣義越來越被認可,隨著藝術(shù)市場越來越好,我們可以看到今天有多少人在使用這樣的方式。
今天很多藝術(shù)家在使用這些視覺圖像,已經(jīng)有很多人都是因王廣義作品中的語言形式而受到啟發(fā)和影響的。這些藝術(shù)家對這種“搬用”加以吸收和改造。比如俸正杰十前年就開始,他的作品是一步一步演變的。但是現(xiàn)在,如果再有人從他這里受到啟發(fā),再進行類似的創(chuàng)作就遠不如俸正杰。當然俸正杰、王廣義是“搬用”但是搬用只能一次,在進行類似的行為就顯然是抄襲了。
我們說杜尚的《小便池》,“搬用”的概念最直接的就是杜尚的《小便池》。《小便池》只有杜尚一個人去搬到美術(shù)館里面,這就是作品。但是如果杜尚之后還有人再搞“小便池”顯然就是抄襲。所以,我們今天講“當代紅光亮”的概念,這里面存在著一個很大的問題。
在很早的時候,二十年前是有這樣一個邏輯背景的。但是搬用以后,王廣義是整體“搬用”大批判的圖像。當他后來知道“文革”的美術(shù)資源可以借用、可以搬用,就有吸收、有改造、有組合、甚至還有再生出來的。像岳敏君這張畫《我為祖國放駿馬》,廣庭渤的《我為祖國放駿馬》原畫是有牧民在上面的,岳敏君把這個人去掉了,盡量追求那種那個時代的繪畫語言、包括感受和技巧,畫面整個追求過去的那種東西。
所以,你說這張畫跟過去之間究竟是什么關(guān)系?岳敏君十年前畫過《開國大典》,也是沒有人。我覺得岳敏君的東西都能很形象地說明這個問題。但是如果現(xiàn)在的人再來畫這個東西,以后肯定會有人畫,當然也是很好的。但是我們講這個展覽里面的十位藝術(shù)家,都是很早就開始堅持自己的探索。所以,我選擇了這樣十位藝術(shù)家。
裴:這里面有一個問題,當時在毛澤東時代的政體和經(jīng)濟是一體的。他的方法論、思想和形象整個是一體化的,是完善的而不是分裂的。由于這種“一體化”,它既區(qū)別于西方,也區(qū)別于中國的傳統(tǒng)。包括經(jīng)濟是計劃經(jīng)濟,但是今天的現(xiàn)實是在市場經(jīng)濟下。今天市場經(jīng)濟在今天的政治體制下和過去比較而言是不同的,或者說已經(jīng)不是那么一體化的。
在這種情況下,藝術(shù)上仍然會有所謂“紅光亮”的這種情結(jié)。裴:它們之間的承接關(guān)系,或者是在文化上的啟示又是什么?是不是有這樣一種意義?高:啟示是這樣的。作為一種視覺經(jīng)驗,它可以有一種延續(xù)性。比如時代不同了,但并不是簡單地講一個時代的藝術(shù),一定是這個時代社會現(xiàn)實的反映。這種反映,并不是直接的像鏡子似的反映。
而是反映歷史里面的一些現(xiàn)象,如何反映歷史?如何繼承和發(fā)展?在反映的時候必須是剛剛過去的歷史、剛剛過去的經(jīng)驗,而且這種歷史經(jīng)驗一定要對這個藝術(shù)家起到作用。20年前,1988年的時候。文化大革命剛剛結(jié)束十二、三年,雖然80年代是思想解放的開始,但是依然有很多東西都仍然向文革時期的方向發(fā)展。思想解放只是停留在中國政治界的高層和知識界的知識分子的思想解放。在普通的機關(guān)、企業(yè)、工廠、農(nóng)村完全是毛澤東時代意識形態(tài)。
92年鄧小平南巡以后要搞市場經(jīng)濟。在這樣一個社會體制里面,又開始要市場化。就會產(chǎn)生巨大的反差。所以他必然要用自己熟悉的、曾經(jīng)有過的經(jīng)歷和視覺經(jīng)驗與當下經(jīng)驗做一個混合。藝術(shù)作品一般都是這樣的。所以,這個展覽我想強調(diào)一點。“當代·紅光亮”這個展覽是帶有藝術(shù)史性的展覽,是帶有回顧性和總結(jié)性的展覽。它是從藝術(shù)批評的角度重新提煉1990年到今天,18年來中國當代藝術(shù)中一個重要的現(xiàn)象。
在藝術(shù)家創(chuàng)作出藝術(shù)作品后,就是藝術(shù)理論和藝術(shù)批評工作者怎么來梳理和闡釋的問題。它是一個開放的結(jié)果。如何闡釋?找到什么樣的角度來闡釋?這是非常重要的。大家都知道一個理論最有效的就是概念、范疇、命題,沒有這些東西,這個理論就不成立。所以在命題、概念、范疇里面,我覺得“當代紅光亮”和“黑白灰”是一樣的,它是一個概念,它是一種新的概念。為什么叫“當代·紅光亮”?
如果“紅光亮”是“文革時期”的一個概念,我們今天應該重新再造一個概念。但是在中國這樣的特殊現(xiàn)實里,重新造一個概念不如直接搬用。我在文字上也學了王廣義直接搬用。但是我加了一個“分號”,表示方法就是“當代·紅光亮”。
這在西方學界是兩種概念的互文性,英文叫Intertextuality,又翻譯成文本間性。兩個不同時空的概念同時并置在一起的時候,它們可以產(chǎn)生互相之間、今天與過去之間的關(guān)系。今天的不完全是今天的,它是從過去來的。比如“當代·紅光亮”,當代和紅光亮之間產(chǎn)生一種互相對照性。語言學家羅蘭·巴特把它提煉得特別好,也就是他們之間有一種互生性。所以“當代·紅光亮”有一個并置的概念在里面,它產(chǎn)生了新的概念。比如王廣義的作品《大批判》,把popart和可口可樂并置在一起,這說明了什么?
以過去的經(jīng)驗會覺得這個東西毫無路數(shù),屬于無厘頭。比如像無厘頭,像周星馳的港臺電影里面就有很多并置的元素,是超時空的并置。后現(xiàn)代藝術(shù)里面有很大一塊就是文化的并置,是互文性的關(guān)系。所以,如果說王廣義是在視覺藝術(shù)的形式上搬用了過去的圖像,我在文字上也搬用了過去的圖像,與當代的語境做了一種并置。這個比我再去找三個新的字做一個概念,更容易使人們進入和理解,更能夠體驗到對于這些藝術(shù)家作品真實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