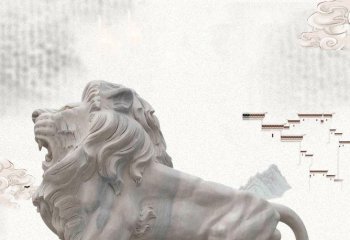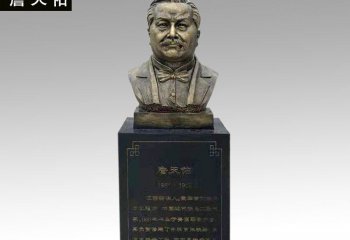劉禮賓:這次訪談將沿兩條線索展開,一是以當(dāng)代藝術(shù)的發(fā)展為線索,二是以你的收藏為線索。我們會涉及作為收藏家的你對當(dāng)代藝術(shù)的理解和把握,對個體藝術(shù)家創(chuàng)作的關(guān)注,你的收藏理念以及你對當(dāng)代藝術(shù)史的認(rèn)識。伍時雄:訪談圍繞一個全方位對中國當(dāng)代藝術(shù)史的理解來探討藝術(shù)收藏理念,這種角度比較貼切,我作為所謂的“收藏家”去收藏一批當(dāng)代藝術(shù)作品,卻不需要征詢別人的意見,是因為我了解“85美術(shù)思潮”的發(fā)展過程,并參加了“85美術(shù)思潮”,從“星星畫會”的藝術(shù)家和朦朧詩人,到“四月影會”的藝術(shù)家,在當(dāng)時不少是我的朋友,也曾一起共事。

伍:對,那時候走得比較近。他們到廣州,其中一些朋友會住在我家,當(dāng)時我在中山大學(xué)、華南師大、廣州美術(shù)學(xué)院及省博物館舉辦關(guān)于“世界藝術(shù)攝影的意識與形態(tài)”的學(xué)術(shù)講座,同時也為北京來的藝術(shù)家安排講座。當(dāng)時梁明誠是一位十分敏銳的著名雕塑家,是我的前輩了,當(dāng)他騎著單車老遠(yuǎn)的來聽我和馬德升的講座時,我是十分感動的,他覺得從中可以感受到比較清新而真切的思想。期間與星星畫會馬徳升、嚴(yán)力和黃銳,朦朧詩人芒克、歐陽江河和音樂家候德健,四月影會王志平、王苗和李曉斌等都有聯(lián)系。

伍:我在廣東省工藝美術(shù)研究所當(dāng)研究員。“四人幫”在位的時候,我開始偷偷閱讀“世界美術(shù)史”。北京天文館有一位非常著名的教授,叫李元,1973年的時候,我從他家借了一本民國時期出版的《西方美術(shù)史》,上面已經(jīng)介紹到了后期印象派及畢加索等藝術(shù)家,在還書之前,我把整本書給抄了,因此對西方文藝復(fù)興以來的西方藝術(shù)流派有了一個較系統(tǒng)的了解。劉:在國內(nèi)較早接觸到新鮮東西,可能與周邊同行的知識結(jié)構(gòu)相比,開始有所不同。那你具體做什么藝術(shù)創(chuàng)作呢?

伍:當(dāng)時主要從事藝術(shù)攝影,其實也是從美術(shù)史的角度切入的。我把西方19世紀(jì)末一直到現(xiàn)代主義運動的攝影流派與當(dāng)時的美術(shù)流派的發(fā)展理論結(jié)合起來進(jìn)行思考,使我積累了一定的史論基礎(chǔ)。當(dāng)時很努力地向海外朋友尋求境外出版的藝術(shù)書刊,這類書在國內(nèi)的圖書館根本借不到,向私人借也十分稀罕。你想看西方的美術(shù)史,在國內(nèi)簡直是沒有渠道可以挖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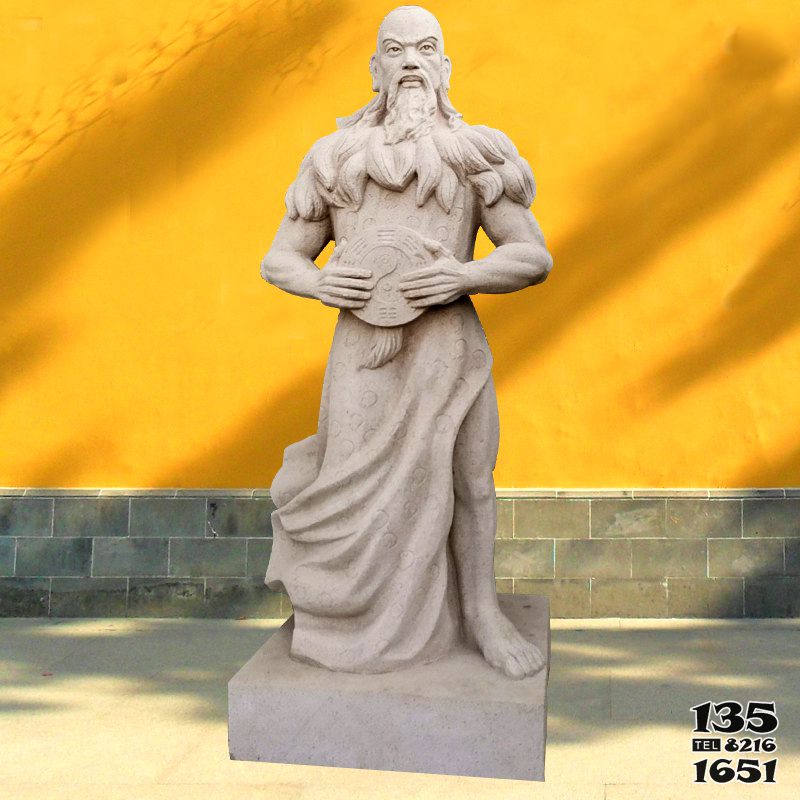
伍:我有幸讀到那些書,收益挺大,1970年在就讀廣州美術(shù)學(xué)院期間,我與香港和巴黎的朋友一直都有私下書信來往,他們常常會寄一些國外藝術(shù)新聞剪報和畫冊過來但無一例外這些郵件都要接受中國海關(guān)拆封檢查。伍:他們知道我關(guān)注這方面的信息,國內(nèi)很缺乏,他們很樂意幫助我。伍:早在1971年就開始了。

西方現(xiàn)代藝術(shù)資料看多了,對后來“85美術(shù)思潮”的崛起就不覺得奇怪了。1980年,我第一件現(xiàn)代觀念的作品《青與蘭》已在日本東京都美術(shù)館《亞洲現(xiàn)代美術(shù)展》上展覽了。1983年,我感覺中國會重復(fù)走一段西方現(xiàn)代主義的藝術(shù)歷程,后來出現(xiàn)的“85美術(shù)思潮”也是必然的。記得在“85美術(shù)思潮”珠海會議上,陶詠白老師做過一個專題講座,對上世紀(jì)三四十年代的很多中國現(xiàn)代主義畫家,如龐薰琴、倪怡德等一大批從西方留學(xué)回來的藝術(shù)家做了詳細(xì)的介紹。她說:“其實在中國出現(xiàn)現(xiàn)代主義作品并不是從1985才開始,早在30年代就開始了。
”我認(rèn)為歷史背景不太一樣,那時候現(xiàn)代藝術(shù)處于極少數(shù)萌芽之弱勢狀態(tài),受到舊中國頑固的封建文化勢力的壓制,欣賞和認(rèn)可的人極少,未成氣侯。到了1980年代,中國現(xiàn)代藝術(shù)面對的不僅是封建意識殘余,更多的是來自政治意識形態(tài)的壓力,但涉及的社會群體已相當(dāng)廣泛。伍:“糾纏不清”一直是非常時期的主要特征。
陶詠白老師提醒年輕的與會者,三十年代已經(jīng)有人開始在中國做了很多現(xiàn)代派的探索。由于自己對現(xiàn)代藝術(shù)史與國際背景有所認(rèn)知,在看待“85美術(shù)思潮”時就沒有那種純感性的狂熱,反倒持比較理性的態(tài)度和立場,我認(rèn)為運動歸運動,藝術(shù)最終還是會回到本體上來的。在珠海會議上針對當(dāng)時政治時局的局限性和發(fā)展的可能性,我作了一個題為“群體必然會消亡,藝術(shù)終歸回到個體”的發(fā)言,高名潞當(dāng)時雖然把我的文稿也收集了,但我的觀點被“靠邊”已是意料中事。
王川私下對我說:“老伍,您找錯地方說錯話了。”可我不以為然。伍:這是當(dāng)時的一種文化政策所造成的歷史現(xiàn)象,如果當(dāng)時的文化政策造成了一種政治運動,那么抗衡它的運動同樣是一種政治運動,此時只有群體才能聚集和釋放能量。劉:二元對立思維在發(fā)揮作用,正反方的行事方式以及思維模式是一樣的。伍:當(dāng)政治矛盾最激化的時候,藝術(shù)創(chuàng)作很難體現(xiàn)個體對藝術(shù)的看法和追求。
自由的創(chuàng)作權(quán)利沒有得到解決的話,創(chuàng)作又如何能夠體現(xiàn)個性化的追求?不過那時有《中國美術(shù)報》等雜志,還有“85美術(shù)思潮”的群體推動,所以我覺得已經(jīng)開始打破禁錮。1986年的珠海會議,事實上是借助珠海畫院的一筆經(jīng)費,移花接木地做了一個“85新潮幻燈片展及學(xué)術(shù)研討會”,這是一次成功的策劃,但在這個會議上發(fā)生的一些現(xiàn)象卻又使我感到疑惑與納悶。伍:當(dāng)時全國各地的前衛(wèi)藝術(shù)家和群體已經(jīng)“登臺”了,運動仍需推進(jìn),還沒到塵埃落定的時候,珠海會議上有人就已經(jīng)開始產(chǎn)生要排座次的訴求了。
這個時候某些人看到時機(jī)來了,借主持的話語權(quán),迫不及待想確定自身的江湖地位,在全國巡回幻燈展評選時,私下布局是有預(yù)謀的,身不由己的我也成了當(dāng)事人之一,心里非常清楚。伍:大會預(yù)備會議我沒參加,關(guān)于“85美術(shù)思潮”全國巡回幻燈展評選預(yù)備會我參加了,會議給與會人打了個招呼:示意要把某些地區(qū)的群體或作品排斥在“85美術(shù)思潮”幻燈巡回展入選范圍外,表決時態(tài)度要堅決…
事態(tài)顯然與藝術(shù)完全沒有關(guān)系了,開始蛻變?yōu)橐粋€權(quán)益分配的PK臺,事與愿違地讓我感到有點意外和惡心。因為我覺得藝術(shù)評判不應(yīng)該采用權(quán)術(shù)手段,在利益節(jié)點上,有想當(dāng)“宋江”的人把85精神當(dāng)做敲門磚,讓民主精神倒退了100年,超人哲學(xué)所謂:“謊言說一百遍也能成為歷史”的觀點不止一次被人提起,實在有點忘乎所以了。當(dāng)時被排斥的主要有兩大地區(qū),一個是廣州,另一個是上海。結(jié)果在珠海會議上引發(fā)了地區(qū)與地區(qū)之間激烈的抗?fàn)幣c對罵,給所有與會代表留下了一段令人并非愉快的難忘記憶。
某些藝術(shù)群體在這個語境中占盡了便宜。這里面有很多人為的,由話語權(quán)不均而導(dǎo)致的不公,這個時候誰有話語權(quán),歷史評說就可以改寫了。關(guān)于這一點彭德、曹涌和我私下交流過,都覺得欠妥。伍:1984年《現(xiàn)代攝影》已經(jīng)創(chuàng)辦,這本雜志實際上是隨著矇眬詩人、星星畫會、四月影會等文化大趨勢一起走過來的。伍:當(dāng)時我們在南方,正是利用了深圳在政治上不太敏感的這一地緣特點才有機(jī)會辦前衛(wèi)的學(xué)術(shù)雜志。
還沒有辦這本雜志的時候,我曾在廣州一些院校講“世界藝術(shù)攝影的意識和形態(tài)”專題講座,從形態(tài)出發(fā)來闡述攝影作品的意識與流派,并收集了幾百張幻燈片,把各種流派進(jìn)行歸類與闡釋,為日后辦《現(xiàn)代攝影》雜志積累了一些素材。《現(xiàn)代攝影》雜志發(fā)行后美術(shù)院校訂購的特別多,創(chuàng)刊號再重印了一版,才滿足了需求。
伍:當(dāng)時辦的這本雜志,幾乎成了國內(nèi)攝影界唯一一個可深入了解外部世界的“窗口”。1994年,我在美國三藩市魚人碼頭遇見兩個移民美國的中國畫家,閑聊起來,他們說起:“在美院讀書時,很多同學(xué)就訂你們辦的《現(xiàn)代攝影》…”當(dāng)時很多美術(shù)學(xué)院的學(xué)生愿意看這本雜志,尤其關(guān)注的是其中大量的不同流派的國際圖像信息,同時雜志也為中國年輕攝影家開辟了一片思想開放的前沿陣地。伍:在廣州我花了三個多月參與編輯籌備,當(dāng)時國家規(guī)定成立雜志編輯部必須有一名以上的大學(xué)生,當(dāng)時只有我一個。
等到國家出版總署把刊號批下來以后,深圳市舊文聯(lián)領(lǐng)導(dǎo)卻把我定調(diào)為“創(chuàng)作思想很有問題”的人嚴(yán)加排斥,并決定不讓我進(jìn)入雜志編輯的編制內(nèi),雖然我是創(chuàng)刊人之一,刊物主體結(jié)構(gòu)、欄目和圖片由我編輯,但我的名字不允許出現(xiàn)在編輯名內(nèi),所以我一直沒能領(lǐng)工資卻繼續(xù)去干了三年沒有名份的編輯工作。最后我接受了一個折衷的安排,就是把我安排在深圳市文化局下屬的一個公司。之前我在廣東省工藝美術(shù)研究所的研究員位子挺好的,就是為了創(chuàng)辦這本雜志才移民深圳的,無奈之下為“曲線救國”,也就只好忍辱屈就了。
創(chuàng)刊號出來后,市舊宣傳部長找我談過話:“你們辦雜志應(yīng)重點宣傳深圳的建設(shè)成就…”我反駁說:“那是深圳市圖片社干的事!《現(xiàn)代攝影》應(yīng)當(dāng)辦成全國唯一一本與國際攝影接軌的專業(yè)雜志。”往后種種干擾持續(xù)不斷。1989年全國反對“精神污染”的時期,編輯部壓力很大,主編說不想干了,在一起聊著聊著我們都難過得流下了眼淚。1984年底,王川也曾到我們編輯部工作過。
現(xiàn)在翻開中國現(xiàn)代攝影史,《現(xiàn)代攝影》已被公認(rèn)是中國攝影史的一個里程碑,不堪回首的往事已是過眼云煙隨風(fēng)散去。劉:但重要的是你能做這些事情。你對國際攝影藝術(shù)的熟悉與你辦這本雜志構(gòu)成怎樣一種聯(lián)系?伍:在我們之前有“四月影會”,它的主要爆發(fā)點源自天安門事件的“四五運動”,推動了中國紀(jì)實攝影的發(fā)展,把攝影回歸到對社會形態(tài)真實的記錄以及相對比較人性化的表現(xiàn)層次上。
不再是那種扛著紅旗、打著腰鼓、倡導(dǎo)紅光亮題材類的宣傳照片。我們與全國各地興起的新進(jìn)攝影群體聯(lián)系密切,與國外藝術(shù)家也有聯(lián)系。此時美術(shù)界關(guān)于西方視覺藝術(shù)的信息還相對很少,我通過雜志對國外藝術(shù)流派理論的介紹,引進(jìn)了大量的西方攝影藝術(shù)方面的代表作品。實際上攝影發(fā)展與繪畫發(fā)展是幾乎同步的,從表現(xiàn)主義、超現(xiàn)實主義、新現(xiàn)實主義、抽象主義,到極少主義流派等等,它的產(chǎn)生時間和理論基礎(chǔ)幾乎是同一時期的。伍:與傳統(tǒng)攝影比較,它的觀念是全新的。
很多年輕攝影家開始關(guān)注社會深層的披露,如《瞭望》雜志記者李曉斌作品《上訪者》;視覺探索角度新穎獨特,每位攝影家關(guān)注點都不一樣,日漸顯露出個性追求,傳達(dá)意識比較鮮明,這種氣象是改革開放前所沒有的。2007年第二屆廣東國際攝影雙年展圍繞著一個重要的專題就是——中國攝影史的回顧,展覽上把每個時期的代表作都拿出來進(jìn)行了梳理。策展人有法國蓬皮杜藝術(shù)中心主任阿蘭·薩亞格先生和香港理工大學(xué)教授馮漢紀(jì)先生等。雙年展前言寫道:“…
在80年代的中國,出于對景物攝影主流的逆反以及對撲面而來的西方現(xiàn)代主義思潮的匆忙回應(yīng),伍時雄、凌飛和鮑昆被列為中國攝影界代表了國內(nèi)少數(shù)藝術(shù)家,集結(jié)在語義模糊的‘現(xiàn)代主義’旗幟下,發(fā)起了‘更純粹的攝影藝術(shù)’試驗,以期重釋攝影的本義,并留下了一批代表作。”伍:開始我從事批判現(xiàn)實主義的創(chuàng)作,后來進(jìn)入意象批判現(xiàn)實主義創(chuàng)作,最后進(jìn)入純視覺藝術(shù)探索,三個階段共有43張作品參加這屆雙年展。《形無意系列》是我的代表作,參加了1989年中國現(xiàn)代藝術(shù)大展,這四件抽象剪貼的攝影作品把一些微觀的物質(zhì)形態(tài),根據(jù)視覺感覺重新組合而成。
作品從抽象的角度試圖喚醒人們本能的純視覺感應(yīng),而不要被固有的視覺慣性和經(jīng)驗所壓垮。我從來不是中國攝影家協(xié)會會員,1988年中國攝影家協(xié)會在上海召開全國攝影理論研討會上公開點名對我進(jìn)行批判,夠抬舉我了。可笑的是,1989年中國攝影家協(xié)會在京舉辦“紀(jì)念世界攝影術(shù)發(fā)明100周年中國藝術(shù)攝影展”時,該會卻派人到中國美術(shù)館偷走了我參加“中國現(xiàn)代藝術(shù)展”的作品《形無意系列》,掛在“中國藝術(shù)攝影展”上,以此向國際顯示中國也有抽象攝影藝術(shù),夠國際化了吧!
夠百花齊放了吧!三個月后,有人送來畫冊時我才知道騙展的事。過后我被中國美術(shù)館倉管部門告知:《形無意系列》原作已丟失。2006年嘉德拍賣行有意征集這組原作,我把原委告訴了劉剛先生,并表示我沒有復(fù)制的意欲。劉剛說:“此事太荒唐了!”伍:1982年與安哥等人成立了廣州第一個最前衛(wèi)的攝影組織“人人影會”,舉辦過三屆藝術(shù)展,在社會與大學(xué)生群體中引起了強烈反響;我的作品《卵石》成了建國以來第一張被公開展出的人體照。
“85”時期適逢各地成立藝術(shù)群體,在深圳與王川等一起成立了“0”展群體,因得不到主流社會的支持,只好在街頭路邊舉辦“0”展,并作為南方的藝術(shù)群體之一被載入“85美術(shù)運動”史冊中。1986年,珠海會議前我們還成立了一個名為“中國特區(qū)藝術(shù)家聯(lián)盟”的組織,并印刷過“宣言”四處散發(fā)。伍:王廣義是主席,我是秘書長。這是基于中國經(jīng)濟(jì)特區(qū)地域建立的一個前衛(wèi)藝術(shù)組織,顧問都是全國的當(dāng)代藝評家。
當(dāng)年珠海市市長在珠海市政府會議上發(fā)話:“珠海市有少數(shù)幾個畫家和深圳幾個畫家建立了一個非法組織,我們必須要取締這個組織。”迫于公安條例,最后我們也沒有了存活的空間。伍:85時期珠海舉辦過兩個重要會議。一個是1986年的“85美術(shù)思潮”珠海會議,一個是1987年的“中國攝影趨勢研討會”,我都是以藝術(shù)家身份參加的。伍:這個時候大家已經(jīng)是朋友了,大家一起在深圳與珠海之間做事,都很有激情。伍:當(dāng)時真不知道他為什么去珠海畫院工作。因為我在藝術(shù)上一直不看好南方。
他從東北往珠海跑,我覺得很奇怪,因為這里的氛圍根本不適合搞當(dāng)代藝術(shù)。但據(jù)我理解,當(dāng)時很多人急于去找一個工作與生活環(huán)境好點和較開放的地方。反正搞藝術(shù)也不是靠當(dāng)?shù)氐馁Y源,我從這個角度能理解他。他最后離開南方,我覺得也是必然的。他1991年左右走的。
我的“世紀(jì)末藝術(shù)工作室”成立于1990年,當(dāng)時就收藏了他的油畫《玩偶一號》。伍:同時收藏了一批作品,他的作品是其中之一,那時候我還沒有真正花大錢去做收藏。因為那時候我自己也在從事創(chuàng)作,并沒有投資收藏的意識。到了1991年、1992年的時候,因為從事了幾年設(shè)計,手頭有點資金,又成立了“世紀(jì)末藝術(shù)工作室”,想通過工作室在深圳推動現(xiàn)代藝術(shù),于是開始收集現(xiàn)代藝術(shù)品。甘少誠先生在我的藝術(shù)工作室創(chuàng)作了一年,五十多件雕塑遺作因此被收藏了。少誠兄也是星星畫會的成員,1996年于香山因車禍離世,同年在中國美術(shù)館我們?yōu)樗e辦了《甘少誠遺作展》,2008年為紀(jì)念老甘,我在荷蘭作了一件大型木雕作品《戰(zhàn)士》,已被荷蘭藝術(shù)基金會收藏。
甘少誠的作品在我的工作室占了很大的比重,在這里是看不到傳統(tǒng)繪畫的,沒有“風(fēng)花雪月”一類的東西,這表明了自己對當(dāng)代藝術(shù)的一種立場和態(tài)度,喜歡“當(dāng)代”的品質(zhì)與感覺。那時候我忙于設(shè)計事業(yè),沒有什么機(jī)會搞藝術(shù)創(chuàng)作,只想通過收藏這種方式抒發(fā)我的關(guān)注點,在自己的環(huán)境里隨時能看到這些優(yōu)秀作品,可算是對當(dāng)代藝術(shù)情結(jié)的一種填充,有可能的話還想辦一個私立美術(shù)館。
伍:1987年參加珠海“中國攝影趨勢研討會”后,一回到深圳我就辭掉了公職。我當(dāng)時是第一批考進(jìn)特區(qū)的國家干部,然后又成了第一批下海的體制內(nèi)干部。伍:1983年,在廣州舉辦過一個來自舊金山的“美國何鉄華禪畫藝術(shù)展”。通過翻譯我與美國的這批藝術(shù)家聊了4個小時,談到“藝術(shù)與生活”的關(guān)系,有位藝術(shù)家的禪畫抽象難懂,做市場更難,我特意問他怎么解決藝術(shù)與生存的關(guān)系,他說:“沒有關(guān)系,畫畫不是為了生存,在生活中,我的工作就像普通工人一樣什么都干,上半年賺來的錢夠下半年藝術(shù)活動用…”這次對話很重要,很大程度上影響到我以后的生活態(tài)度。
我決定重新安排自己的人生時間表,先解決生存問題,后解決藝術(shù)發(fā)展問題。那時候我和“禪宗”有過一次接觸。1982年,為恢復(fù)廣東鼎湖山的一個明代寺廟,我負(fù)責(zé)畫壁畫,真人大小一共畫24個人物,名叫“二十四諸天”。整體構(gòu)圖我負(fù)責(zé),然后由四個人用工筆重彩的方法去完成,為此我們在寺廟里生活了三個月。
伍:算是個居士吧。1982年,我到九華山寫生,不自覺地皈依了佛法。因為年輕的時候比較好奇,有天傍晚,太陽已經(jīng)下山了,我還在百歲宮寫生,主持方丈對我說:“你應(yīng)該是有佛緣之人,有悟性,我收你當(dāng)徒弟吧!”我半開玩笑地答應(yīng)了。然后他說你得做個儀式,于是我五體投地,在“真身”面前跪拜,方丈從柜子里拿出明代用血書寫的“血經(jīng)”,在我頭上敲了三下,敲得我心驚膽戰(zhàn),他給我起了個法名,在供臺上拿下一個供果給我吃,這樣就算是收徒弟了。當(dāng)時我還竊笑作弄了主持方丈。
但有緣的是我當(dāng)年就參與了修復(fù)鼎湖山慶云寺佛教藝術(shù)的工作,造訪了北京廣濟(jì)寺中國佛教協(xié)會和法源寺法學(xué)院收集文獻(xiàn),考察了云崗石窟和龍門石窟,在寺廟里修復(fù)佛教藝術(shù)品,開始對佛教有了一些認(rèn)識,在理論上受六祖慧能禪宗的影響很深,心態(tài)上也做了很多的調(diào)整,開始禪化。
這還是1982年的時候,是“85美術(shù)思潮”之前的經(jīng)歷。1985年我還協(xié)助朱青生先生出版了日本鈴木大拙關(guān)于禪學(xué)的論著《禪·西方的黎明》一書。劉:所以到了“85美術(shù)思潮”的時候,你的心態(tài)和“85的英雄們”還有些不一樣。伍:是有點不一樣,心里寧靜些。在藝術(shù)家之間相比而言,我更喜歡朦朧詩人、星星畫會、四月影會這撥人,他們的創(chuàng)作比85思潮還早,他們的思想表述更接近一種真知。像馬德升,隨時找個餐館,就能跳在桌子上演說,看似有點神經(jīng)質(zhì),其實很真誠,我骨子里面很敬重真誠。
伍:我去過美國以后,覺得人生應(yīng)該有一個“時間表”。先入世做“人下人”,后出世行“大智慧”,人格獨立不是一句空話。我比較認(rèn)可“自救”,最后徹底選擇自謀生路,不受別人牽制,愿意怎么樣就怎么樣。我也相信自己有能力活得比體制內(nèi)更自在。自從深圳市文化局下屬公司出走以后,我一年的產(chǎn)值相當(dāng)于原公司60個人的總產(chǎn)值,體制內(nèi)很多人似乎是白活了,所以我相信脫離體制是對的。
憑著自己的能力,通過做設(shè)計、出版和策劃工作,進(jìn)行艱苦創(chuàng)業(yè)。剛下海時,我除了交一年的房租,口袋里就只剩下一千元錢了,當(dāng)時一家人在特區(qū)生活,其艱難和風(fēng)險可想而知的。伍:不“舍”又何“得”呢!我要的是自由,這樣抉擇會令人生目標(biāo)加快。與其說在一個單位賴著干,然后又偷偷干自己的事情,反倒不如光明正大地自己干!這種風(fēng)險是值得去冒的。下海前,在單位很多人羨慕我被提拔為副總,適逢分房,我的評分最高,結(jié)果在要分房的那個關(guān)鍵時刻,我遞了辭職信,當(dāng)時全公司的人都傻了:覺得在單位打拼了3年,才熬到文化局建好四室二廳的房子隨即到手,竟然說不要,要去單干,太瘋了!
伍:對,當(dāng)時在公司我算是年輕的,才30多歲,公司里面有很多60年代與老總同時畢業(yè)的同班同學(xué)老要老總照顧,但老總偏看重我,待遇比別人都好,可惜這對我沒有意義,因為我不能自主人生。我覺得人生目標(biāo)不論是什么,首先要解決人格獨立的問題。
長痛不如短痛,下決心單干去!劉:單干戶在當(dāng)時不是個光彩的名稱,為了單干你離開了文化局,也離開了《現(xiàn)代攝影》編輯工作,他們怎么看您?伍:體制內(nèi)如何評價倒無所謂了,《現(xiàn)代攝影》的同事看不慣則讓我有點傷心,在《現(xiàn)代攝影》某主編的授意下,一個中新社記者寫了一篇題為《深圳的太陽特別辣》的文章,編造事實把我做個體戶的經(jīng)歷嘲笑了一番。
我認(rèn)為這樣做并不道德,在學(xué)術(shù)雜志上,有不同觀點可以互相批判,雜志是我們共同創(chuàng)辦的,有共同的信仰和立場,曾并肩與保守勢力對抗,應(yīng)是同一戰(zhàn)壕的戰(zhàn)友,我從來不領(lǐng)編輯部一分錢工資,為了生存我當(dāng)了個體戶,看不慣就該在戰(zhàn)友背后插上一刀嗎?
我不理解為什么在嚴(yán)肅的學(xué)術(shù)雜志上拿這些不沾邊的事開涮。三年后這位中新社記者登門道歉了。我說:“這次你不來,我會永遠(yuǎn)不再見你,憑什么去取笑一個幸存者?這跟攝影藝術(shù)有何相干?”劉:1987年以前,你其實已經(jīng)認(rèn)識了很多當(dāng)代藝術(shù)家,在你有實力去收藏的時候,你對當(dāng)代藝術(shù)圈的情況已經(jīng)很了解,這一點與許多現(xiàn)在的藝術(shù)收藏者的經(jīng)歷很不一樣。伍:是的,但我不會只做藝術(shù)創(chuàng)作,好像其他事情都沒有意義。我還喜歡做設(shè)計和策劃方面的事情,但我心里面沒有解脫當(dāng)代藝術(shù)的情結(jié),所以我一直和各地的藝術(shù)朋友保持著暢通的聯(lián)系。
劉:其實你對整個中國當(dāng)代藝術(shù)發(fā)展的脈絡(luò)以及他們的個人狀態(tài)是很了解的,這為你以后做收藏奠定了一定的基礎(chǔ)。伍:我在辦《現(xiàn)代攝影》雜志的時候,接觸到的都是國內(nèi)外當(dāng)代藝術(shù)家。有些國外藝術(shù)家是我通過給他們寫文章在國內(nèi)推介以及做一些學(xué)術(shù)交流活動時認(rèn)識的,都在關(guān)注著新思潮,在藝術(shù)鑒賞方面,我也形成了自己的標(biāo)準(zhǔn)。1990年“世紀(jì)末藝術(shù)工作室”的成立是給當(dāng)代藝術(shù)家提供了一個工作與展示的空間,當(dāng)時成為深圳唯一一個從事當(dāng)代藝術(shù)的工作室,1990年還在深圳博物館舉辦過現(xiàn)代藝術(shù)展。劉: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你不但建立了工作室、還進(jìn)行個人收藏,并頻繁與藝術(shù)家交往,當(dāng)代藝術(shù)在當(dāng)時市場情況如何?
伍:“八五美術(shù)運動”興起時,沒有人談當(dāng)代藝術(shù)收藏,創(chuàng)作的作品都不是為市場而作的,因為誰都沒有想到要“賣作品”這個事情。重點都在高揚自己的思想主張。“八五”以后,西方對中國采取了一種新的文化戰(zhàn)略,這個時候他們開始把“手”伸進(jìn)大陸,試圖借助爭取“人權(quán)與自由”的名義,給中國政府施加壓力。對藝術(shù)家開始采取一種資助態(tài)度,此時西方對有政治傾向的作品顯露出極大的興趣,通過收藏的方式將中國當(dāng)代藝術(shù)逐漸導(dǎo)向西方的價值標(biāo)準(zhǔn)。這種政治預(yù)謀是顯而易見的。易英老師是較早點破此迷局的學(xué)者之一,我們交流過,并非常同意他的觀點。
一旦有了市場,大家就開始考慮賣畫了,這種現(xiàn)象在了1990年代初變得比較明顯。1986年我介紹香港藝術(shù)中心總監(jiān)陳贊云先生與王川結(jié)識,后來陳贊云成了漢雅軒畫廊的總監(jiān),1987年之后張頌仁先生就把王川代理了,在全國都有零零散散的同類現(xiàn)象。“星星畫會”后期,藝術(shù)家也開始與西方收藏者合作,雖然那時作品的價格都非常便宜,但是被松動了藝術(shù)目標(biāo)開始向市場漂移。伍:大部分成員都到國外去了,再沒有集群活動,該成歷史者便成歷史。我手頭上還有他們的木刻版畫和手刻蠟版印制的“地下詩集”。劉:你收藏當(dāng)代藝術(shù),一方面,是表達(dá)你對于當(dāng)代藝術(shù)的一種立場和喜愛,另一方面,你有沒有考慮以后的市場?
伍:起碼沒有預(yù)感,反應(yīng)十分遲鈍。憑喜歡把它們收著、掛著,一直夢想有一天辦個美術(shù)館。這一點就像葉永青先生說的:“老伍,你若是一個畫商,畫的價格漲兩三倍時就恨不得出手了,怎么會把收藏的作品悶了十幾年這么久?
哪輪到現(xiàn)在給你漲上了百倍甚至千倍的機(jī)會。所以說,歷史對你是很公平的”。但我始終認(rèn)為:藝術(shù)品屬于市場的只是價格,而屬于歷史的才是真正的價值。伍:因為幾個原因。直至2000年起,我開始專注藝術(shù)創(chuàng)作,經(jīng)常受邀到美國、荷蘭和比利時等國進(jìn)行創(chuàng)作活動,當(dāng)我專注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時候,我發(fā)現(xiàn)我沒時間和精力成為這些收藏品稱職的監(jiān)護(hù)人了,我不能營造一個有空調(diào)和控濕的環(huán)境來保護(hù)我的藏品,它們開始?xì)埮f和衰敗。
再加上我本身還在不斷地制造“身外物”,我的能力很有限。我想歷史上所有的收藏者都不外是個過客,不可能終生廝守身外物。如果這批畫最后因為我的原因被毀壞了,還不如讓真正有時間和能力保管它的人去保護(hù)它,因為它們的價值并不屬于我個人的。早期為什么沒有這樣想?
是因為我一直夢想建一個美術(shù)館。但近十年來,當(dāng)我進(jìn)入創(chuàng)作狀態(tài)以后,發(fā)現(xiàn)自己不是這種材料,肯定做不了這等偉大的事業(yè)。這批作品肯定得找更愛惜且有條件去照顧它的人來保管。另一個原因就是我還是喜歡繼續(xù)關(guān)注年輕藝術(shù)家的作品,它們更有時代感。這一點與當(dāng)年對“85作品”的喜好程度是一樣的。
伍:讓當(dāng)代藝術(shù)顯露出自身有被收藏的空間和可能性,價格高低并不重要,能努力改變收藏者的價值觀,把這種歷史記錄下來才是件有意義的事情,這也是我和孔雁從1992年~1997年先后出版了三集《中國藝術(shù)收藏年鑒》的原意。伍:尤永先生是我最敬佩的鼓動者,他對我的收藏品作了極細(xì)致的學(xué)術(shù)整理,十分珍重與善待這些歷史作品的價值。其實到目前為止,我們真正拍出的作品也并不是很多,也就拍了五件。
從這一點你也應(yīng)該看得出來,我們并不是為了賺錢。如果是為了賺錢,早些時候有個開發(fā)商建議要把我們收藏的作品打包給他收藏,一次性出價挺高,我們沒有同意,因為那不是在要畫,而是在要命!受不了。夏小萬那張油畫《先靈》,曾上過中國第一屆學(xué)術(shù)提名展作品集封面,應(yīng)比尤倫斯藝術(shù)中心收藏的那張更精彩,很多收藏家勸我們讓給他們,都一一被拒絕了。這張是我們最喜歡的,倒不是因為他的作品價格有多高,而僅僅是因為喜歡他那種超現(xiàn)實的主題和風(fēng)格,這張畫就放在我們的臥室里,別人看了還覺得怪嚇人的。
包括尚揚的油畫《涅槃》,在這些藏畫里是我們最喜歡的兩張,價格很高的我們未必喜歡,這與我們對畫品與作者人品的判斷有密不可分的關(guān)系。劉:當(dāng)時我打開你編輯的《中國藝術(shù)收藏年鑒》的時候很驚訝,我想這是一個人的收藏嗎?回頭去看收藏的這批“85”的作品,你會怎樣去評價它們?這些作品都是你自己選擇出來的嗎?
伍:當(dāng)時選了一批人,他們的作品都是代表作,由于資金有限,只收藏了一部分,到目前為止它們都不失為博物館應(yīng)有的歷史收藏價值。其實這些人我?guī)缀醵颊J(rèn)識,都有過來往,因為大家都是朋友,一方愿意這個價錢賣,另一方愿意接受,當(dāng)時對大家來說都是一件好事情,一拍即合。我知道大家當(dāng)時很需要經(jīng)濟(jì)來源,雖然我也并不富裕,但是在那個歷史時期,生活少花錢,省下的就可以拿來收藏藝術(shù)品。劉:當(dāng)時并沒有當(dāng)代藝術(shù)收藏這個概念,只有一些外國人有這種意識,像希克、尤倫斯等。伍:1992年我們曾投資編輯出版了《藝術(shù)收藏》和《藝術(shù)市場》雜志。
我和孔雁在1992年至1997年之間編輯《中國藝術(shù)收藏年鑒》的時候,有個想法就是想把我們所有收藏的作品化整為零,都沒標(biāo)明是我個人收藏,全都標(biāo)示我們的下屬機(jī)構(gòu)收藏,包括“世紀(jì)末藝術(shù)工作室”“深圳市藝術(shù)研究會”“專遞美術(shù)館”等,用不同的收藏出處發(fā)表在年鑒上,目的是想擴(kuò)大藝術(shù)家的收藏范圍,更有利于推介藝術(shù)家,讓人們知道,當(dāng)代藝術(shù)是值得收藏的。當(dāng)時我們在年鑒上把所有入選年鑒藝術(shù)家的照片,聯(lián)系地址和電話都印在書上,我們無意商業(yè)操作,有意搭建直達(dá)的信息通道,希望年鑒能直接幫到他們。
伍:應(yīng)該有吧,幾本年鑒在那個年代有很多人看。雖然水準(zhǔn)不能說很高,但在1992年,是比較早的,那個年代也沒有這種類型的書籍,可能是中國第一本藝術(shù)收藏年鑒,現(xiàn)已被納入國家年鑒檔案庫內(nèi)。先后介紹過幾百位藝術(shù)家,國內(nèi)外有不少收藏家憑書上的聯(lián)系地址找到了藝術(shù)家,現(xiàn)在還有人追問:“為什么不繼續(xù)辦下去了?”伍:朋友的作品能收藏的收藏一些,也沒有很系統(tǒng)的收藏。
在以前看的展覽大都是較學(xué)術(shù)性的,后來看商業(yè)性藝術(shù)博覽會后,開始沒有收藏的激情了。當(dāng)藝術(shù)品接觸商業(yè)領(lǐng)域之后,我反而對收藏沒有興趣了。別人沒關(guān)注的時候,我會關(guān)注,當(dāng)藝術(shù)品進(jìn)入市場以后,我反倒不想關(guān)注了。可以說對“85”這一批作品,我沒有進(jìn)行很嚴(yán)格的系統(tǒng)收藏。很多藝術(shù)家的代表作還不在我收藏的這一部分里面。
當(dāng)時王廣義還沒有做“政治波普”,他是到了武漢才做的,我也沒有想過收藏他這方面的新作品,總之算不上有系統(tǒng)。伍:收藏的時候根本沒想到會升值,如果想到了,當(dāng)時我在掏錢的時候就應(yīng)該更爽快一點。前年葉永青跟我說過:如果說你是個商人,這些畫根本就輪不到你來收藏。我說:當(dāng)時是商人的話,絕不會收這些畫,會升值我也沒有想到哦啊。李象群先生之前送給我一件鑄銅雕塑《微笑的春天》,兩年后有人問我:“你知道現(xiàn)在這件作品的市場價格已經(jīng)上升到幾位數(shù)了嗎?
已經(jīng)到六位數(shù)了!”我說“不知道”。我沒興趣去了解這個,這個跟喜歡絲毫沒有關(guān)系。伍:因為我成立了“世紀(jì)末藝術(shù)工作室”,也辦過兩期展覽,就有很多人說我開始玩收藏了,當(dāng)時也有經(jīng)紀(jì)人覺得他們手上有很多名家作品,拼命地推薦給我,其實大都是些垃圾,都一一被我拒之門外,但好的我未必漏眼,真正讓我挑藝術(shù)作品時,藝術(shù)家有時是心慌的,因為我總不會把差的挑走,著名編導(dǎo)史健全老說我眼光很毒。
一次在王川畫室我挑走了兩件六尺宣抽象水墨,后來發(fā)表在《藝術(shù)市場》雜志上,漢雅軒老板張頌仁先生發(fā)現(xiàn)后質(zhì)問過王川:“你為什么把兩件好畫給老伍?”王川說:“他是在你挑剩的垃圾里揀回來的。”張頌仁聽了不吱聲了。這兩張畫1996年在美國舊金山舉辦的《重返家園》藝術(shù)展上,與趙無極的作品同時展出。那時候任戩曾拿了幾張畫給我挑,我就挑了那張恐怖的《天狼星傳說》,這張果然就是他的文獻(xiàn)上很重要的作品。
伍:他90年代做的《牛仔褲》我也收藏了。其實成立“世紀(jì)末藝術(shù)工作室”也促成了收藏,有空間卻沒有好的藝術(shù)品就太可惜了。因為當(dāng)時我自己也沒時間整天創(chuàng)作,不然工作室空間肯定擺我自己的作品,不會擺別人的,所以要相信“凡事有失必有得”。雖然當(dāng)時我的藝術(shù)風(fēng)格與藏品風(fēng)格很不相同,但是我能隨時看到朋友的作品,體味他的想法、追求以及藝術(shù)形態(tài),心里不但感到欣慰,而且會令你時刻充滿著激情。
是因為喜歡,你才會收藏。伍:是的,對于收藏一直有自己一種價值觀的立場和態(tài)度,做藝術(shù)也是這樣,當(dāng)你人格獨立的時候,市場其實和你沒關(guān)系。我不主張為市場而創(chuàng)作,也從不覺得自己的作品值錢,我想過如果我的作品有人喜歡并能善待它,我會樂意給他,價格并不重要。自在的狀態(tài)不必靠創(chuàng)作找市場的,況且物質(zhì)是不能永存的,要活得明白。伍:我覺得人格獨立很重要。有些畫家活的很累,因為他不愿意做任何與藝術(shù)無關(guān)的事情,在沒有市場支持的情況下,老想靠別人贊助或交易,希望對方可以幫忙分擔(dān)壓力,這種事情我就做不來。
你如果敢于爭取人格獨立,就應(yīng)敢于付出你的心智與勞力,不妨做藝術(shù)以外更有意思的事,有了經(jīng)濟(jì)基礎(chǔ),專事藝術(shù)時就沒有必要糾纏于求施舍和討好他人的事端上。否則,在精神層面還是有一套無形的枷鎖。因為“自救”才能擺脫“求他”的精神困擾,就不會浪費時間去做一些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你的藝術(shù)需要“求他”,最起碼就得試圖去建立一種關(guān)系,這種關(guān)系往往都不是發(fā)自內(nèi)心,只是一種交易需求就沒什么意思了!其實做人和做事的細(xì)節(jié)最能體現(xiàn)一個人的本質(zhì)。
劉:其實小細(xì)節(jié)可以反映一個人大的取舍。2008年中央美院畢業(yè)生作品展,有一個學(xué)生做了一批用被子組成的裝置作品,當(dāng)時我覺得很好。可是有天下雨,他突然就把被子抱回去了,我當(dāng)時覺得非常的遺憾。如果下雨的時候那被子要鋪在那里多好。可是天晴以后他又把被子抱了回來,繼續(xù)鋪在那里。這時候面對作品我已經(jīng)不能感動了。經(jīng)歷了20多年的收藏歷程,回頭看現(xiàn)今的當(dāng)代藝術(shù)創(chuàng)作,如果再收藏的話,你還是會憑自己的喜好去選擇作品嗎?伍:這點是肯定的,現(xiàn)在是個浮躁的年代,很多藝人都在畫錢,其實缺乏真知和真誠,便與藝術(shù)無緣了,更別奢談文化的建樹了,再值錢的作品充其量只是一件商品而已。
當(dāng)前世界經(jīng)濟(jì)危機(jī),突顯了商業(yè)藝術(shù)的脆弱,更別說賣畫者多有藝術(shù)自信了。在創(chuàng)作上,如不需要靠銷售作品求生存,那肯定是自在的,在北京目前執(zhí)行的雕塑零突破藝術(shù)觀察計劃是我和一幫朋友資助年輕藝術(shù)家的計劃之一,我相信,該觀察計劃會有優(yōu)秀作品產(chǎn)生,也會再次實踐我的收藏思路。劉:一個是對藝術(shù)史的了解,一個是對作品的直覺判斷,這對收藏鑒別很重要。伍:是的,在展覽欣賞作品時我不會首先看作者名字,作品能否打動我才是至關(guān)重要的。其實我更多還是看作品的獨創(chuàng)性。
藝術(shù)語言必須要獨特,并且要有一些與眾不同和奇思妙想的東西在里面,是不是名家并不重要,我絕對不喜歡似曾相識的作品,不管它出自誰人之手。劉:要布置一個局,然后把一些很有意思的東西激發(fā)出來,其實是比較有意思的事情。伍:做個過客挺好,也為作品生命的延續(xù)盡過責(zé)了。其實曾經(jīng)擁有就已經(jīng)很美好。
現(xiàn)在想擁有藏品的人很多,要么缺乏專業(yè)判斷力,要么搞不明白自己喜歡什么,又或缺乏資金才沒能擁有。一個人的富足不在于物質(zhì)擁有的多與少,像栗憲庭先生站在評論家的角度,難道他不知道哪些東西是好的?因為他們本身是做文化的,未必想擁有什么。當(dāng)年靠栗憲庭先生推介出來的藝術(shù)家,現(xiàn)在已經(jīng)很有錢了,但老栗的生活如故。也正因為這樣,他的文字及狀態(tài)才可以保持鮮活。盡管人都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只是每個人對物質(zhì)生活的態(tài)度不一樣而已。
伍:到目前為止,當(dāng)代藝術(shù)家收藏當(dāng)代藝術(shù)作品的人有多少,我不太了解。現(xiàn)代人多多少少喜歡擺弄一下古代的東西,我反而對古代的東西興趣不大。遇上一些創(chuàng)意獨特的東西我們還會收藏,不管它們的價值貴賤,只因喜歡。可惜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所以我只能有限度地玩一下,滿足一下好奇心。劉:我覺得在你的整個收藏脈絡(luò)里面,有一個自己對當(dāng)代性的體驗需求在發(fā)揮重要作用。伍:收藏過程是一個體驗過程,新銳的東西很有活力,融入其間心情會很爽。
所以在國外生活,我和孔雁絕對不會錯過那些創(chuàng)意設(shè)計專賣店,凡是有創(chuàng)意的東西我們都會喜歡。正因為這樣,所以整個生活狀態(tài)也會得到一種感染和體驗,所收藏的東西一般都比較有創(chuàng)意。平面設(shè)計、建筑、景觀和小物品我們都會喜歡,但大都是比較另類的,它們會融入自己的生活體驗之中,會給你注入青春活力和產(chǎn)生無限的遐想。伍:對生活應(yīng)充滿激情,要懂得享受工作,享受過程,否則不會有活力,我與年輕人都談得來,他們永遠(yuǎn)是我保持青春活力的導(dǎo)師,這是我對自身生命狀態(tài)的一種基本立場,藝術(shù)收藏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從文化發(fā)展的角度去關(guān)注它,它永遠(yuǎn)會給你帶來無限驚喜與震撼。
其實從過去到現(xiàn)在我對收藏的立場和態(tài)度幾乎沒有改變,對另類的東西,我們會一直保留著濃厚的興趣。與當(dāng)代藝術(shù)同行的收藏是一件隨緣的事,人生有一個奇妙的秘訣就是:播下思想的種子,收獲的是人格;播下人格的種子,收獲的是命運。
種瓜必得瓜,種豆必得豆,因果關(guān)系是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zhǔn)的自然法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