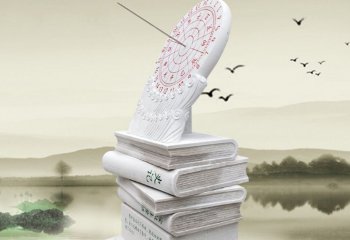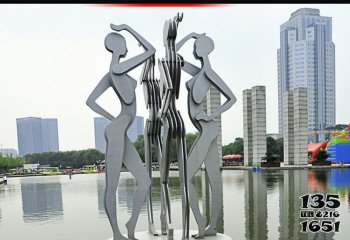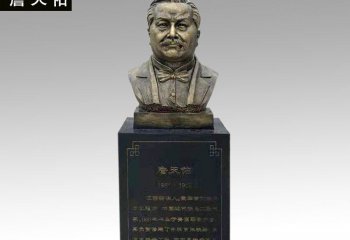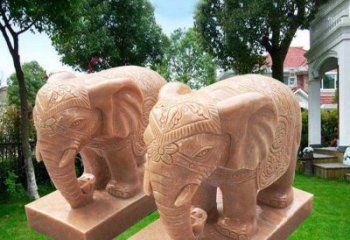帶有西夏文的銅牛,經(jīng)專家鑒定為西夏時(shí)期黨項(xiàng)羌人所鑄,距今約有近千年歷史。這件銅牛所反映的西夏冶金術(shù)再次引起了學(xué)術(shù)界的關(guān)注。西夏的“乾祐”銅牛西夏銘文的銅牛身長約15cm,重約850g,銅鑄空心,體態(tài)呈內(nèi)屈跪臥姿勢、膘肥體胖、兩角彎突、兩耳直立,雙眼炯炯有神,頸部寬厚有數(shù)道膘皺紋,尾部鑄有西夏銘文“乾年”3字。專家認(rèn)為,這只頭牛神情溫馴,造型逼真,而且是已知出土的三件西夏銅牛中唯一一件帶有西夏銘文的珍寶。其中最著名的要數(shù)西夏王陵出土的鎏金銅牛,重188公斤,造型逼真,比例勻稱,線條流暢,制作它需集冶煉、模具雕塑、澆鑄、焊接、拋光和鎏金等工藝于一體,是西夏藝術(shù)品中的珍品。
從這只銅牛身上人們能夠看到已經(jīng)失傳的西夏冶金術(shù)。據(jù)了解,西夏人的冶金術(shù)非常發(fā)達(dá)。西夏工匠已掌握了較高的金屬冶煉鑄造技術(shù)和工藝。尤其是鑄造器物成型的制模、澆鑄、焊接、拋光和鎏金等。西夏政府機(jī)構(gòu)中設(shè)有“文思院”專門負(fù)責(zé)管理金銀器制造。當(dāng)時(shí),西夏人能制造一種衣金,就是把金拉成絲,然后織到衣物之中。
文獻(xiàn)記載,西夏官吏戴金冠,更有甚者“人馬皆衣金”。神秘的“夏國劍”黨項(xiàng)民族尚武,所以西夏兵器制造得很精良。史書記載,西夏甲胄“皆冷鍛而成,堅(jiān)滑光瑩,非勁弩可人”。“凡鍛甲之法,其始甚厚,不用火,冷鍛之,比元厚三分減二,乃成。”西夏陵出土的甲片,制作精細(xì),薄厚均勻,孔眼劃一,有的外表有鎏金。西夏刀、劍制造得也非常出色,當(dāng)時(shí)“契丹鞍、夏國劍、高麗秘色,皆為天下第一,他處雖效之,終不能及”。
《雞肋集》記載,蘇東坡曾獲西夏劍,極其欣賞,便命晁補(bǔ)之作歌贊之:“紅妝擁坐花照酒,青萍拔鞘堂生風(fēng)。螺旋锘鍔波起脊,白蛟雙挾三蛟龍。試人一縷立褫魄,戲客三招森動(dòng)容。”就連宋欽宗本人也常佩帶夏國劍,由此可見西夏劍之犀利與名貴。西夏的“神臂弓”是一種威力極大的兵器,此弓“其實(shí)弩也,以糜為身,檀為銷,鐵為槍鐙,銅為機(jī),麻索系扎絲為弦”。其三百步外,能洞穿重札,最為利器。
先進(jìn)的冶煉技術(shù)西夏金屬制品的精致,除了有高超的鍛鑄技術(shù)外,還與鼓風(fēng)設(shè)備的先進(jìn)分不開。西夏工匠在鍛造中所用的鼓風(fēng)設(shè)備已不是韋囊鼓風(fēng),而開始使用風(fēng)箱鼓風(fēng),這樣可以保持爐膛內(nèi)所需高溫。榆林窟第3窟西夏壁畫中有一幅《鍛造圖》,圖中有三人,一人左手握火鉗夾一金屬置于砧上,右手舉錘鍛打,另一人雙手掄大錘鍛打金屬,第三人坐于墩上,推拉著豎式的扇風(fēng)箱,風(fēng)箱可推拉互用,連續(xù)鼓風(fēng)。風(fēng)箱鼓風(fēng)不僅提高了鍛造速度,同時(shí)也可提高鍛造質(zhì)量。
在伊金霍洛旗出土的鐵鍋,其制作工藝要比當(dāng)今所用的普通鐵鍋復(fù)雜得多。然而年代久遠(yuǎn),人們已經(jīng)把西夏的冶金術(shù)忘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