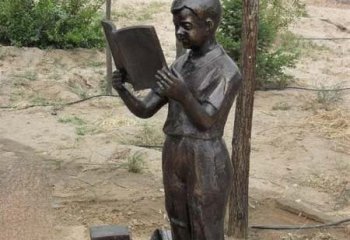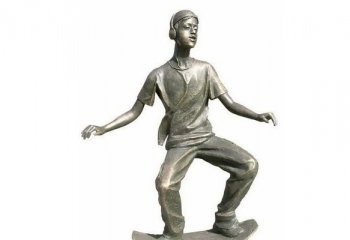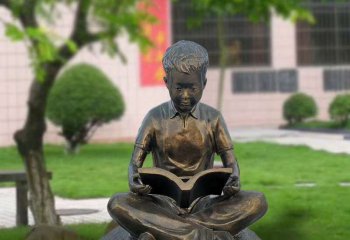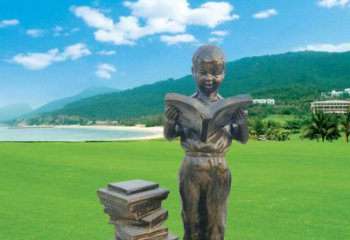我的父母都是文藝工作者。父親是一名優秀的二胡演奏家,音樂家。他自己創作的二胡獨奏曲曾經在全國民族器樂比賽獲獎,是一首描寫天山美景的曲子,很有味道。曲名取得也很棒,叫《天山素描》。除了二胡,他還會擺弄薩克斯、單簧管等的很多種樂器。母親是一名優秀的兒童話劇演員,得過的獎很多,但我佩服她的是能歌善舞,會彈鋼琴,自彈自唱總是很精彩。母親從不發脾氣,總是微笑著。但是她很忙,不停地演出。

曾經一年里只有三個月是在家里度過的,其余時間就在全國各地演出。據說小時候,有一次她演出幾個月回來,我都不認識她了,在公共汽車上,突然想起她是誰了才一個勁兒的親她,車上其他人都很詫異,母親跟他們說明了情況,他們都覺得我很可愛。所以我童年的記憶多半是跟爸爸有關,記憶中他除了上班都會用心的為我做飯,在灶臺邊花上很多的時間。但他閑暇里絕大部分的時間還是把自己關在我家小小的臥室里跟他的樂器度過的,此外的大部分時間就是要為了維持生計而四處演奏賺錢。

記憶中母親后來異地的演出似乎也沒有小時候那么多,她的閑暇也就都奉獻給了為生計而演奏。有時父母親會在同一地點,以一個樂隊的形式出現。偶爾我也會跟著,樂隊里還有其他有才華的叔叔阿姨,都能歌善舞詼諧幽默。演出多半是在別人的假期里才被需要,所以經常會是周末,于是我才有機會跟著他們。可惜我什么也不會干,就只是跟著,幫不上什么忙。周末演出的早晨要起得比平時上班還早,這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

畢竟那時我還小,無論周末與否,被窩里才是最愛的地方。但是,同樣也因為我還小,一切事物對于我都很新鮮,所以那時父母們為生計而不得不從事的辛苦工作在我眼中卻充滿了樂趣:三五好友一起玩玩音樂,玩得盡興,人家就會付錢,還有一頓免費附贈的豐盛大餐。我的任務除了跟到地方,每次隨便遇到幾個陌生的小朋友一起胡亂打發打發時間之外,就只有那頓豐盛的大餐!耶!可這一切從成人的角度看起來完全不一樣,父親覺得搞音樂挺辛苦。印象中漸漸清晰的又是父親練琴的景象,一個人,形單影只。

母親在外地演出,我悄悄溜出家門去跟小伙伴兒撒野了。那時的夏天沒有電扇空調,熱!家里常常敞開著大門。我跟小伙伴玩野了時常是三過家門而不入,雖然不入,卻能把屋里的情況瞟個清清楚楚,那一瞟有點像是按了相機的快門一樣-咔嚓,也沒時間仔細看,但真就是像拍了快照一樣,那么的清晰而又印象深刻:父親躺在廚房的地板上睡著了,就躺在地板上。現在想起這番景象覺得好心酸,當時自己怎么就沒停下來叫醒他讓他上床再接著睡呢?就那么沒心沒肺的白駒過隙了。耳濡目染中,這些還都只是表面的“苦”,那些不表面的我當時看了卻也看不懂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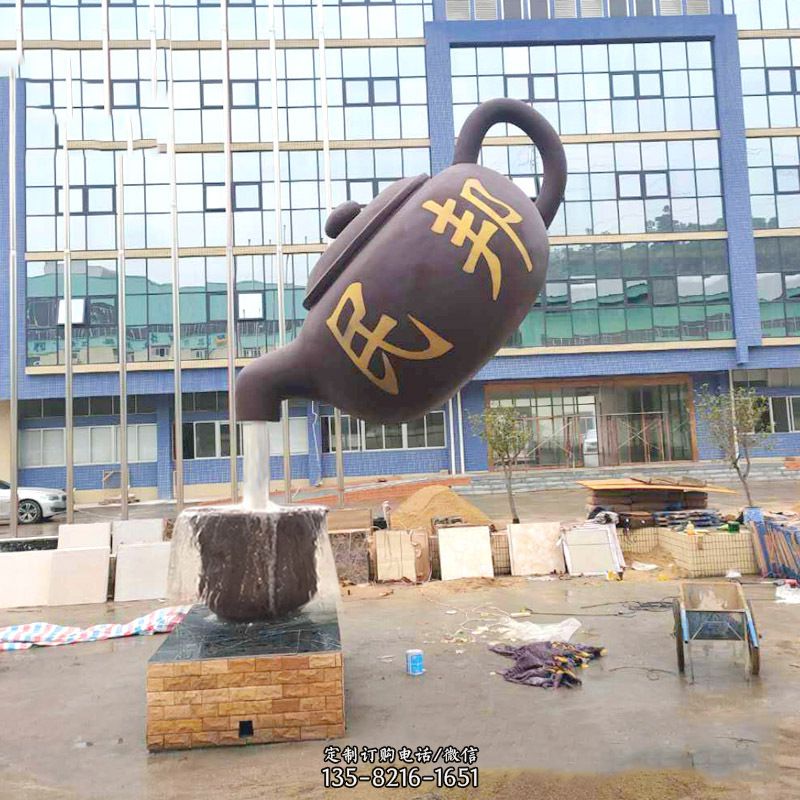
我不懂,但父親懂得啊。于是,父親平時都是盡量回避音樂方面對我的熏陶。當我心頭為某樣樂器所動了,他總要當頭棒喝,毫不姑息。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既因為對樂器的喜好,又帶著對電視劇里大俠的崇敬,我悄悄給自己買了一只竹笛。帶回家正準備好好稀罕稀罕的時候,遇上正要如廁的父親,只得到一句,兩個字“退了!”后來我了解到,父親的反應其實是因為早在心中替我擬定了人生方向—美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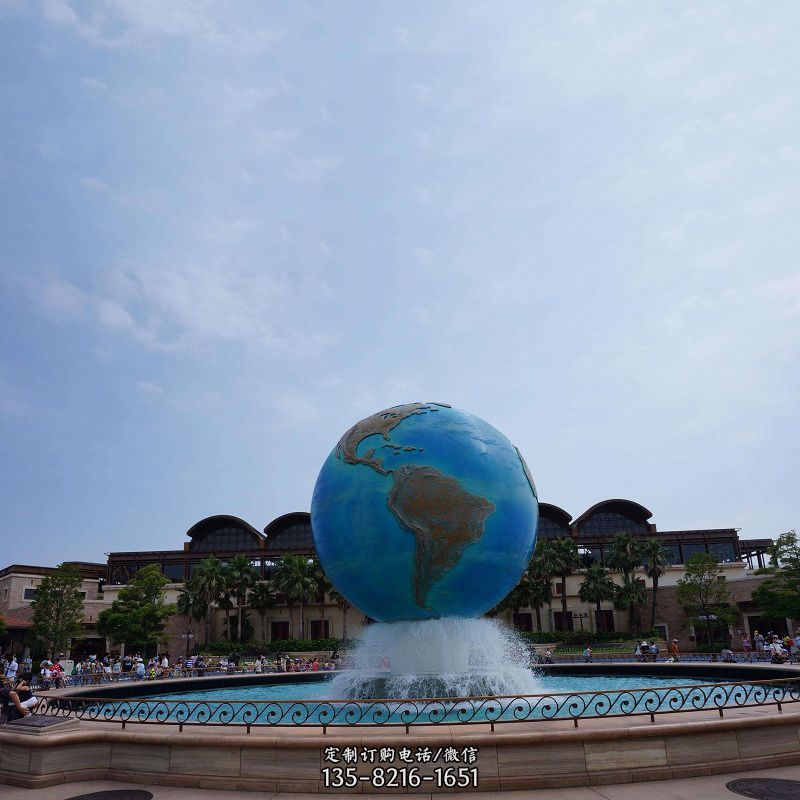
我當時小學還是幼兒園現在不記得了,只記得自己不知道“雕塑”是什么,卻挺因為聽說自己將要成為雕塑家而沾沾自喜。我不知道,但家里的大人們全知道。那時,“雕塑”對我而言就是玩橡皮泥,“雕塑家”大概就是祖父和父親,因為祖父跟父親都能夠輕易地用橡皮泥做出十分像樣的“拖拉機”:揉四個圓面餅,兩個大兩個小,再揉幾個小方塊兒,拼幾下,用火柴棍一串,成了。

一個巨棒的“拖拉機”,我超喜歡。他們比我做的好,我就拿著他們捏成的玩兒。我捏不成他們那樣規矩的形狀,用今天的話說我屬于“創作型人才”,總是胡亂捏些小玩意兒。時間久了,橡皮泥被一遍又一遍的捏來捏去,從原來的五顏六色變成了灰色,我的手藝也跟著有了長進。我開始捏十二屬,“子鼠、丑牛、寅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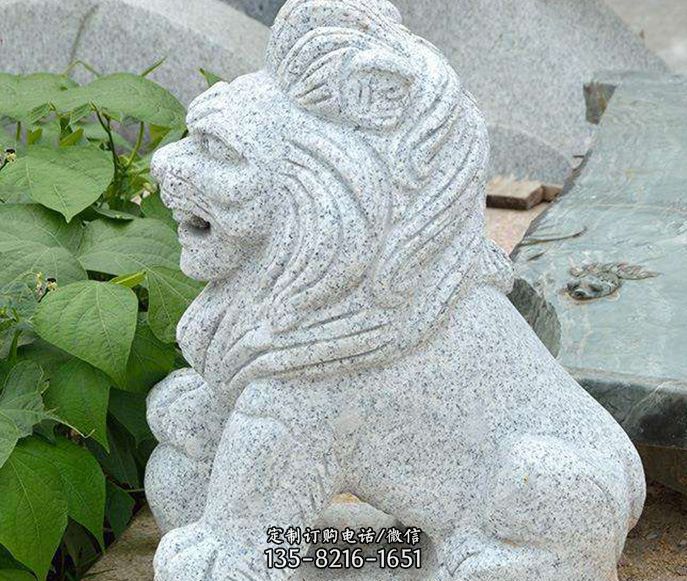
巳蛇”,這“巳蛇”可真是難住了我。我跑去問姨奶。她接過橡皮泥雙手搓了幾搓,一個長長的泥條子出現了,接著她把泥條子盤啊盤,盤成一個小圓盤,留著個頭立著,在上面點了兩個點兒。嘿,一條“巳蛇”就這樣出現了,原來姨奶這么厲害!家里的雕塑家可真多。這以后,我做十二屬,“巳蛇”都按這個法子做。直到今天,姨奶還是逢人就講她當年教我捏蛇的故事,不知聽了多少遍。以至于我現在都搞不清是自己當年就清清楚楚的記住了這件事,還是后來聽她講得多了,再也難以忘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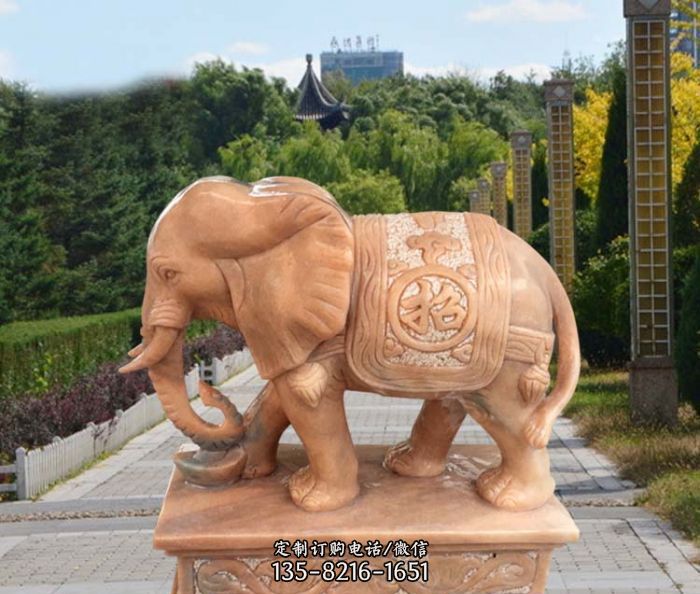
后來,我做出了我的“十二屬”。有那么一個階段,這幾乎成了我的招牌。只要家里來了客人我就會被喚至一旁,展示我的“高超雕藝”,不知道有多少回。據祖父說那時我的“雕藝”也是出神入化,當年上幼兒園的時候,老師一早是要把小朋友從家帶來的所有玩具之類的東西全部“收繳”的,直到放學的時候才會盡數歸還。這是當時人人遵守的規定。

但是,我當時每天都帶著橡皮泥,卻從來沒上繳過。祖父說我那時都是把橡皮泥藏在褲兜子里輕松過關的,他管那叫“卡巴襠”。每次到了放學他去接我的時候我總能交給他全套的“十二屬”之類的,所以他現在還常說,“我孫子當年的雕塑都是從‘卡巴襠’里做出來的”。我挺愛聽他講我這段光輝歲月的,但是,想想也不對呀,真在“卡巴襠”里做雕塑,那多難呀!后來上了小學,“十二屬”就做的沒有那么勤了。不是因為學習忙,而是因為興趣發生了變化手里的活活泥巴或者弄些粉餌揉成拳頭大小也就跟著有了變化。

那時愛看動畫片,邊看邊捏,《小飛龍》、《變形金剛》什么的。家里的大魚缸能有一米多長一米多高,最上面蓋著玻璃板,玻璃板上面就成了我展示作品的平臺。就連工程部隊組合的大力神都捏出來了,更別說擎天柱威震天了。

就連顏色都是用了跟原著里一樣顏色的橡皮泥對號入座的,在我印象中真叫一個棒!那會兒在學校,大家都是男生女生搭配著做同桌。忘了是什么原因,我曾經有那么一個階段是跟兩個女同學一起,三個人同桌。我坐中間,上課的時候開小差兒,表面上故作鎮定,兩只手就藏在書桌洞兒里玩教孩子們玩起真正的泥巴。做個小飛船,翅膀里面剪一小段鐵絲,降落之后還能把“機翼”收攏。我都是小心翼翼的,生怕被老師發現,俘虜了我的“飛船戰隊”去充公。誰知道跟我同坐的兩個女同學真是大膽,其中一個見老師轉身寫板書的空當兒,抓了我的飛船就作起飛狀,我還沒來得及做出任何反應,就從書桌洞兒“飛”了出來,直“飛”到大家視線的高度,飛向坐在我另一邊的女同學。

另一邊的女同學見狀極其配合的接過來又飛回了書桌洞兒,并完成了降落。整個過程真是讓我驚心動魄,好在寫板書的老師錯過了整個“空軍表演”的過程。那時課不多,學校時常要裝修。我們被安排在去附近的學校借教室上課,這樣一來常常只有半天課,下午通常都是自由活動的時光。我父母都很忙,所以我的大部分閑暇時光都被安排在祖父家度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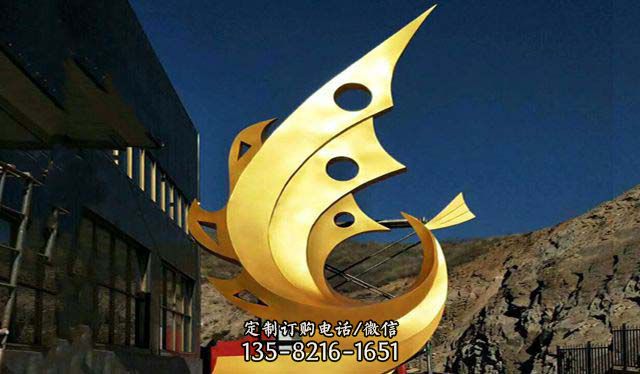
那個時候電視還不是什么不新鮮的玩意兒,所以經常是全家老小圍坐觀摩的。大人們顯然覺得我做個快樂的小突然聽到一聲小孩兒的哭聲就行了,并沒打算要求我學習如何優異。所以我經常可以很自由的選擇打打游戲機,到戶外跟小朋友捉捉蟲,或者看看電視什么的。我當然沒有什么自制力,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會沒事的時候自己想想,我要做個好孩子,所以應該做作業,不應該總是玩兒,絕對不會。

現在想想,那個時候的自己做什么都好,對今天總是有益的。當他們圍坐電視機前,我就拿著橡皮泥湊過去,看見里邊演什么就捏什么。有一次,二舅姥爺來做客,我又被喚至一旁進行表演。那會兒特別熱衷于捏大狼狗,可能是那一陣子電視里總有警犬義犬之類的電影吧。大狼狗捏罷,二舅姥爺自然是一番夸贊。想想成年人對他們眼中的小小毛況且他身邊漂亮的女孩兒多得很要求能有多高呢。
我記得他十分驚訝的說:“這么小的孩子就能把這后腿的解剖結構都拿捏得這么到位呢!”記得當時在場的大人們都很開心,我自然是最得意的那個。但是,“解剖結構?”拜托,我那時哪里聽得懂他們在說什么,只不過人家表揚你,還表揚的那么真誠,你都不好意思不認的。不過我那時的大狼狗真的捏的惟妙惟肖的。
后來上了中學,學習的壓力一下就變得大的不行。我就像是變了一個人,一個猛子就扎進了各路的“題海”,“卡巴襠”里再沒有了橡皮泥。即使是后來考上了中央美院附中,每天都在學習真正的美術了,甚至后來上了中央美院真的選擇了雕塑專業,始終都沒能讓我再重溫當年玩兒通往菠蘿的海的泥巴路上擠滿了人和車的樂趣。直到今天,當我把這些文字敲進電腦的過程中,我才又遇見了當年那個懷揣著橡皮泥的小毛孩。時隔多年,我想說“久違了,小朋友!
久違了,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