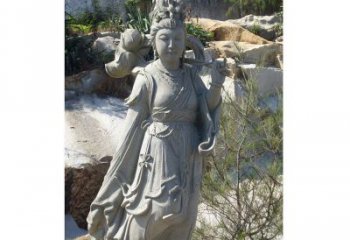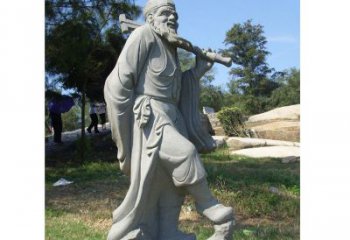訛傳不是頌揚,編造只能失去公信,甚至成為一種褻瀆。唯有真實,才是真正強大的力量。廣告國際化時尚家具設計,生活可以很隨意,很舒適.八仙桌,家具行業風向標,引領家具時尚潮.上世紀九十年代,我和一位江蘇作家得到一次走訪青海的機會,二十多天里,曉行夜宿,留下無數難以忘懷的記憶。柴達木的經歷是其中之一。“柴達木”是蒙古語,意思是“遼闊的地方”。那天晚上采訪結束,已近午夜。當地派來給我們領隊的李處長征求意見,明天是一整天的行車路程,目的地是柴達木油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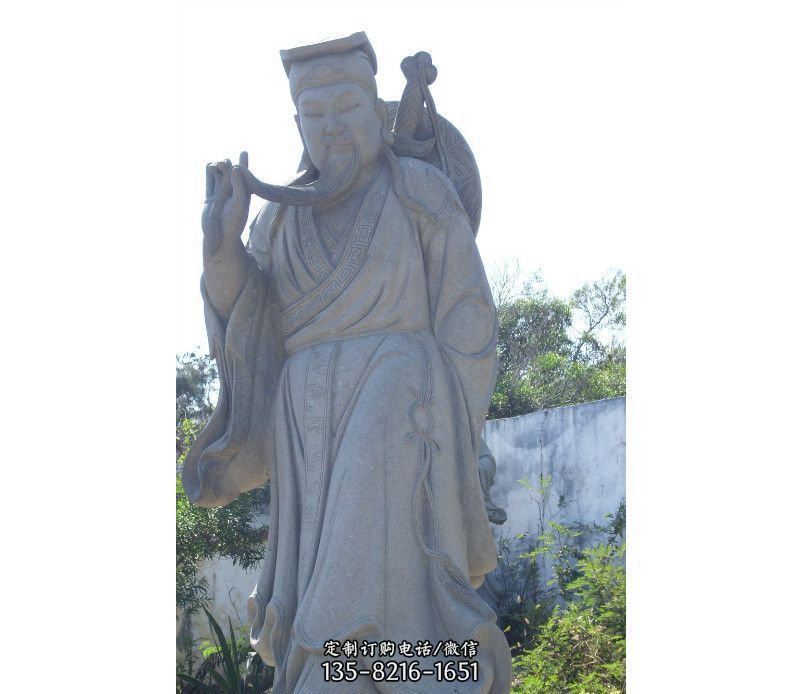
去那里有兩條路,其中一條早已棄用,但可以穿過世界最大最典型的雅丹地貌群——“魔鬼城”。一路上景象奇異瑰麗,但沒有人煙,最大的風險是遭遇沙塵暴。我毫不猶豫說:當然是走這條路!柴達木的雅丹地貌,由七千五百萬年的風蝕而成,雅丹土林總面積兩萬多平方公里。飄忽不定的狂風,在平均海拔三千多米的高原雕塑出似乎無邊無際高低參差的土林,除了毫無生命的跡象,像極了世界最繁華的現代城市群落。詭秘怪異令人不寒而栗的尖銳狂暴的風聲,在蒼茫而陰森的“城市”中間呼嘯洶涌,在高遠而恐怖的“城市”上空卷起猙獰的煙云。
這是一段驚險的旅程。李處長事先的警告并非多余。中午,我們真的見識了沙塵暴的威力,把一整座沙山橫移到公路邊上,余脈在路上堆起高坡。好在我們走近這座高坡之前,沙塵暴已經平息。方圓數百里沒有可以提供幫助的人。我們把早上帶來的饅頭、榨菜、礦泉水塞滿了肚子,然后連滾帶爬地一點一點把那輛小面包車抬著扛著總算萬幸推過了那片沙坡。然而對于那些把一生都奉獻于這片遼闊蠻荒的人們,這樣的經歷根本不值一提。這條路上最著名的一個地點是“南八仙”。
相關的資料介紹:1955年,八位南方來的女地質隊員,為勘探石油進入這里,在迷宮般的土林中跋涉測量,返回途中,鋪天蓋地的黃沙籠罩了荒漠,僅有的標志被掩埋。人們再也沒有在這亙古的荒原找到她們的蹤跡。后人因此把這里命名為“南八仙”。
因為她們的遇難,“南八仙”又稱“難八仙”。走訪結束,我把這個故事寫進散文《柴達木人》,在1999年第十期《人民文學》上刊發出來。“南八仙”一直是歌詠的對象。關于“南八仙”的第一首詩詞,現今可見的是國際著名石油地質專家、中國科學院院士朱夏寫的。這位浙江嘉興世家子弟,少時隨父母學習詩詞創作,一生留下詩詞千余首,被譽為“中國石油、地質學界舊體詩第一人”。
其作《柴達木雜詩》有“大風中自南八仙赴一里坪”:“微聞海上有仙山,出沒煙霞變幻間。今日御風橫大漠,忽窺瓊島識云鬢。”上面的故事,至今在有關柴達木的各種資料以及網絡上存在著。但我卻不斷發現,這并不是“南八仙”來歷的真相。
最早描寫“南八仙”的是《人民日報》記者:八個地質隊員在從無人跡的荒野支起帳篷,開始地質普查。工作完成后想給這里起個名字,不知是誰說的:咱們八個人勝利到達這里,就像八仙過海。咱們又是向南走的,就叫“南八仙”吧!記者后來感嘆:雖然沒有找到那個取名者,卻找到了一個光榮的集體:地質工作者!記者的文章寫于上世紀五十年代,青海開發的初期。
八個地質隊員在這里自稱為仙,顯然是最接近真實的說法。此外,還有一種說法也不無道理:一大片雅丹土林中,有八個險峻土丘,遠看就像八仙過海。這兩種說法,無論哪種,都與朱夏院士和我采信的故事毫不相干。八位女勘探隊員的失蹤沒有任何事實依據,而這樣一個悲劇的發生不可能沒有任何歷史記錄。但杜撰、想象以及采信,卻逐漸形成了一種文化覆蓋。
這其實是一個美麗的錯誤。我在那次時日不短的走訪中,聽到了無數可歌可泣的故事,常常當場為之淚目,過后輾轉難眠。一代代投身青海開發的人們獻了青春獻終身,獻了終身獻子孫,本身就是一曲曲偉大壯烈的生命頌歌,根本用不著任何虛構。訛傳不是頌揚,編造只能失去公信,甚至成為一種褻瀆。唯有真實,才是真正強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