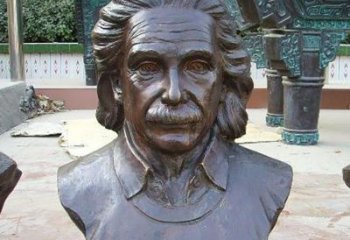在美國總統大選正酣之際,雕塑家丹尼爾·愛德華茲又適時出來“興風作浪”,他推出的新作是奧巴馬的妻子米歇爾。這位被媒體捧為最新名人時尚風向標的“準第一夫人”,竟然被愛德華茲赤裸上身地坦蕩于世人面前了。她胸前一對碩大的圓錐形乳房夸張地橫亙著。一對超大的圓形耳環,一個黑人式的桶裝大發髻,則讓她儼然一位“非洲女王”。但米歇爾裸露的胸口上卻有一個美國國旗的文身,發簪是一只展翅的美國鷹。

該作品取名叫“米歇爾·奧巴馬為美國而裝扮”,10月初便開始在紐約的LeoKesting美術館展出。人們可以輕易發現,米歇爾這個雕塑與現實形象最大的區別在于——赤裸、碩大的乳房以及黑人式桶裝發髻。這些想象性的元素,恰恰正是最耐人尋味的思考點。米歇爾當然不會赤裸于公眾,她總是把自己包裝得既符合高品位時尚又不失個性化特征;碩大乳房所象征的女性氣質也是現實中的米歇爾有意無意間所隱去的,她總以一種很男性化的強勢出現在公眾場合,多少有點“女男人”的味道;非洲式發髻更加不可能出現在米歇爾的現實造型中,她目前的經過拉直的短發已經把先天的非洲性發質做了最大限度的修飾,她實際上是一種“披著白皮的黑人”。

作品名“為美國而裝扮”,其實已經點出了關鍵,愛德華茲是在揭示米歇爾現實形象中被掩飾和虛化掉的一些本原——女子氣、非洲裔,以及強烈人工包裝色彩。她是為了美國而裝扮,為了丈夫的選戰而變身為今天此形象的。當剔除這些“裝扮”后,米歇爾便仿佛一位愚昧的非洲土著女王,眼神僵直呆滯,與大家所見那個意氣風發的米歇爾天壤之別了。當然,如果一件雕塑可以用以上這種“細讀法”進行解讀,就多少說明這個雕塑家的作品并非屬于一種拒絕解讀的后現代性作品。愛德華茲作品的所謂“前衛性”,其實并在于一種天馬行空的超現實表達,而在于他能夠以當下最具時效熱度的名人作為標本,并以一種刺激性的非正常狀態來展現出名人的內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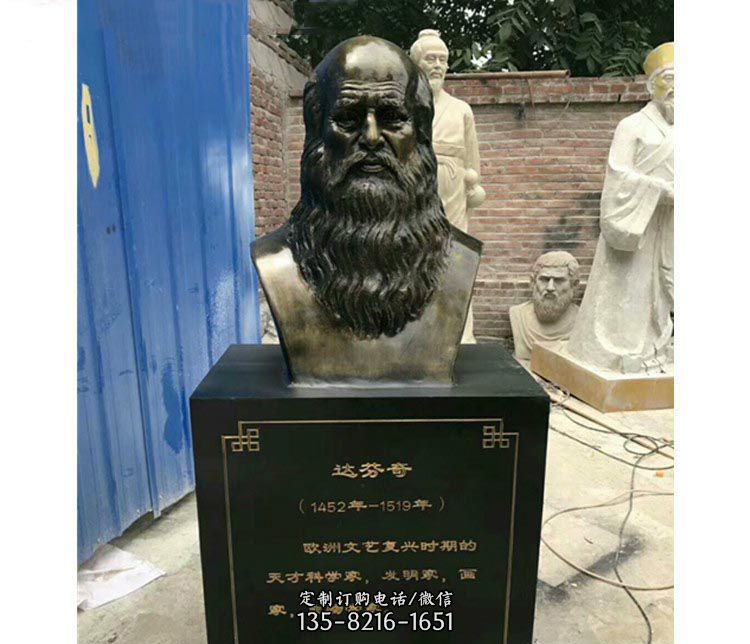
誕生于愛德華茲手上的布蘭妮是一種分娩的臨盤狀態,她赤身裸體地趴在一張熊皮地毯上分娩,屁股高高撅起,乳房半吊著,小孩正從她的張開的陰道口誕出;而帕麗斯·希爾頓則是一種被剖出了腸道內臟的死亡狀態,她叉開雙腿地平躺著,全身赤裸僅剩手上的一臺手機,整盤腸道內臟被置于腳邊,她那著名的吉娃娃小狗在她臉旁叫喚著;哈里王子則是于伊拉克戰爭中陣亡,頭枕一部《圣經》躺在英國國旗前,雙眼上放置著硬幣,右手緊握著一件戴安娜王妃的紀念物,腰上挎著一把裝在槍套里的手槍,腳邊是一只虎視眈眈的沙漠禿鷹。當然,這些名人雕塑之所以能夠吸引眼球,首先是緣于他們都是名人,繼而才是那種匪夷所思的姿態。

這就決定了愛德華茲的作品大體上是一種寫實性作品,他只能在呈現名人客觀本體的基礎上,才作出其他夸張性的創作,顯然也并不是那種極端性的個人主義意欲表達。加之其對超強社會時效性的追逐和契合,所以完全可以把他的雕塑納入大眾流行文化產品的行列。由此,他的作品便可能會在一種媚俗化和顛覆性之間跳躍置換著。是滿足取悅大眾的媚俗欲望?

是具有解構力的批判性表達?這之間的跳躍似乎騎墻和見仁見智的。不過,這種回到社會生活之中的取向,未必不是雕塑乃至各式藝術在窮盡后現代抽象之路后的一種回歸。這或許才是藝術的原本位置以及當代藝術的一種出路。如果說愛德華茲作品具有某種程度上的顛覆性,那么可能就在其于熱衷的一種名人生理性揭示——布蘭妮生育中的下體,希爾頓死亡后的腸道內臟,還有米歇爾以及希拉里的乳房,當然還有阿湯哥愛女蘇珊首次排泄的兩坨大便。

在這種純生理性的唐突展示和參照中,名人們本來甚為炫目的氣質光環,統統被瞬間剝除和打碎,名人不過一種也要生也要死更要排便的凡人軀體而已。而失去了光環的名人便仿佛一具失去了靈魂的行尸走肉,頹廢氣極重了。于是,米歇爾充滿野心的雙眼低垂下來了,希爾頓嫵媚的眼睛竟然閉合上了,布蘭妮眼中的青春亮光也變成沉重的憂郁。這似乎在宣示著,所有光環僅來自包裝,在生理本質面前,根本不堪一擊。

除卻易碎的光環,名人什么也沒有了。這種名人解剖學,未必不適用于每個普通人,這也是其作品最刺人心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