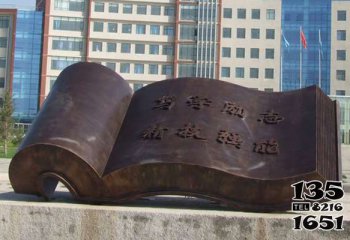作為本年度國內最重要的藝術展覽之一,由蘇州市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主辦的“相嵌蘇州——中國當代藝術展”將于9月5日在蘇州博物館現代藝術展廳內展出。總價值近億的22件油畫和雕塑作品將為蘇州人帶來一場迄今為止最豪華的當代藝術視覺盛宴。耗資百萬,精心籌備一年,邀請了包括張曉剛、方力鈞、岳敏君、王廣義在內的18位中國當代藝術界最具影響力的代表…所有被重點強調的關鍵詞都傳達出這個展覽的與眾不同。

昨天,展覽的承辦方之一,蘇州美術館的常務副館長楊文濤接受了記者采訪。“作為一個傳統文化積淀深厚的城市,蘇州早在400多年前的明朝中后期時,就是當時中國‘當代藝術’的發源地。”對明清文人文化素有研究的楊文濤給出了一個有趣的觀點。

他發現,在“玩好之物,以古為貴”的明朝,在盛世收藏之風中出演重要角色的一直是宋代字畫與瓷器,可是到了經濟更加發達、風氣更加開放的明朝中后葉,擁有“手工藝之都”地位的蘇州人突然變了口味,喜歡起同時代人的作品來了,而且還有財大氣粗的徽商推波助瀾,“吳門畫派”領軍人物沈周的畫、治玉高手陸子剛的“子剛牌”漸漸成為時人追捧的高價奢侈品。——如果從“當代”這個時間概念來粗略定義“當代藝術”的話,蘇州人果真在顛覆好古之風的同時,狠狠地推動了一把中國彼時的“當代藝術”。

然而,僅僅回答蘇州與“當代藝術”素有淵源這個問題是不夠的,蘇博新館開館之際舉辦的當代藝術展并沒有引起太多關注的事實說明,以當代人的情感體驗、思想交流、精神共鳴等等為訴求的“當代藝術”與當代人之間似乎還有不小的距離。“事實上,即便是在學術界,‘當代藝術’仍然是一個十分模糊和開放的概念;而且在全球化愈演愈烈的今天,不同國家、地區中產生的‘當代藝術’有時甚至是大相徑庭。

”楊文濤說。他仍以明清時期的蘇州為例,“經濟富足的蘇州,在明清兩際產生了大批私家園林,這就類似我們今天的房地產業;參與設計、造園的文人為這些城市山林注入了相當豐富的藝術細胞,我們今天看來,這些已經成為世界文化遺產的古典園林完全就是一座很當代的裝置作品,不是嗎?

”接下來,“房子起來了,園子造好了,家具陳設內部裝修要跟上,文人氣十足的明式家具出現了,竹木牙雕文玩清供出現了,物質解決了,精神愉悅也必須考慮到,高雅的昆曲唱起來了,紅氍毹上的‘家班’出現了。所有由當代人創造的當代藝術就是這樣來自生活、影響著生活。
”——正因為蘇州曾經如此強勢地在中國傳統文化和藝術發展史上參與過、建設過,由此蘇州才擁有今天在這些領域內的深厚底蘊。楊文濤表示已經準備為“相嵌蘇州”申請圖像商標,因為他希望這個概念能慢慢延伸為展示蘇州文化形象的一個窗口和平臺。所謂相嵌,包含了相互植入的意思。將當代藝術嵌入蘇州,既是為一種深厚的傳統文化注入創造的生機,同時也是賦予當代藝術以傳統文脈的聯系。
所有的藝術從誕生之際就有著鮮明的時空印記,要想跨越不可再生的時空,它自身首先必須進行創造性的轉換,必須適應新的時代條件和社會情形。與此同時,當代藝術也并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它作為當代人的一種精神創造,應該是有源之水,有本之木。此次展覽邀請了中國當代藝術界一些頗具代表性的藝術家,諸如方力鈞、張曉剛、岳敏君、王廣義、周春芽、何多苓、祁志龍、隋建國、展望等等,都是中國當代藝術的象征性人物,他們的作品早已經作為中國當代藝術的重要標志,為世界藝壇所矚目。
他們成功的關鍵原因就在于其作品不僅反映了當代中國人的生存心理,而且還創造性地轉換了自己獨有的傳統語匯。比如張曉剛、方力鈞和岳敏君對中國民間年畫的吸收和利用,周春芽、何多苓對“文人畫”情趣的發揮,以及隋建國對“中山裝”的挪用和展望對“假山石”的當代轉換等等,都堪稱是中國當代藝術在國際語境下創造自己獨特文化形象的典范。“從這些作品中,我們不僅看到了傳統與當代能夠‘相嵌蘇州’的可能;
而且,我們還有理由相信,蘇州語境可以成為當代藝術的一塊豐厚酵母。”楊文濤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