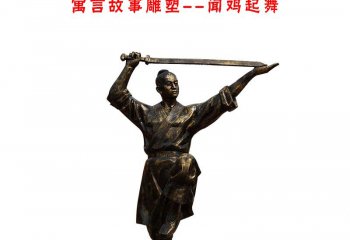有時,生活中的一次偶然會演繹出種種情形,而種種情形又會衍生成這樣或那樣的事實。這在成都女雕塑家沈允慶的故事中,一次又一次地得到了證明。前言雖然素昧平生,但她的親和與恬淡讓我們初次見面就有似曾相識的感覺。我想,大概每個人都會有同感。沈允慶的確是個無可挑剔的女主人。她非常盡心地把我安頓在她工作室外的木椅上,桌上擺滿了茶水、堅果和各種誘人的小食品。

她引以為自豪的工作室坐落在城南被稱為“藍頂”的頗有名氣的藝術(shù)村附近。這里聚集著6位相繼出生在60年代的雕塑家。沐浴在秋日慵暖的陽光下,我立即被層層的白樺樹擁抱著,林間令人驚喜地點綴著她的花,她的鳥,還有她那五彩繽紛、千姿百態(tài)的鍛鐵作品-魚,它們在婆娑的樹林中搖曳著、婀娜著、跳躍著、游戲著、燦爛著,和我一樣盡情地享受著這和平、寧靜、自由和陽光-真的,我被眼前的美景深深地感動了!第一章:藝術(shù)入門的故事直到18歲她對藝術(shù)仍然一竅不通。

連續(xù)兩年高考落榜讓她的父親大失所望。這位四川省博物館受人尊敬的資深考古學(xué)家一心指望自己的女兒成為歷史學(xué)家,讓她從小就抄寫和背誦大量的古文古書,當然包括所有聞名古今的唐詩宋詞。然而他最終放棄了這一遠大理想,建議她在博物館當臨時工學(xué)雕塑。18歲的天真女孩好奇地問:“啥是雕塑?”她的父親煞有介事地說:“雕塑就是捏泥娃兒嘛。

”那便是她對雕塑最初的理解和認識。沈允慶心滿意足地接受了這份新工作,開始學(xué)習(xí)泥塑和修復(fù)出土文物。“趙樹桐是我的啟蒙老師,是他把我領(lǐng)入了雕塑行業(yè)。晚上他常常教我們塑頭像。不久我就有了一樣新的愛好-為我所有的朋友塑頭像。我不僅塑造得很快,而且還像模像樣。從某種意義上講,這為我今后學(xué)習(xí)雕塑打下了一定的基礎(chǔ)。”她微笑道。沈允慶常常在成都附近的寺廟里一呆就是好幾個月,修復(fù)那些在“文革”期間受損的佛像。“我最早接觸的雕塑是廟里各種各樣的觀音菩薩,而我最初認識的浮雕則是當時新都剛出土的漢畫磚。

”沈允慶回憶著。1983年由于有人走關(guān)系開后門使她失去了臨時工轉(zhuǎn)正的唯一機會。在朋友們的催勸下,這位生性樂觀的女孩只身前往重慶,住在四川美院的招待所里,埋頭苦學(xué)專攻素描技巧。她每天完成兩張素描,請老師修改指導(dǎo),就這樣日復(fù)一日地堅持了兩個多月,她的基本功一天天進步了。

雖然她缺乏精致、細膩以及對素描幾何結(jié)構(gòu)的準確把握,但或許她的作品透著一股特有的質(zhì)樸和真實,從而彌補了繪畫專業(yè)技巧的不足。1984年她過關(guān)斬將通過了所有的考試,當她接到四川美術(shù)學(xué)院的錄取通知書時,許多人就連她自己都不敢相信她居然一下子就敲開了藝術(shù)的大門。
她迫不及待地將這個好消息告訴她正生病住院的父親。“你現(xiàn)在總算是個大學(xué)生了。”那就是他所有的回應(yīng)。第二章:活水掀起的激情通過在美院5年系統(tǒng)化的專業(yè)學(xué)習(xí),沈允慶有了一些自信,她總算擺脫了那種沒有藝術(shù)根基的感覺。畢業(yè)后她東游西晃,每年只出一兩件作品。
“我整整荒廢了10年的時間。”她無不遺憾地說。真正開始潛心創(chuàng)作是在1997年。一次偶然的機會,她結(jié)識了當時負責(zé)活水公園的策劃總監(jiān)美國藝術(shù)家貝特西.達蒙女士。初次見面后,達蒙女士對她的作品很感興趣。經(jīng)過溝通和交流,她們和成都另一位雕塑家鄧樂一起,開始了長達一年多的合作,完成了其設(shè)計、制作和安裝藝術(shù)作品。這是沈允慶第一次參與公共環(huán)境與雕塑的創(chuàng)作設(shè)計。
作為成都府南河綜合整治工程的重要部分,以魚形為整體設(shè)計的活水公園本身就是一件非常精美的藝術(shù)品,它是世界上第一座以水為主題的城市生態(tài)環(huán)保公園。曾獲“中國環(huán)境教育典范”、“國際優(yōu)秀水岸獎”等多項國內(nèi)外褒獎和榮譽。的確,經(jīng)歷了相當長的時間,沈允慶才發(fā)現(xiàn),世上沒有任何東西像雕塑那樣讓她如此癡迷不悔,如此忘我投入。
而且,她一旦開始,便欲罷不能。“我喜歡魚。它們很簡單,卻無比生動。”于是就誕生了她的系列作品“魚”。我相信它們給許多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塑得最多的還是胖女人-而且大家也比較認同。雖然我也用模特,但我更多的是在做我自己。我就是覺得胖女人特別可愛。”她咯咯地笑了。瀏覽她的系列作品“風(fēng)韻”,的確“豐”姿綽約,同樣楚楚動人!第三章:“大拇指”帶來的福音2000年由于與某房地產(chǎn)公司簽訂了合同,沈允慶必須在20天內(nèi)趕制完成使她飽受爭議的“大拇指”,為此,她承受了不少煩惱與壓力,每天不得不心急火燎地忙于制作現(xiàn)場。
在這令人并不愉快的奔波途中,她總是瞥見路邊有家毫不起眼的鐵匠鋪。一天她在那兒偶然遇見一位朋友。“你會打雕塑嗎?”她隨便問道。“雕塑?我不曉得,我可以試一下。”鐵匠漫不經(jīng)心地回答說。這突如其來的念頭讓她異常興奮,于是她連夜做了一個很簡單的草稿,第二天興致勃勃地來到鐵匠鋪,在她細致入微的精心指導(dǎo)下,他居然打出了一件有模有樣的“作品”來。從此,鐵匠鋪成了她的工作室,二人開始了長達7年的合作,雖然,一位做雕塑的藝術(shù)家和一位做農(nóng)具的鐵匠在交流、理解和互動上并不總是那么容易。
“我只憑借我的直覺,而不是某種觀念。其實我在創(chuàng)作中很少有什么主題。我把一些點點滴滴的想法放在一起,慢慢地我的作品就出來了。有時,甚至?xí)a(chǎn)生一些有趣的錯誤,我干脆就將錯就錯地做下去。”她的言語中有種掩飾不住的熱情。
沈允慶喜歡并享受著在鐵匠鋪里的即興創(chuàng)作。“我覺得差不多了就讓他停下來。打出來的東西往往與我最初的草稿截然不同,我喜歡隨意的組合,拼湊成什么就是什么。那種創(chuàng)作帶來的喜悅和滿足無與倫比,感覺非常好!”她執(zhí)著于她的雕塑,經(jīng)常參加各種各樣的展覽和比賽,她喜歡與來自世界各地的藝術(shù)家交流思想和信息。
2002年沈允慶有幸成為中國唯一的女雕塑家參加了在北京舉辦的“國際城市雕塑藝術(shù)展”,在現(xiàn)場制作長達1個多月,其間中央電視臺“半邊天”欄目對她進行了《女性與雕塑》的專題采訪和報道。沈允慶漸漸地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藝術(shù)風(fēng)格。鍛鐵雕塑成為她作品的標志。“人們往往先認識我的作品,再認識我本人。他們中的許多人,就連一些老一輩的雕塑家都認為沈允慶是個男人,當他們見到我時顯得非常迷惑,甚至很驚訝。”她得意地笑著,臉上有幾分孩子氣。
沒有人能否認她作品中涌動的力量。那些看似破爛的、斷裂的、拉扯的、拼湊的銹跡斑斑的廢銅爛鐵在她的手下蛻變成交錯著真與幻、虛與實、動與靜的夸張的、變形的、復(fù)雜的、奇妙的藝術(shù)作品…后記她的一位閨中密友告訴我,只要和沈允慶在一起,你什么也不用擔(dān)心,她會安排好一切,照顧好每個人。我相信那是真的。在日常生活中,她是一個很女人的女人。
但是她的藝術(shù)作品卻沒有絲毫女性的柔弱和矯情。要真正玩味并抓住她作品里的精髓,你只需步入她的工作室。在那間寬敞明亮、樸實無華的大房子里,即便是最小的作品,看上去都很自然、很美麗。她作品中有些很中國的東西,透過那些精致、巧妙的細節(jié),如魚鱗上突現(xiàn)的古老的青銅文字,胴體上若隱若現(xiàn)的中國結(jié),不經(jīng)意地流露出來,令人心曠神怡,讓人浮想聯(lián)翩。
那些作品和選題沒有磅礴之勢,它們源自她對自然與生活的觀察,展示著一個開朗、執(zhí)著、獨立、自信、樂觀、雄心勃勃的單身女人特有的個性、情感和生活經(jīng)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