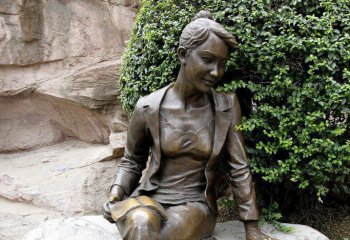《兩個(gè)英國女孩與歐陸》是一部關(guān)于對英國姐妹和一個(gè)法國男的愛情片。這部電影改編自小說,其人物關(guān)系和文本藝術(shù)品的關(guān)聯(lián)頗為相似。影片中經(jīng)常有信件和日記被交換,藝術(shù)品經(jīng)常被買來賣去,安娜和米西爾兩姐妹,同勃朗特三姐妹很相似,而法國男人克勞德也很像普魯斯特。

特呂弗和品利一皮埃爾?侯歌的對話在開場的演職人員表里通過特呂弗的注解呈現(xiàn)出來。在多年后,我們看到了這部創(chuàng)作于1956年的羊皮卷一般的小說原著手稿。這種對時(shí)間特性的分層疊放,決定了電影中其他一些文本方面的關(guān)聯(lián)。

這部影片對一戰(zhàn)的控訴,通過《加萊義民》的雕塑鏡頭被呈現(xiàn)出來。這尊像描繪了英法百年戰(zhàn)爭中的一個(gè)歷史事件,當(dāng)時(shí)加萊市正遭英國圍困愛德華三世承諾絞死6個(gè)人質(zhì)作為免加萊城的交換條件。這些人質(zhì)后來得到了寬恕,但羅丹捕提到了他們臨死前憔悴的時(shí)刻。影片尾聲的背景是1920年代,而旁白則涉及與雕像有關(guān)的一戰(zhàn)和1347年。

這個(gè)時(shí)間層面同樣含蓄而暖昧。對兩場戰(zhàn)爭的指涉,暗示了貫穿歷史的無益紛爭的延續(xù)。此處也有對修正主義歷史圖景的暗示。歷史告訴我們:1347年的英國是法國的死敵,但1914年至1918年間卻并非如此。這里是否有些對英法在一戰(zhàn)中結(jié)盟的暗示?我們有必要對影片提出質(zhì)疑,片名在英國女人和“歐陸”之間營造出一種雙重內(nèi)涵,它象征了英國和其他歐洲大陸國家的關(guān)系,影片一語雙關(guān),其展示的內(nèi)涵內(nèi)容引人深思。影片中通過雕像來描寫內(nèi)涵不僅僅只有上面一處,《加萊義民》雕像的出現(xiàn),也讓我們回想起米西爾在加萊失去純潔的場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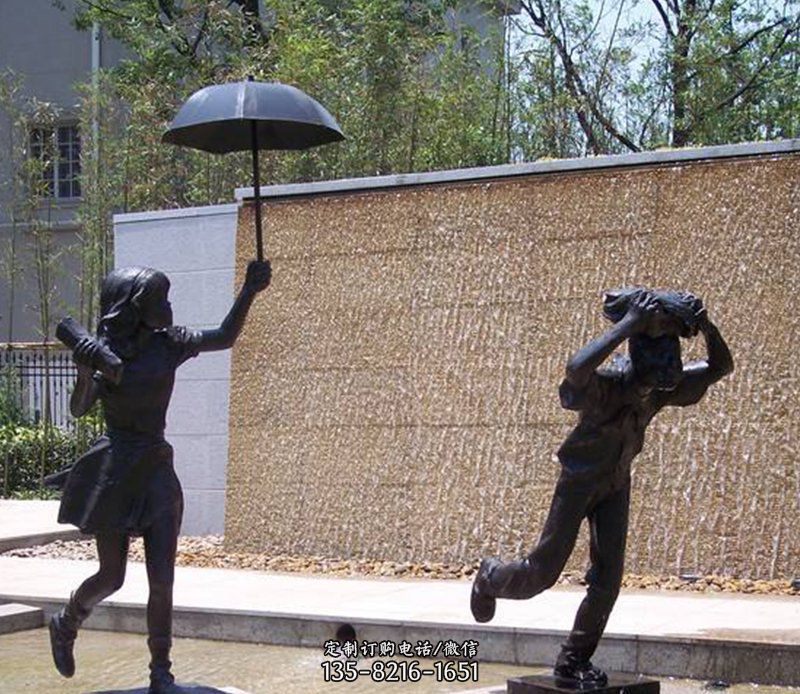
這是一種雙重獻(xiàn)身:米西爾為了接近克勞德,放棄了自己的清教觀念;而克勞德則犧牲了自己與她的戀人關(guān)系“將她當(dāng)作一個(gè)女人擁入懷中”,這件事情發(fā)生后,她便永遠(yuǎn)離他而去了。克勞德在米西爾離開時(shí)所感到的羞恥,作為他和安娜背叛米西爾的惡果,同加菜義民的羞恥感相照應(yīng)。例如接下來的鏡頭展現(xiàn)的是《烏戈里諾及其二子》雕塑,這個(gè)鏡頭成為連接克勞德在尾聲中的首次露面與雕塑《加菜義民》鏡頭的樞組。

在但丁的《地獄篇》中,烏戈里諾講述了自己如何被囚禁以及吃掉二子尸體的故事。這尊雕像位于一個(gè)裝飾性的湖心小島上,它具備封閉的構(gòu)圖形式,表現(xiàn)烏戈里諾躬身、他的孩子爬到他身上和膝下的情景。封閉的構(gòu)圖形式—人類面向自己的身體—預(yù)示著同類相食。一方面,這個(gè)鏡頭伴隨著畫外音對戰(zhàn)爭的評述而出現(xiàn),暗示出陽剛之氣在無益的爭斗中已經(jīng)消耗殆盡。

男人都死了,只剩下女人們,這是一個(gè)何等凄慘的世界,如同人間地獄一般。我們在尾聲里看到英國女中學(xué)生們一直在奔跑,她們作為歐洲的未來被呈現(xiàn)出來:一個(gè)沒有男人的未來。影片片名中所暗示的保守性—一英國女人們和歐洲大陸,在這里被顛倒過來了,書寫反轉(zhuǎn)未來。男性角色,烏戈里諾和他的兒子們,被孤立在小島上無法移動(dòng)。與此同時(shí),英國女孩們在陸地上自由移動(dòng)。

克勞德本來想成為一位作家,并不想生兒育女,某種意義上說,他已經(jīng)允許這種想法消磨掉他潛在的父性。雕像的靜止與女孩的飛奔之間的對比不止意味著藝術(shù)凝固了時(shí)間特呂弗強(qiáng)調(diào)說,藝術(shù)存在于時(shí)間里卻終被歷史改變。旁白指出了人們對羅丹的《巴爾扎克像》變動(dòng)不居的反應(yīng),該雕塑的社會內(nèi)涵隨著時(shí)代變化幾經(jīng)浮沉。自1920年代以后,世人對羅丹作品的態(tài)度也發(fā)生了一些變化,其作品的聲譽(yù)在1930年代急劇下滑,于1950年代開始復(fù)興,到1960年代已得到相當(dāng)一部分人的認(rèn)可。
這部電影結(jié)尾部分的悲劇基調(diào)平衡了苦難和詩意的正義。這樣看來,結(jié)尾的作用和主流電影的尾聲十分相似。電影評論家愛德華?布拉尼根認(rèn)為:“尾聲的意義,就是一部電影的情節(jié)中含蓄的道德規(guī)訓(xùn)。”然而《兩個(gè)英國女孩與歐陸》的結(jié)尾比一則簡單的道德訓(xùn)誡還要含混得多,讓人深思。尾聲不僅反思了這些體驗(yàn),而且拓展了影片。
羅丹美術(shù)館成了克勞德的記憶舞臺,其中雕塑和它們的故事也得到演繹。借助尾聲中對時(shí)間、歷史、記憶、藝術(shù)和影片的物質(zhì)特性本身進(jìn)行反思,影片營造出一種散文化的空間,可謂恰到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