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7日,坐落于天府藝術公園的成都市美術館新館正式向公眾開放,兩座新館及其開幕首展——2021成都雙年展也就此拉開序幕。受此前疫情影響,本屆雙年展取消了開幕式,并需要觀眾提供48小時內核酸報告。自上周成都全域轉為低風險后,通過在成都美術館公號上預約、現場出示健康碼即可參觀。

于是,上周末——11月27、28兩日,每天5000人的預約名額被迅速約滿,一批又一批熱情滿滿的觀眾涌向2021成都雙年展展場,親身感受這場國際化、高水平展覽為這座城市帶來的藝術享受。今日下午,在2021成都雙年展現場,成都市美術館副館長肖飛舸告訴紅星新聞記者,這場展覽讓成都觀眾們有機會在家門口欣賞、了解目前最新、最頂級的當代藝術,對整個城市審美水平的提升都具有重要意義。

“超融體”——2021成都雙年展,是今年成都乃至全國規模最大、藝術水準最高的雙年展。這場規模和規格都極為可觀的大展,邀請到了來自全球35個國家和地區的272位優秀藝術家,包括安尼施·卡普爾、托尼·克拉格、奧拉維爾·埃利亞松、卡斯滕·霍勒;張曉剛、周春芽、曾梵志和徐冰等。他們帶來了506件精彩紛呈的藝術品:從傳統的架上油畫到前衛的新媒體影像,從高達數米的巨型雕塑到想象力超凡的裝置,幾乎涵蓋了當代藝術的所有類型。

在當代藝術館的主展廳內,卡斯滕·霍勒的燈光裝置作品《十進制時鐘》牢牢吸引了所有觀眾的鏡頭和目光。在光線略暗的大廳內,這件碗狀造型、散發著金色和紅色柔光的“時間之燈”,有著攝人心魄的魅力。今年60歲的霍勒,最特別的背景就是他從科學領域跨界到了藝術圈——1993年,他離開科學領域,轉向藝術創作。或許是因為科學家出身,霍勒的藝術作品既富有科技感,也充滿實驗性。這件《十進制時鐘》是一個“功能性時鐘”——110個霓虹燈環代表了一個完整的白天和黑夜,它們分成10個小時,100分鐘和100秒,每11個環代表一個小時,分與秒則都是由里至外,從最小的環開始計算相加。

這盞“時間之燈”幾乎正對著英國著名雕塑家托尼·克拉格的作品《直立》。作為英國最負盛名的后現代主義藝術家,今年73歲的克拉格一直被藝術界認為有取代雕塑大師亨利·摩爾的勢頭。克拉格的雕塑作品雖然靜止而立,卻仿佛有一種無名的旋律縈繞其間。充滿矛盾的物體的幾何理性美,也充滿幻想和詩意的材料與色差。現場這件作品的外觀,看起來像是許多堅硬的管道或圓鞘重疊在一起,然后被一把無形而鋒利的刀削成現在的模樣,在四壁光滑的人造空間內,這些形狀涌動著、生長著,充滿了原始生命力。在展廳另一側,安尼施·卡普爾的兩件鏡面裝置作品《淺綠間紅蘋果》和《隨機三角鏡》最為吸睛。

兩件作品都運用了高科技光學原理,前者看起來是一個綠色光滑的凹陷鏡面,站在“鏡面”前,人影會倒過來出現在鏡面上方;而后者則擁有許多切割面,仿佛一枚巨大的鉆石,其折射出的光影又別有一番意味。只要是對當代藝術略加了解的人,對卡普爾的名字便不會陌生。這位出生于20世紀50年代的印裔英國藝術家,在國際當代藝術界成名已久,經典作品也遍布世界各地,陳列在芝加哥千禧公園的那件銀色雕塑《云門》,已經成為那座城市的藝術名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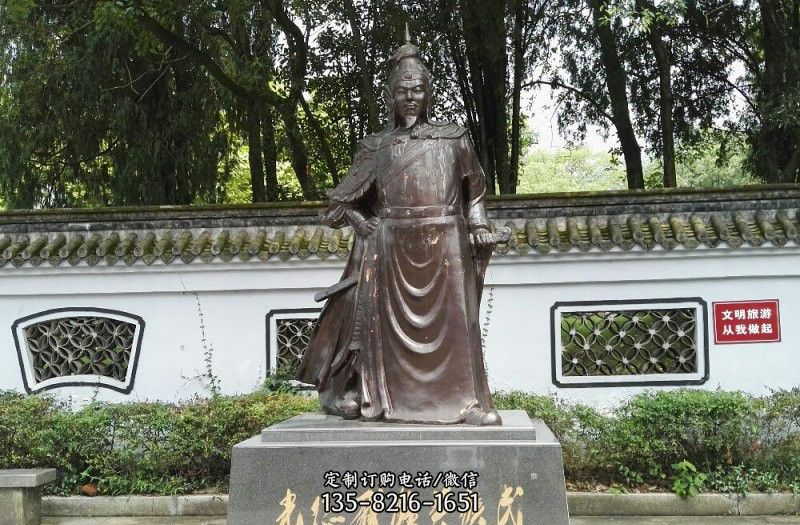
卡普爾以大型雕塑作品聞名,其實他的小型雕塑和裝置也令人印象深刻。他善用簡單的曲線結合凹洞和凹陷的方式,營造出一種讓人凝神的氛圍,被人稱為當代藝術界的“魔術師”。藝術家這次沒有選擇他慣用的顏料和石頭,而是選擇用鏡面來制作這件作品,他希望觀眾們在這兩件作品前駐足的同時,也能反思其周圍的環境和自身。

另一位著名藝術家奧拉維爾·埃利亞松,此次參展作品的名字很別致:《你正發生的、已經發生、即將發生》。這位出生在冰島的藝術家,可謂現今當代藝術界最炙手可熱的人物之一,他以大型裝置作品而聞名遐邇,曾在倫敦泰特美術館創造過一輪巨大的“太陽”,在紐約架起過四條緞帶般的“瀑布”,還在丹麥奧爾胡斯市打造出一道彩虹…這次他帶來的作品更加空靈——沒有實物,只有光影:七盞彩色聚光燈對準一面墻,組成了這件圍繞著光線、陰影、顏色以及觀眾互動而形成的裝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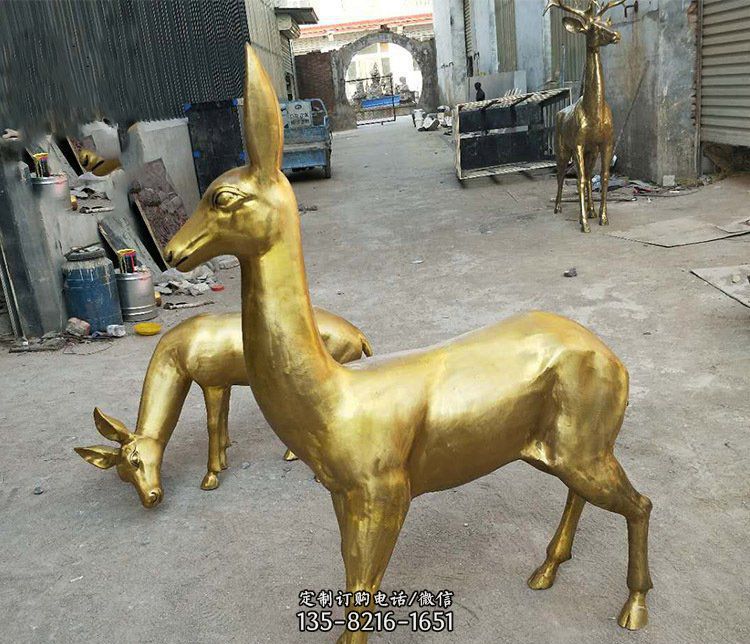
紅星新聞記者在現場看到,圍在這件作品前的觀眾以年輕人居多,他們興奮又好奇地排著隊,挨個兒走到燈光和墻壁之間,“激活”作品——觀眾的影子在墻上以7個剪影的排列形式出現,并且剪影輪廓會隨著人的移動,產生顏色強度和比例的變化,從而點染出時間的流動。

張曉剛為本次成都雙年展帶來的兩幅油畫是《2020年三月的某一天》和《對話》。暗黃色調的畫面,依然透著藝術家特有的那股沉靜、深思的氣質,也依然貫穿了“時間”這一核心主題。可以想象,大多數人在看到《2020年三月的某一天》這件作品的名字時,都很容易第一時間想到如今仍在對我們生活造成影響的這場疫情。
這也是藝術家想要表達的感觸之一。2020年獨有的“集體時間感”體現為驟然減速的、甚至是近乎凝固的時間。在隔離期間,張曉剛第一次嘗試用極慢的速度去完成一幅畫作。那手電筒射出的柔和光錐,朝著天空的方向,也指著未來的希望。肖飛舸告訴紅星新聞記者,徐冰這件作品別出心裁之處,是沒有通過顏料的調配來模擬三維效果,而是通過對光的調配來建構。“很多觀眾都在這件作品面前停留很久,反復比對觀察正面反面。
”此外,本次雙年展的多媒體和影像藝術作品也是一大亮點,精彩紛呈。陳粉丸的《轉運花園》頗有幾分草間彌生“無限鏡屋”的意味;田曉磊的《后人類博物館》系列影像可謂腦洞大開,奇趣橫溢;孟柏伸用傳統手工徽墨制成的“墨燈”裝置,和高揚模仿熱帶雨林天氣聲音的《沙漠雨笙》,都既吸引觀眾眼球,也值得回味思考。在金黃銀杏葉的映襯下,中國當代藝術在成都迎來了2021年的一個“高光時刻”,可以預見的是,這道光芒還將一直照耀這座城市直至明年,而它留下的更深遠影響,則將伴隨我們更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