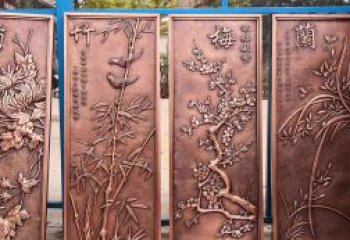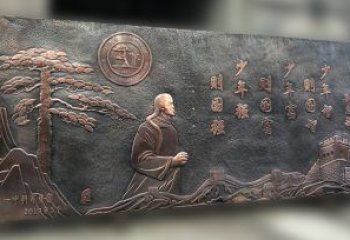1925年,在《再論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中,魯迅說:“悲劇將人生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當站在克孜爾石窟前,應該能真切體會到魯迅筆下的悲劇重量。躲過了一千多年來的時光沖刷,卻在近代被人為暴力掠奪,如今流散世界各地。

克孜爾石窟,古時稱作“耶婆瑟雞寺”,是古龜茲國的文化遺存。古龜茲國為西域三十六國之首,而克孜爾石窟又是古龜茲王國境內最大的石窟寺群,在西域地區首屈一指。這里曾經是佛光之城,石窟僧院,壁畫雕像,繽紛滿堂;又有高僧講經,徒眾研習,貴人參拜,凈人勞作于其間,儼然一個佛國世界。佛教的光輝以這里為節點,開始輻射到中國內地,并對中國文化產生方方面面的影響。大約從公元10世紀以后,龜茲王國不復存在,此地居民流散,信仰轉移。這里的石窟群落也漸次湮沒,佛像大半被毀。

然而更沉痛的災難還在后面…19世紀中葉,隨著工業革命的完成,世界上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走向壟斷資本主義階段與對外侵略擴張的方向。上個世紀之交的中亞探險考察熱,便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產生的。而新疆及河西走廊地區,是中古時期著名的絲綢之路途經地,遺留著大量的古代文化遺跡。

當時,在新疆克孜爾,先后來了俄國人、日本人、德國人、法國人。他們都沒有空手而歸,而尤其以德國人的“收獲”最多。德國皇家吐魯番探險隊最初是由當時德國著名的畫家、佛教美術家、柏林民俗學博物館印度事務部主任阿爾伯特·格倫威德爾組織的,考察時間從1902年11月到1903年3月,重點在高昌故城。格倫威德爾作為專業學者,主張就地研究,因此當時的收獲主要是那里發掘出梵文及回鶻、蒙古、古突厥、漢、藏語文的寫本,還有泥塑、壁畫、木雕、木板畫以及大量的摩尼教、景教文物,共計46箱文物,每箱重約37.5公斤。

這一次的收獲,在德國漢學界引發大轟動,連德皇本人都注意到了,還特別組織了一個委員會,由軍火大王克努伯和德皇以個人名義提供資助,在這以后,他們盜取的中國文物都用克努伯兵工廠的炮彈箱盛裝。這在以后還引發了一段驚險的插曲,1945年,蘇聯紅軍率先攻入柏林,看到這些炮彈箱,以為是炸彈,準備集體銷毀,而其中一箱的文書掉在地上,才使得這批文物躲過一劫。

第二次考察,格倫威德爾因病不能前往,勒柯克于是陰差陽錯地被推上前。勒柯克1860年出生在柏林一個富有的酒商家庭,從小就桀驁不馴,后被學校開除。他父親一心想讓他繼承家業,先后送他到英國和美國接受商業訓練,兼習醫術。1902年,勒柯克自愿無薪進入柏林民俗學博物館工作。于是,在第一次探險的領隊身體不適,另一名隊員又不在的情況下,勒柯克成為第二次探險的隊長。

不過他們事先約定,一旦格倫威德爾身體好轉,隨時入隊接替勒柯克當隊長。與格倫威德爾不同,勒柯克是個狂熱的收集分子,堪稱壁畫收割機,他恨不得將整個石窟搬去歐洲。這次探險時間在1904年9月到1905年11月,經費充足,達到3.2萬馬克,其中1萬馬克是德皇資助,軍火商克努伯也贊助部分。人數只有勒柯克和巴圖斯兩人,后者是博物館的勤雜工,具有豐富切割壁畫的經驗,是唯一一個全程參與四次考察的人。這一次勒柯克帶回103箱文物,每箱重量為100到160公斤不等。

其中一幅摩尼教創始人摩尼的壁畫,有近6尺高,保存完整,此畫一直被勒柯克認為是他一生之中發現最重要的一件。在柏孜克里克,他們還用弧形鋸暴力取走15幅大型佛教壁畫。第二次考察中途,格倫威德爾病愈,臨時趕赴新疆,勒柯克奉命與之會合。此時,勒柯克已經聽到敦煌藏經洞的傳聞了,在格倫威德爾和敦煌之間,勒柯克猶豫不決,最終決定通過拋硬幣的方式來做取舍,而硬幣結果指示還是要與格倫威德爾會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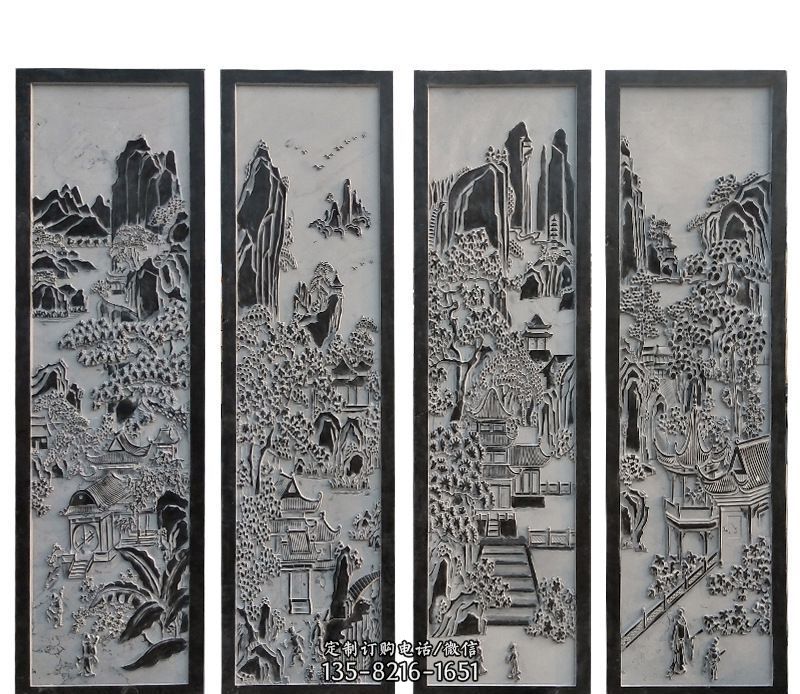
因為這個,勒柯克錯過了敦煌藏經洞的驚世大發現,這也為他們二位的矛盾埋下了伏筆。注意,這還是1905年,勒柯克半個月左右就能從新疆趕到敦煌,如果真是這樣,敦煌的遺書及壁畫也很可能遭到勒柯克的荼毒,而不會留到第二年才趕到此地的斯坦因。誰能想到,敦煌的命運就被這枚硬幣給暫時解救了。1905年12月,勒柯克與格倫威德爾在喀什碰頭,德國皇家考察隊的第三次考察活動正式開始。

這一次考察隊一共四人,格倫威德爾和他帶的一名翻譯助手波爾特,勒柯克和巴圖斯。名義上由格倫威德爾領隊,但是他身體不好,指揮干活的主要還是勒柯克。也就是在這次考察中,他們來到了克孜爾千佛洞,格倫威德爾的主要精力放在臨摹壁畫上。

而勒柯克則被克孜爾壁畫震撼住了,據他自述:“這里的壁畫,是我們在中亞任何地方所找到的最優美的壁畫,它包括傳統中佛陀的種種形態和他所處的種種場景,它們幾乎都具有古希臘風格。”然而,他卻肆無忌憚地暴力攫取。可惜的是,這樣偉大的杰作,被揭取到柏林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毀于盟軍轟炸。克孜爾壁畫成為此次最重要的“收獲”,勒柯克暴力攫取壁畫的行為也引起格倫威德爾的不滿,他堅持認為應把壁畫放在它原來的地方研究。

而勒柯克早已想好了借口,他認為這些壁畫在這里會受到盜寶者及地震的破壞,將它們打包帶走才是萬全之計。為此,他倆幾乎到了絕交的地步。即便這樣,第三次考察依舊是滿載而歸,共有128箱文物被運往柏林,每箱70多公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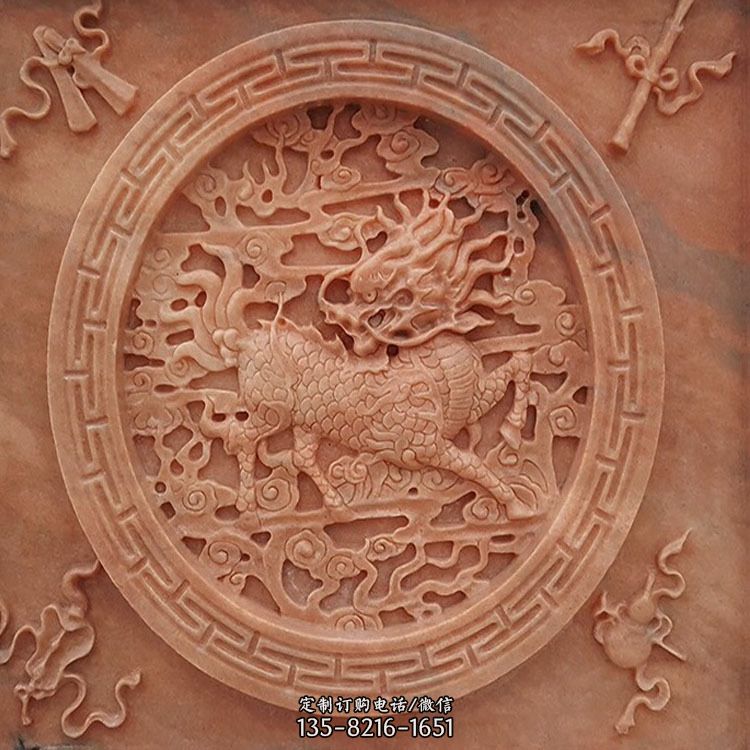
1913年1月,在第三次考察結束6年后,第四次考察開始。這次只有勒柯克和巴圖斯兩人,且阻力比之前更大。當時清王朝倒臺不久,新疆局勢動蕩,德國外交部對勒柯克發出安全警告,但勒柯克已經近乎瘋魔,他簽下了生死書,不顧一切奔赴新疆。這一次他們主要調查了庫車、圖木舒克地區的千佛洞。
到1914年2月撤離,他們共弄到156箱文物,每箱重約70到80公斤不等。統計起來,德國人這四次考察一共盜取新疆地區文物433箱,共計3.5萬多公斤。其中各類壁畫達到630多幅,據勒柯克自己說:“這四次考察所取得的成果,絕不亞于俄法英日考察家們的收獲。”它們對研究佛教是如何從中亞向中國內地傳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佛家講究因果報應,皇家考察隊的這兩位主要人物結局怎樣呢?在此也簡單敘述下:勒柯克1930年就死了,死時境況慘淡,一戰令他經濟破產,獨子也死于戰場;
而格倫威德爾則在1935年死于精神病院。當年,勒柯克打著保護的借口將這些壁畫暴力揭取,但事實上,掠奪者對他國的文化遺產并沒有真正的敬畏保護之心。1921年,為了籌措資金,勒柯克將部分壁畫放在藝術市場上售賣,據說有近40幅作品被賣到了美國。但據調查,被售出壁畫的數量也遠不止40幅,光從柏林售至美國的克孜爾石窟壁畫就達49幅之多。
售出的壁畫又開始顛沛流離,分散收藏在歐美及日本各大官方或私人機構中…此外,還有少量壁畫被勒柯克作為禮品贈送了出去。1918年,勒柯克將兩塊克孜爾石窟壁畫作為禮品贈送給匈牙利布達佩斯東亞藝術博物館第一任館長費文奇。最令人痛心疾首的,是相當一部分的壁畫毀于二戰戰亂。1945年二戰結束前夕,柏林民俗博物館為防止文物遭受戰亂毀壞,曾將各類文獻及雕塑裝入木箱搬出柏林。此時戰事瞬息萬變,工作還在進行時,蘇聯紅軍就打進柏林了。
據彼得·霍普科克講,蘇聯紅軍攻陷柏林后曾在護城河中打撈出5箱文物。又在動物園的一個地堡中,搜出了至少10箱文物。這些都被帶到了蘇聯。不過最大型的壁畫精品,由于被水泥固定而無法轉移,在盟軍的轟炸中化為灰燼。包括最精美的28幅大型壁畫。據稱,這批文物在二戰中至少損失了百分之四十。反手撥弦自在彈,盛唐流韻裊千年。
無數壁畫在時代的潮流中被撞擊得七零八落,在大浪淘沙中流落異國他鄉,在炮火閃鳴里粉身碎骨。這對世界無疑是一場徹頭徹尾的悲劇,暴力掠奪走的不只是極美的壁畫,更是現代文明社會之下的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