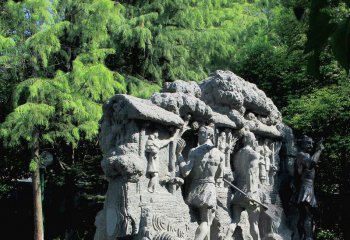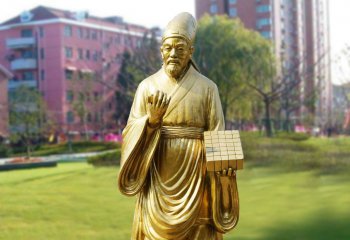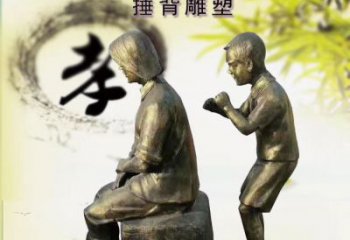5月6日,一個慵懶的周日下午,脫掉大衣的人們換上短袖,北京城匆匆迎來夏天。從山東來的大姐鉆進城南天橋劇場附近的一家食品店,想買串糖葫蘆,被店員脆生生的北京話頂了回去:“大熱天兒的,誰吃它呀?北冰洋挺好的,您不來一瓶兒?”旁邊小區的大媽進了店門,熟練地向左拐,抓起兩個“果子面包”,一分鐘不到就結完了賬。老伴在門口等她,他講不出幾十年來獨愛這一款的確切理由,或許是喜歡帶著核桃仁香味的筋道,或許拆慣了浸著黃油的蠟紙包裝。

門楣上,暗紅色的招牌上噴著鮮黃的大字——”百年義利”。這個隸屬于北京第一輕工食品集團的百年老店是一家國有企業,現主營“義利”面包糕點和“北冰洋”冷飲。人們對它的記憶,無一例外地指向春游前把“果子面包”塞進布書包的那一刻。
差一點,這些熟悉的滋味,就隨著兩代人的童年一同消失。廣義街5號南五環外的義利大興廠區里,辦公區的一角掛著小電視,液晶屏上的廣告寫著:嘿兒嘍蜜,老北京話里,是吃凍柿子自得其樂的意思。趙占中來自河北保定,他講不出這句北京土話,只知道這個在京城打響名號的企業并非土生土長,是建國初響應“繁榮首都”的號召,從老上海的租界區遷徙而來。
搬到大興廠區前,一直在城內廣安門附近的廣義街5號。1951年,義利遷至北京后,在原宣武區廣內王子墳建立新廠,據考證,由于義利后發展成京城著名的食品企業,廣內王子墳便因此更名為“廣義街”,沿用至今。新京報記者尹亞飛翻拍附近的老居民都能講出街名的來歷:“廣”是廣安門,“義”是義利食品廠。從1951年到2001年,“義利”在這里度過了整整50年。
在工廠后墻根下住了63年的老周,自稱聞著“義利”味兒長大,對昔日的輝煌記憶猶新——七八十年代,等貨的汽車在后門排起大隊,延綿兩三百米。小推車直接到生產線上去等貨,出來一箱拉走一箱。凌晨四五點送到西單、王府井等幾個大的銷售點,聽說已經有人等在那里,連軸轉的機器從早到晚響個不停。“果子面包”是從老上海的“圣誕面包”演變而來。起初夾的是新鮮水果,可北京除了四月杏、六月桃兒,新鮮的時令水果很少,就把水果換成了果仁。自記事起,趙一發的父親就在義利餅干車間配料,他十幾歲時也跟著父親學工,在餅干車間待過短短幾個月。
6分錢一兩的動物餅干對趙一發來說過于奢侈,“5分錢,能買一碗豆腐腦,配一個火燒。”他最常吃的,是父親帶回來的“餅干頭兒”:下腳料烘烤出來的,手指頭那么寬,歪七扭八的,剁成一塊一塊兒。當時間來到了1976年,全廠已經有兩千多工人。誰也不會知道,兩年后鄧小平宣布中國走上改革開放之路。他們的和企業一樣,都將迎來命運棋盤的改變。賣一個賠一個的果子面包1979年6月,18歲的李奇接到回城通知信時,正在通州農村的日頭下割麥子。在申報的四個工作志愿里,他最想去首鋼當一名翻砂工,理由很簡單:重體力勞動崗,工資33塊,比其他單位高一大截。
結果他沒有被錄取,來到義利食品廠的面包車間。和許多五十歲以上的國企職工一樣,他記得自己最初十年間的工資變化,那是一條不慌不忙的上升曲線:79年18塊,81年20多,86年40多,89年60多。改革最初是何時從廠里開始的,沒人給出一個確切的答案。
但大部分人憑感覺相信,1984年算得上一個重要節點。1984年4月,”義利“在西單南口的西絨線胡同開了一家西式快餐店。門口擺著”空調開放“的大牌子,走進去輕音樂撲面而來。洗完手,水池旁有一個熱風機,不到1分鐘就把手烘干。取餐處,食品都放在一個托盤里,方便又新鮮。除了漢堡包和火腿三明治,廚師還從香港學了咖喱牛肉,服務員是車間里選出的最年輕漂亮的女工。就在那一年,工廠第一次迎來了美國人,但隨之而來的改變,全廠上下無人預料。
生產餅干的國際大廠納貝斯克主動找過來,希望成立合資企業。義利占股51%,對方占49%,企業名稱叫“義利-納貝斯克”,義利放在前面。對時年34歲,任義利食品廠勞資科的胡會中來說,起初只覺得餅干車間搬走了,廠里少了一波人。但合資后,動物餅干、蘇打餅干款式全部取消,改成納貝斯克的款式。從那之后,北京天津的顧客只知道“樂之”、“富麗”,不知道是義利生產的,義利的名氣逐漸被取代。
很多年后她才明白,外國人看重的是義利的市場,“人家按經濟規律做生意,咱們那時候對市場一竅不通,只知道國家派多少料,咱就生產多少。”義利面包舊時的生產工藝。新京報記者尹亞飛翻拍但在當時,吃慣了國家撥款的“義利”沒有意識到變化。
廠里覺得貸款也是國家給錢,不花白不花,從國外引進了11條生產線。“可市場丟了,創造再多也沒有用。”糖、油、面這些生產原料也從之前的國家配給變成自行采購,原料價格上漲,商品定價卻由物價局統一管理。果子面包4毛2一個,由于不能漲價,90年代初停產了,“再繼續生產,賣一個就賠一個”1992年《北京晚報》的一篇發章讓胡會中感嘆不已,標題是《義利面包哪里去了》。
“要不是消費者想著你呼喚你,估計這面包早沒了。”之后不久,果子面包恢復售賣。“多好的廠子,沒了”1996年至1997年的下崗大潮,風雨飄搖的義利未能幸免。當時工人和設備逐一離開,只剩空空的廠房。車間里,昔日的忙碌有序也不復存在。老職工印象最深的不是義利的產品,而是一塊5毛6一升的燕京扎啤,“成天待在宿舍樓里,一邊喝啤啤,一邊打撲克”。有人上班簽個到就走了,上外面干私活兒,“不垮行么?”胡會中倒是忙個不停,忙著安排職工下崗分流。有人罵她”干缺德事兒“、“光想著趕我們走”,每個職工見到她,都能講出家里家外一籮筐的難處。
她只能把廠里的情況如實相告,“廠子還不上貸款,工資開不出來,要說破產,那也就一句話的事兒了”。1995年,剛實行繳納住房公積金不久。一到15號開支的日子,會計就去找銷售催款籌錢,職工100元的工資,“湊夠90塊錢發下去那就算不錯,扣的10%,企業應交的10%,都交不上。
”糖果車間成了下崗大戶。前幾年,胡會中路過虎坊橋公交站,看見一個她經手的下崗老工人搖著小旗正維持秩序,“冬天也戴著大墨鏡,怕別人認出來”。她的心里五味雜陳。剛來廠時,她在酥糖車間幫工。五層高的糖果樓四面砌著蘇式紅磚墻,到處飄著香甜。80%的芝麻醬和20%的花生醬配成“二八醬”,外面涂上一層硬殼,黃色包裝紙包成大蝦的模樣,做成“黃蝦酥”。剛熬出的糖稀200度左右,倒在裝有循環水的巨大鋼案板上晾著。溫度適中后,小伙子把它們疊成一厘米厚一尺見方的糖塊。
夏天,胡會中最喜歡摸那個“水臺子”,滑滑的、涼涼的。有時饞了,看見糖塊兒打下來的渣子,她偷偷掰一點嘗嘗。如今,廠區僅剩的一幢老樓,因90年代賣給印刷一廠而得以保存。老周記得,老職工離開時,很多人哭了,念念不忘墻上的水泥,磨得像鏡子,“多好的廠子,沒了。”北冰洋的復興李奇在廣義街工作了16年,他最熟悉的是面包車間和一種看不見的生物——酵母。1988年,他來到“產品開發部”,研發面包生產技術。
練就了看一眼面團就知道原料配比準不準,面粉打的時間夠不夠,發酵的程度合不合適的絕活兒。但五年時間不到,由于沒有市場,“開發部”名存實亡。1995年,廠里正響應“退二進三”的改革政策——退出二環,搬進三環;退出二產,邁進三產。
5月份,他在南二環外一個300平米的廠房落下腳跟。和他一起被“甩出去”的承包廠,當年有十來個。這里原本是一個大型生產線停產后存放設備的地方,每年交十五萬租金的場地費。廠領導給了他50萬啟動資金,讓他開發新產品推向市場,“能把租金賺回來就行”。
于是,金穗面包廠從這里誕生。十幾個人,自負盈虧,李奇經歷了一次百分之百的創業。走出醒發室,他蹬上三輪車,把新研發的面包送進街頭巷尾的小賣部,之后幾年,自選超市如雨后春筍般冒出來,李奇看中了北三環的超市發,在那里開拓了第一家現場烘焙的“店中店”。
超市里,老年人看見海報走進來,拎起兩個打折的牛角面包;年輕人聞著香味兒走進來,捧走一盒剛出爐的奶油泡芙。五年下來,金穗給義利的固定資產增值將近一千萬。2018年5月8日,大興區,北京義利面包食品有限公司,面包生產車間,工人們正在忙碌。新京報記者尹亞飛攝那時的母公司義利食品廠,除了掛在名下的四五千名退休職工,已所剩無幾。所有員工都知道的一件事就是,“面包廠救了義利,置之死地而后生。
”2001年,金穗面包廠和其他面包廠合并,更名義利面包廠。2011年,李奇出任“義利”總經理,同時接手了兄弟企業“北冰洋”。接手后,他琢磨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北冰洋復出。90年代中后期,國際品牌“百事可樂”在政策鼓勵下收購了這家公司,曾在北京市場占據有統治地位的北冰洋冷飲,品牌被雪藏。2007年,北冰洋收回了品牌商標,但承諾“四年內不能生產碳酸飲料”。
十幾年過去,便利店的飲料柜里,塑料瓶和易拉罐早已塞得滿滿當當,玻璃瓶的包裝逐漸被遺忘。大量涌進京城的”北漂“喝著可樂雪碧長大,不認識苗條的瓶身上的“雪山白熊”。股東會上,李奇跟領導說,”賭一把玻璃瓶兒吧,老百姓找的是回憶。”他聲音洪亮,顯得底氣十足,但心里也并無十足把握。起初,廠里上了一條小規模的生產線,每小時生產18000瓶,沒想到一售而空。淺黃色皇冠形金屬蓋一打開,冰涼的瓶口冒起白煙,人們嘗出了原汁原味的“小時候”。
大叔想起了踢完野球,掀開蓋著棉被的箱子,抓起奶油雙棒塞進嘴里的那一刻,小棍兒上留下自己黑黑的手印。阿姨想起了自己攢過的糖紙,五顏六色的還夾在瓊瑤小說泛黃的書頁里。如今,義利和北冰洋已有1400多員工,一年的工資總額達到2個億。來日方長下午6點,大興廠區里,工人陸續走出車間,跳上班車回家。北冰洋車間還沒下班,清洗工倒掉玻璃瓶里喝剩的殘渣,掏出煙頭、冰棍棍兒、餐巾紙,再碼放到流水線上清洗。熱空氣堆積在屋頂,散發出有機物高溫分解時的嗆人氣味。“玻璃瓶清洗回收成本很高,洗不干凈有很大的風險。
大企業都撿省事的事兒去做,只有難事兒是我們生存的空間。”此時的李奇已十分清楚,義利早已不是當年的“大企業”。2018年5月8日,大興區,北冰洋生產車間,工人們正在對回收上來的玻璃瓶進行清洗。新京報記者尹亞飛攝他在廠區辟出幾百平米綠地,人工湖上豎起北冰洋汽水的雕塑。兔子窩在湖邊的籠子里,啃起了掰碎的切片面包。20歲的美院學生正往綠色油漆桶上刷彩繪,來這里做布景兼職之前,他從沒聽說過“義利”。
李奇坦言,年輕人和外地人不知道義利,一聽國產面包都覺得老派,企業也嘗試著改變。2018年5月18日,北冰洋義利園區北2門。兩位前去北冰洋義利旗艦店購物的老人,從北2門口走過。新京報記者尹亞飛攝義利的自營門店里,黑黑的“網紅臟包”擺在最靠近收銀臺的位置,努力吸引年輕人的眼球。
中關村的創業大街上,北冰洋贊助了一家互聯網企業組織的員工相親大會。李奇覺得,情懷和品牌是敲門磚,能做久了還是靠品質。“我的父親是鉗工,我也是靠手藝一步步走過來。每個人進廠學手藝都有師傅,師傅教他一些方法,他學會后在這里立業成家。幾代人都做這樣的事,就是瑞士的鐘表匠。”他覺得義利要走的路,來日方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