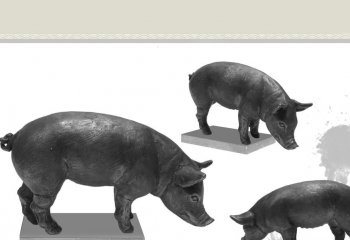在印度古典建筑學(xué)與堪輿理論中,人類在大地上建造的神廟是宏觀宇宙的縮影,同時(shí)又是人體微觀宇宙的投射,一座完美的神廟,其構(gòu)件之間的位置和比例需嚴(yán)格對(duì)應(yīng)人體的七個(gè)主要脈輪。從進(jìn)入神廟到完成對(duì)神像或林伽“覲見(jiàn)”的過(guò)程既是一場(chǎng)同宇宙本源的對(duì)話,又是一種逐漸深入自我并打開(kāi)身心的內(nèi)觀。他們恰恰崩潰于印度教的起點(diǎn):對(duì)混沌深淵的認(rèn)知,把悲苦當(dāng)成人之條件來(lái)接受。——奈保爾1第一次從北印回來(lái)時(shí)我曾矯情地發(fā)誓,“需要緩沖一年半載再去”。

事隔三個(gè)月,我又打臉踏上了南印的國(guó)土。沒(méi)錯(cuò),那些泔水垃圾場(chǎng)里的夜間巴士站,露天火葬亭里的嗆人濃煙,新德里貧民區(qū)猶如大型逃生游戲的街頭,齋普爾被司機(jī)強(qiáng)行拉去的黑幫染印廠,阿格拉差點(diǎn)從天而降掉進(jìn)咖喱碗里的壁虎,在被淹沒(méi)一半的瓦拉納西看夜祭時(shí)從恒河淤泥中爬上腳背的巨型潮蟲(chóng),燒尸河階邊以“為窮人買燒尸柴”訛詐的假祭司…依然會(huì)時(shí)不時(shí)出現(xiàn)在驚夢(mèng)中。
但更為清晰和鮮活的,是一種蜃景般的、模糊著現(xiàn)實(shí)與想象之經(jīng)緯的、幾乎稱得上如夢(mèng)似幻的錯(cuò)位感。一切都那么古老,一切又宛若新生,所有迷宮般的巷道都拽著我走向深處,所有的千年廟墟上都有人在哭你昨天的眼淚。記憶中的印度是明麗與幽黯交替的布料,也是剪輯師缺席的連環(huán)默片,或許就如奈保爾所說(shuō),這是一個(gè)虛懸在時(shí)間中的國(guó)家。對(duì)任何一個(gè)從那兒回來(lái)的人而言,從此往后,世界僅僅分為印度和非印度。
世界分為印度和非印度,而印度又分為北印和南印。以德干高原南側(cè)為界,兩邊的人們似乎相信自己分別生活在南北半球,并且互相以對(duì)方為反足人,完全不覺(jué)得有深入理解或彼此融合的需要。的確,北印是喜馬拉雅雪山、恒河平原與亞穆納河的世界,大一統(tǒng)的榮光在印度—雅利安人和外族人手中擊鼓傳花,孔雀朝的佛教窣堵坡與莫臥兒朝的伊斯蘭皇陵同時(shí)列入世界文化遺產(chǎn),印地語(yǔ)和英文占據(jù)不容置疑的語(yǔ)言霸權(quán)。南印則屬于印度洋、阿拉伯海、孟加拉灣、高韋里河與東西高止山脈,在次大陸上生活更悠久的達(dá)羅毗荼土著從未形成統(tǒng)一政權(quán),泰米爾語(yǔ)、泰盧固語(yǔ)、卡納達(dá)語(yǔ)、馬拉亞姆語(yǔ)…
各邦的語(yǔ)言與它們頻繁更迭的王朝一樣紛紜且互不相讓,印度教傳統(tǒng)有更繁復(fù)的怛特羅、更激越的情感表達(dá)、扎入更深更暗處的樹(shù)根。也許如這首古老的匿名濕婆頌詩(shī)所唱的:“人類看三種事物永不厭倦,星辰、火焰和流水;因此我看你也不厭倦,因?yàn)榱魉谀惆l(fā)間,火焰在你掌中,寰宇億萬(wàn)星辰形成在你呼吸之間。
”此次我從泰米爾納德邦的首府金奈入境南印,途經(jīng)三個(gè)邦十六座城市,計(jì)劃考察帕拉瓦、朱羅、潘迪亞、曷薩拉、毗奢耶那伽羅諸朝的三十余座中世紀(jì)神廟,其中一半以上至今仍是“活廟”。是的,比起泰姬陵這類完全成為景觀的墳?zāi)梗腋珢?ài)那些作為人們實(shí)踐信仰之現(xiàn)場(chǎng)的、會(huì)呼吸也會(huì)擊掌而歌的建筑,我希望在神廟的陰影中隱沒(méi)而凝視,因?yàn)椤胺悄怯幸磺е谎劬?因陀羅有一百只眼睛/你和我,只有兩只。
”普祭中的毗濕奴派婆羅門,賜福者之主神廟接吻的愛(ài)侶,賜福者之主神廟千柱廳2和同伴一起抵達(dá)甘吉布勒姆那天,正逢豐收節(jié)首日。街上的牛在突突車與摩托的縫隙間悠然穿行,脖子被系上了五光十色的鈴鐺,染了眉毛,點(diǎn)了額飾,牛角被涂成血紅或金黃。家家戶戶門口地上都畫著豐收節(jié)主題的“柯藍(lán)”裝飾:兩側(cè)是甘蔗枝,四角是菠蘿和燭臺(tái),中央是六芒星或愛(ài)心等幾何裝飾圖案。
擔(dān)任柯藍(lán)繪者的多是家中年長(zhǎng)的婦女,只見(jiàn)她們彎腰及地,紗麗垂足,手指拈著粉筆或蘸取面粉,專心于眼前的方寸之地,猶如辛勞的拾穗者。路面交通依然一片混亂,但這兒似乎要比北印寧?kù)o得多。豐收節(jié)是泰米爾納德邦重要的民間節(jié)慶,慶祝的是冬日將盡,太陽(yáng)進(jìn)入摩羯座,從此開(kāi)啟日頭漸長(zhǎng)的六個(gè)月份,一般落在公歷1月14日前后的三至四天。
名義上,該節(jié)的敬獻(xiàn)對(duì)象是吠陀時(shí)代的太陽(yáng)神蘇利耶,因而最隆重的第二日也叫蘇利耶豐收日,但和南印大多節(jié)日一樣,實(shí)際上主要給大家提供了吃香喝辣,走親訪友,以及最重要的,去神廟里敬拜三相神的契機(jī)。三相神自然并不包括太陽(yáng)神,僅指創(chuàng)世神梵天、護(hù)世神毗濕奴、滅世神濕婆,在虔愛(ài)主義的發(fā)源地南印諸邦,幾乎沒(méi)有專門供奉梵天的神廟,而成毗濕奴派與濕婆派二足鼎立的格局。
我前往觀看晨間普祭的賜福者之主神廟即甘吉布勒姆最大的毗濕奴派神廟,始建于11世紀(jì)的朱羅王朝,是108處毗濕奴“優(yōu)勝寶地”之一。早晨八點(diǎn)半趕到時(shí),婆羅門祭司已用層層疊疊的花環(huán)完成了對(duì)游行神像的裝飾,十幾個(gè)祭司正用大竹竿子穿起兩頂神轎,分別抬著毗濕奴及妻子拉克希米,在白底紅紋蓮葉華蓋下齊唱梵文頌歌。最小的祭司大概十三四歲,戴著眼鏡,面容沉靜,偶然忘詞,和其他人一樣上身赤裸,僅佩一條圣線;最大的可能有六十以上。領(lǐng)拜者手握火炬和銅鈴,對(duì)著轎上的神像行光明禮。
五步開(kāi)外立著三排雙臂交抱的中年婆羅門,他們是專司唱誦的儀仗隊(duì),不僅前額畫上了毗濕奴派特有的“山”字圣印,以區(qū)分于濕婆派的“三”字圣印,連兩條大臂、胸口和肚臍也一絲不茍畫上了。這種統(tǒng)稱為提拉卡的圣印是印度教信徒最可見(jiàn)的身份標(biāo)簽,神廟內(nèi)的多數(shù)人也絕不憚?dòng)谠谥苌碜钚涯康牡胤浇o自己貼上標(biāo)簽,作為其信仰派別的彰顯。毗濕奴派近十個(gè)主要支派的額標(biāo)就各有微妙差別,更不用提底下蕪雜的次分支。
賜福者之主神廟的祭司們顯然屬于南方大派室利系:構(gòu)成“山”字外圍的白色U形以檀香膏畫成,再用朱砂涂抹中間的紅豎杠——精確地說(shuō)是纖長(zhǎng)的水滴形。《奧義書》中將“山”的三道豎解為三部吠陀經(jīng),或者“”口訣的三個(gè)音節(jié),但若你在街上拉住一個(gè)室利系的普通信徒詢問(wèn),他多半會(huì)告訴你外圍兩豎代表毗神的尊貴兩足,而中間一豎代表拉克希米:“要接近我主必須先通過(guò)女神傳話…
”這樣,通過(guò)辨識(shí)額標(biāo)和衣著,兩個(gè)陌生人在路上一照面,甚至不用開(kāi)口說(shuō)話,對(duì)于彼此的教派、種姓、宗族都已有了籠統(tǒng)的印象。南印人并不以此為懼。知道自己是誰(shuí),屬于哪里,知道自己在紛紜世界中的確鑿位置,這就如同知曉每年的季風(fēng)何時(shí)過(guò)境,或雨季何時(shí)終結(jié)一樣重要。我猜想這是在此地生活的先決:混沌登峰造極之處醞釀著最嚴(yán)苛的秩序,數(shù)千年來(lái),種種令外人無(wú)措的稱號(hào)、儀軌和等級(jí)是印度教于現(xiàn)世的颶風(fēng)中央提供的臺(tái)風(fēng)眼,這里面有一種悖論的民主。
豐收節(jié)柯藍(lán)用面粉起草柯藍(lán)的婆婆3甘吉布勒姆是中世紀(jì)早期一度稱霸南印的帕拉瓦王朝的舊都,印度教七圣城之一,因?yàn)橥瑫r(shí)是濕婆、毗濕奴、薩克蒂女神信仰的中心,也稱“三神居”。公元7世紀(jì),這是玄奘在天竺所踏足的最南端的土地,他在《大唐西域記》中把這座泰米爾文化的中心城市稱作“建志補(bǔ)羅”:“達(dá)羅毗荼國(guó)周六千余里,國(guó)大都城號(hào)建志補(bǔ)羅,周三十余里。土地沃壤,稼穡豐盛,多花果,出寶物。
氣序溫暑,風(fēng)俗勇烈。深篤信義,高尚博識(shí),而語(yǔ)言文字,少異中印度。伽藍(lán)百余所,僧徒萬(wàn)余人,皆遵學(xué)上座部法。”達(dá)羅毗荼國(guó)即彼時(shí)統(tǒng)治泰米爾納德地區(qū)的帕拉瓦王朝,但帕拉瓦國(guó)君大多信奉印度教,偶有信奉耆那教,同時(shí)寬容其他宗教。
公元1至5世紀(jì)間佛教曾在建志蓬勃發(fā)展,傳說(shuō)印度禪宗28祖菩提達(dá)摩是5世紀(jì)帕拉瓦某國(guó)王的三王子,自香至國(guó)航海來(lái)廣州而北上弘法,始成中國(guó)禪宗初祖達(dá)摩祖師——此為《景德傳燈錄》《傳法正宗記》等漢語(yǔ)佛教文獻(xiàn)記載,印度文獻(xiàn)中只稱他為“少林功夫創(chuàng)始人”。不管怎么說(shuō),到了玄奘赴天竺時(shí),佛教在印度全境已趨衰落,但作為曾經(jīng)三大宗教神廟林立的圣地,《大唐西域記》中“伽藍(lán)百余所,僧徒萬(wàn)余人”的描述或許并非夸張。何況玄奘去建志補(bǔ)羅本是為繼續(xù)南行,渡海赴僧伽羅學(xué)習(xí)上座部佛法,適逢僧伽羅國(guó)戰(zhàn)亂,大批僧侶北上建志避難,無(wú)奈才向這群北漂僧就地求法。
建志補(bǔ)羅見(jiàn)證了帕拉瓦石刻藝術(shù)的高光時(shí)刻,也拉開(kāi)了泰米爾納德地區(qū)石砌神廟建筑的帷幕。如果只能在這座“千廟之城”中拜訪一座神廟,我無(wú)疑會(huì)選那羅辛哈跋摩二世敕建的吉羅娑之主神廟。聽(tīng)名字便知這是一座濕婆派神廟,吉羅娑之主是濕婆的別號(hào),今天位于我國(guó)西藏的吉羅娑山,是印度教神話中濕婆的永恒居所。這座建于公元700年前后的神廟雖然不大,卻已有了早期達(dá)羅毗荼石砌神廟的一切主要構(gòu)件,自東向西依次為:山形瞿布羅塔門、神牛南迪殿、曼達(dá)波柱廳、胎室和胎室上方的角錐形維摩納主塔,構(gòu)成一個(gè)步步深入的線性宗教空間。
其中胎室起源于安放中心神像或林伽的神龕,是一座神廟最核心的建筑體,重要性堪比天主教堂的至圣所。周圍狹窄幽暗、僅由昏暗油燈照明的回廊供信徒順時(shí)針繞行神像使用,也被視作胎室建筑的一部分,進(jìn)入胎室繞行參拜的過(guò)程是一種進(jìn)入子宮重獲新生的空間象征。如此,沿著水平軸線從東到西,信徒將走過(guò)一條由導(dǎo)入空間到禮儀空間再到覲見(jiàn)空間的朝圣之路,逐步抵達(dá)神廟被藏起的精神核心。
有時(shí),覲見(jiàn)空間和禮儀空間中還會(huì)有一個(gè)過(guò)渡空間,我們幾天后繼續(xù)南下考察的朱羅王朝三大廟,就是在帕拉瓦人奠定的基本規(guī)制上不斷補(bǔ)充附屬空間、增大建筑和雕塑規(guī)模的結(jié)果。朱羅三大廟是南印最著名的世遺和中世紀(jì)印度教建筑的名片,而吉羅娑之主為代表的帕拉瓦王朝神廟是朱羅神廟的源頭。
在印度古典建筑學(xué)與堪輿理論中,人類在大地上建造的神廟是宏觀宇宙的縮影,同時(shí)又是人體微觀宇宙的投射,一座完美的神廟,其構(gòu)件之間的位置和比例需嚴(yán)格對(duì)應(yīng)人體的七個(gè)主要脈輪。相傳與吠陀經(jīng)典一樣古老的《筑造論》中對(duì)這些對(duì)應(yīng)關(guān)系有詳細(xì)的記載,比如眉心輪對(duì)應(yīng)胎室,頂輪對(duì)應(yīng)胎室上方的維摩納主塔,心輪對(duì)應(yīng)曼達(dá)波柱廳,臍輪對(duì)應(yīng)南迪殿等。這種解剖學(xué)—怛特羅—宇宙觀之間的一體論在南印發(fā)展得尤為純熟:我即原人,原人即神廟,神廟即世界。從進(jìn)入神廟到完成對(duì)神像或林伽“覲見(jiàn)”的過(guò)程既是一場(chǎng)同宇宙本源的對(duì)話,又是一種逐漸深入自我并打開(kāi)身心的內(nèi)觀。
吉羅娑之主神廟雖然是建志城內(nèi)現(xiàn)存最古老的濕婆廟,但放到達(dá)羅毗荼印度教神廟建筑史中看,它并非起點(diǎn),而是一個(gè)典范性的小高峰。在它之前還有帕拉瓦人開(kāi)鑿在沿海地區(qū)的石窟神廟,甚至可能有成熟的木質(zhì)神廟建筑,其歷史與印度教信仰的歷史一樣久遠(yuǎn),只是木構(gòu)易朽,沒(méi)有留下物質(zhì)證據(jù)罷了。此外,南印安達(dá)羅王朝、北印貴霜和笈多王朝的佛教石質(zhì)神廟也一定為早期印度教石質(zhì)神廟的建造提供了靈感和競(jìng)爭(zhēng)的刺激源。吉羅娑之主神廟柱廳外墻上騰躍而非蹲距的獅子就是帕拉瓦晚期風(fēng)格的特征,而環(huán)繞主體建筑周圍的繞行院落也是晚期特征。
院墻內(nèi)側(cè)的58個(gè)小型壁龕中生動(dòng)的深浮雕有如一連串砂巖浮世繪,在相對(duì)迷你的框形空間內(nèi),以幾近圓雕的縱深嵌入了極富動(dòng)感的畫面:濕婆的舞王相、施恩羅波那相、誅安陀加相,其妻雪山女神帕爾瓦蒂作為杜爾伽女戰(zhàn)神的誅水牛相,表現(xiàn)濕婆合家天倫的蘇摩室建陀相…無(wú)時(shí)無(wú)刻不在提醒你大天是神廟資助者“獅子王”的家神。壁龕側(cè)壁殘存的壁畫是世上僅存的兩處帕拉瓦壁畫之一,可惜風(fēng)化剝落嚴(yán)重,不把整個(gè)身子壓扁鉆進(jìn)壁龕內(nèi)部幾乎看不見(jiàn)。
最精彩的還是神廟主殿外墻上的一圈巨型石雕,它們集中展現(xiàn)了1300年前帕拉瓦人對(duì)砂巖這種介質(zhì)的純熟掌握。與笈多時(shí)期達(dá)到巔峰的、以靜穆的坐姿和立姿為主的北印佛教石雕不同,印度教石雕多表現(xiàn)動(dòng)感十足的神話故事場(chǎng)景。由于每位主神都有諸多化身,判斷主神正以哪一個(gè)小號(hào)登錄的重要依據(jù)就是看他/她正在誅殺哪個(gè)惡魔,比如上文提到的誅水牛怪摩西沙和誅阿修羅安陀加相,著名的濕婆腳踏愚魔跳滅世之舞的舞王形象也可以歸入這類誅魔相中——類似于基督教圖像學(xué)中判斷圣徒身份的重要依據(jù)是他或她殉道的工具。
這些暴力場(chǎng)景對(duì)如何用最笨重的介質(zhì)來(lái)表現(xiàn)最矯健的動(dòng)作和戲劇張力提出了挑戰(zhàn),帕拉瓦人的長(zhǎng)項(xiàng)正在于此。此外他們還好創(chuàng)新,常在那些高度程式化的圣家族場(chǎng)景中添入意外生動(dòng)的新細(xì)節(jié),比如主殿外墻壁龕中有一尊經(jīng)過(guò)灰泥修復(fù)的大天烏瑪隨侍相,就背離了濕婆夫婦各自執(zhí)法器并排正襟危坐的傳統(tǒng),讓翹腿而坐的濕婆親昵地抬起斜倚在座位上的烏瑪?shù)南掳停裼中哂窒驳纳袂閹缀跻糁鴰r石溢出來(lái)。
又如主殿轉(zhuǎn)角壁龕里的濕婆成親圖,表現(xiàn)這一場(chǎng)景的通常程式是“俊美新郎相”,而帕拉瓦人卻給了濕婆一個(gè)發(fā)辮披散的雷鬼頭,配一個(gè)極其性感的扭臀動(dòng)作,仿佛大天因?yàn)槌两谟磹?ài)的狂喜中而忘了妝扮。雷鬼發(fā)辮其實(shí)來(lái)自濕婆的另一個(gè)常見(jiàn)形象“南面經(jīng)師相”,此相將大天表現(xiàn)為面朝南方坐在榕樹(shù)下講道除惑的導(dǎo)師,吉羅娑之主的主殿壁龕里就有這一形象。通過(guò)巖石傳達(dá)肌肉的美感,讓柔情和力量輪番流動(dòng)在石頭的紋理中,這是看似質(zhì)樸無(wú)華的帕拉瓦石雕的杰出特質(zhì),這一點(diǎn),我們?cè)谀祭漳返木扌透〉袷谏蠒?huì)有更直觀的感受。
吉羅娑之主神廟的維摩納、曼達(dá)波和院墻主殿外墻的南面經(jīng)師相4南印現(xiàn)存最早的石砌神廟位于卡納塔克邦艾霍萊,而帕拉瓦王朝7世紀(jì)前的神廟并無(wú)留存。到了8世紀(jì),帕拉瓦人兵敗于來(lái)自德干高原的老對(duì)手遮婁其人,首都建志補(bǔ)羅淪陷,但熱愛(ài)藝術(shù)的遮婁其國(guó)王不曾破壞吉羅娑之主神廟分毫,反而將一大批建志工匠帶回遮婁其都城帕塔達(dá)卡,仿照吉羅娑之主的樣式興建了大量混合南方達(dá)羅毗荼式與北方那伽羅式的“中間式”風(fēng)格神廟,即著名的“德干風(fēng)格”,遂成印度中世紀(jì)建筑史上一段南北交融的佳話。
昔日的“千廟之城”建志今天當(dāng)然已沒(méi)有千座神廟,但光是獻(xiàn)給濕婆的神廟仍然有108座,這并非杜撰。吉羅娑之主神廟外,最著名的是大約三公里外的芒果樹(shù)之主神廟,同樣由帕拉瓦人首建于7世紀(jì),現(xiàn)存的建筑大部分是朱羅王朝在10世紀(jì)和毗奢耶那伽羅王朝在15世紀(jì)重修的,有著規(guī)模宏偉的曼達(dá)波和瞿布羅,如今是建志香火最旺的濕婆廟,每天定時(shí)做六道普祭,換言之,與僅作為廢墟供人參觀的吉羅娑之主不同,這是一座真正的“活廟”。
這也是一座談戀愛(ài)主題的神廟——主神動(dòng)輒長(zhǎng)達(dá)億萬(wàn)年的愛(ài)情故事是南印人民最津津樂(lè)道的藝術(shù)主題之一,濕婆與帕爾瓦蒂之間無(wú)數(shù)的爭(zhēng)吵與復(fù)合被看作神向人示現(xiàn)的“理拉”,分分合合不會(huì)破壞大天夫婦之間的濃情蜜意,這也被看作對(duì)凡人婚姻生活的指導(dǎo)。本廟的奠基傳說(shuō)正是基于這一“理拉”:有一次大天兩口子又鬧別扭,帕爾瓦蒂被詛咒皮膚變得像她的小號(hào)迦梨一樣黑,為了贖罪,女神跑去附近一棵芒果樹(shù)下苦修,濕婆這個(gè)模范丈夫堅(jiān)持要考驗(yàn)妻子的虔心,先放火燒再放恒河水淹芒果樹(shù);然而恒河女神亙伽本是帕爾瓦蒂的親姐姐,聽(tīng)到妹妹的祈禱后就沒(méi)有再努力鬧洪水了,于是考驗(yàn)成功,帕爾瓦蒂就地用砂土塑了一個(gè)林伽獻(xiàn)給濕婆,就是本廟的主位被拜物“地林伽”了。
另一個(gè)香艷的版本是被水淹時(shí)女神身邊正好有一尊林伽,于是女神趕緊抱住林伽求生,因?yàn)樘箘哦央p乳的形狀刻在了林伽上…可能這就是人類最早的石膏胸像。第三個(gè)版本把這段故事放在男神女神婚前:帕爾瓦蒂正在芒果樹(shù)下崇拜砂土做的地林伽,附近的維加瓦蒂河突然發(fā)洪水,眼看就要淹沒(méi)林伽,護(hù)夫心切的帕爾瓦蒂將林伽抱入懷中緊緊相擁,于是濕婆大為感動(dòng),下凡娶她為妻,這一形象的濕婆從此在泰米爾語(yǔ)中被稱作“溶化在她擁抱里的人”。
我們可以在這些林林總總的民間傳說(shuō)中瞥見(jiàn)泰米爾人民對(duì)“神圣理拉”的理解:即使是濕婆這樣的最高神之一也絕非什么四平八穩(wěn)的完人,神的親密關(guān)系同樣會(huì)充滿磨難,而主神夫婦以戲劇向凡人示現(xiàn)他倆婚姻關(guān)系的不完美,恰是要鼓勵(lì)人們對(duì)自己的配偶多些耐心,像神一樣克服困難往前走。不管這些建廟傳說(shuō)的實(shí)際老娘舅效果如何,烏瑪—帕爾瓦蒂?gòu)拇司妥鳛橘つ讼T谶@座神廟內(nèi)同夫君一起被崇拜。而那棵傳說(shuō)3500歲高齡的芒果樹(shù)至今仍屹立在神廟內(nèi)庭中央,圍繞它筑起了高臺(tái),供人們像胎室里繞林伽一樣順時(shí)針繞樹(shù)祈愿。
據(jù)說(shuō)這顆圣樹(shù)的枝丫可以長(zhǎng)出四種口味的芒果,可惜一月不是結(jié)果的季節(jié),連一個(gè)青芒果都沒(méi)看到。上面提到芒果樹(shù)之主是五元素神廟中的“地”元素廟,實(shí)際上“五元素神廟”是南印傳統(tǒng),人們相信濕婆曾以地、水、火、風(fēng)、空五種形式的林伽示現(xiàn)于南印各地,這些林伽中的四座至今被供奉在泰米爾納德邦,第五座風(fēng)林伽神廟則在安德拉邦。早在《阿達(dá)婆吠陀》中就有人體內(nèi)的五元素如何與五種體液對(duì)應(yīng),共同影響身心健康的論述,與中醫(yī)理論和歐洲中世紀(jì)四體液說(shuō)多有相通,到了后吠陀時(shí)代,隨著三相神取代吠陀舊神成為至尊主神,濕婆也被看作是宇宙中一切元素的主人,有詩(shī)為證:水、地、火、風(fēng)、蒼穹日、月、阿特曼你擁有這一切,你即一切手持骷髏碗的英俊者啊,為什么你還要浪跡天涯,瘋瘋傻傻從天真的姑娘們手中接過(guò)布施仿佛你一無(wú)所有?
進(jìn)入芒果樹(shù)之主神廟的瞿布羅前,一個(gè)守著塔門賣鮮花的婆婆看到我脖子上戴了一串金盞花環(huán),立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shì)將一串更沉的花環(huán)掛到了同伴頭上,一邊大聲說(shuō):“你是濕婆,她是帕爾瓦蒂…”同伴只能忙不迭掏錢。即使是小販搶做生意都能做出如此氣魄,就是這座地元素神廟的另一種接地氣之處了。